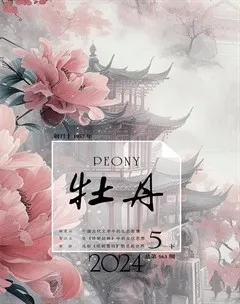論遲子建“小敘事”下的歷史書寫
龔恬
“小敘事”是在后現代的背景下提出的概念,是一種非線性的敘述方式,其本質是由外向內,走進個體的內心世界,從平淡的日常中挖掘出復雜而深刻的意味。遲子建在創作初期便表現出濃厚的歷史書寫情懷和責任感,她以一種有個人情感傾向性的敘事筆法,以小人物、小日常、小故事為切入點,在中國當代文壇擁有不可撼動的地位。
遲子建出生于中國最北邊的一個小村莊——北極村,那里越過邊界便是俄羅斯。她從童年起就接觸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最喜歡的娛樂活動便是聽村里的老人講故事,由此培養了她豐富的想象力。另外,那里還靠近大興安嶺,與大自然做伴的成長經歷奠定了遲子建小說的美學基調,也影響了其作品的敘事風格和題材選擇。有人說,遲子建的“東北敘事”就是一部百年東北史。但是與莫言等人的激進尖銳不同,她的歷史書寫擁有女性作家獨有的柔軟和靈性,又帶有獨一無二的詩意與童話色彩。她筆下的東北大地深沉而樸素,真摯而純真,她的敘事筆調溫柔而不失強韌,蒼涼卻充滿希望,蘊含著個人獨特的生活體驗,向讀者展現了一幅充滿溫情的北國畫卷。
一、“宏大敘事”與“小敘事”
“宏大敘事”(元敘事)與“小敘事”是兩種不同的敘事視角和風格,二者各有優劣,在文學創作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20世紀80年代以來,敘事研究學者越來越關注“小敘事”的獨特作用,并對其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和激烈的討論。
(一)“宏大敘事”下的歷史書寫
“宏大敘事”一詞來源于利奧塔在其著作《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中提出的“元敘事”概念。他認為文學的“元敘事”或“大敘事”是與“現代”一詞相聯結的,是一種具有合法功能的敘事,其敘事功能裝置包括偉大的英雄、偉大的冒險、偉大的航程,以及偉大的目標。“宏大敘事”與政治意識形態緊密相關,曾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十七年文學”階段,以《紅旗譜》《創業史》《紅日》等作品為代表,集中體現了宏大敘事的特點:典型英雄人物的塑造、波瀾壯闊的歷史背景設置、政治性鮮明的創作主題。“宏大敘事”對文學的歷史書寫有重要意義,它可以從宏觀的層面編織歷史情節、構筑歷史空間、審視大環境中的每一個個體。利奧塔認為它是“啟蒙敘事”,從屬于思辨哲學,有助于在發話者和受話者之間建立共識,推動支配社會關系的體制合法化、規范化。然而,利奧塔也提出,20世紀50年代末現代社會向后現代社會的過渡就開始了,原有的敘事體制必然走向解體,“元敘事”也必然向“小敘事”轉變。
(二)“小敘事”下的歷史書寫
“小敘事”是與“后現代性”相關的概念,它是現代社會進入后現代的必然產物,是由“元敘事”分解而來的敘事方式。利奧塔在書中說到,“小敘事”的重要特點是其對“元敘事”的懷疑,它向宏大敘事的合法性、公正性、規范性提出質疑,其背后體現出時代的進步、科學的進步。“小敘事”不僅是政權的工具,還提高了人們對差異的敏感度,它強調“每個人都返回自我”,創造自己“真正的精神世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小敘事”關注的是個體,但是其本質上是集體中的個體,絕對不是處于離散狀態的原子。相反,“它處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復雜、更多變的關系網中”。
學者陳曉明在《小敘事與剩余的文學性——對當下文學敘事特征的理解》一文中對“小敘事”進行了詳細闡述。他提出,“小敘事”即小人物、小故事、小感覺、小悲劇、小趣味……,是后現代時代文學的新發展,是歷史剩余的碎片,是現代性的、剩余的文學品質。他生動地形容后現代的文學寫作是猴子式的寫作,因為它不再盲從主流,并且主動規避了現代社會文學書寫的消費性和功利性,同時一針見血地揭露人性的本質,直擊社會痛點。陳曉明指出,與“宏大敘事”相比,“小敘事”的歷史書寫更能凸顯出文學性,其僅僅依靠文學敘述、修辭與故事本身來吸引人。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小敘事”也更符合新歷史主義的相關理論,其非線性的敘事特點也更適合于文學的歷史書寫,能夠使作家在歷史情節的編碼和虛構上更為得心應手。
二、《碾壓甲骨的車輪》歷史書寫的獨特性
歷史書寫向來是遲子建寫作的重要方向,她始終執著于為小人物立傳,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展示小人物的命運浮沉。《碾壓甲骨的車輪》是遲子建的中篇小說新作,刊登于《收獲》雜志2023年第4期,從起筆到定稿長達八個月。她查閱了大量有關羅振玉和王國維的史學資料,進行了謹慎的審視與修改,才最終成文。
(一)四大樂章形式的行文框架
《碾壓甲骨的車輪》采取了交響樂章的形式來建構全文,共分為四個樂章。
第一樂章名為“櫻花奏鳴曲”,奏鳴曲是一種由三至四個獨立樂章構成的大型樂章套曲,這些獨立的樂章間既有內在聯系又相對獨立,常常展現出矛盾沖突。而“櫻花奏鳴曲”由“我”與丈夫李貴相識相知、公公因貪腐入獄、家境沒落、與賀磊的淵源等“獨立樂章”組成,其間夾雜著李貴看完櫻花后就與“我”吵架、影樓生意慘淡、李貴經常徹夜不歸等現實矛盾,總體上介紹了李貴失蹤的背景。
第二樂章“甲骨變奏曲”正式切入小說正題——甲骨和車輪。小說從李貴的郵件和“我”的回憶視角介紹了李貴的祖父李滿與車輪的故事,交代了李貴失蹤的原因。變奏曲的特點是多個變奏段圍繞一個主題段落進行,在本部分,那只碾壓過甲骨之后便變得有些詭異的車輪是中心主題,李貴與老李的相遇,羅振玉、王國維、王懿榮等人的故事,李滿與巧鳳的故事等都是“變奏部分”。
第三樂章回歸現實,以“洞庭街小步舞曲”為名,小步舞曲素來以典雅、優美、舒緩、端莊聞名。這一章暫時將書寫重點從李貴轉向了“我”,記敘了“我”和賀磊之間的一段曖昧關系。
第四樂章是小說的高潮,也是小說的結尾,作者以“馬車輪回旋曲”命名,頗具深意。小說的懸疑部分走到了一個轉折點,李貴的失蹤似乎另有隱情,而不確定是不是他寄回來的馬車輪也疑點重重。這時“我”與賀磊的關系僵持不前,順順對賀磊的態度也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當有關李貴死亡的線索似乎都指向賀磊時,賀磊卻突然被馬車輪砸成了植物人……作者借“我”的心理活動呈現了多條推理線索,卻沒有給出最終的答案。正如遲子建在創作談中說的,這篇小說還有第五章“未完的樂章”,等待讀者自行去探索。回旋曲由一個主部和多個插部組成,通常采用熱烈、歡快的曲風。但這一章,“我”在合家歡慶的新年夜里卻要面對最親密的兩個男人的死亡,而且自己的情夫很可能是殺死丈夫的兇手,心情著實談不上歡快。作者這一命名,呈現出和小說標題一樣的敘事張力,與小說未明的結尾一同給人一種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感。
(二)雙線并行的敘事結構
繼《喝湯的聲音》與《白釉黑花罐與碑橋》之后,《碾壓甲骨的車輪》成為遲子建書寫東北歷史的第三篇小說。遲子建在其創作談中曾提及,這三篇有關東北歷史的小說都是雙軌結構,一條是現實,一條是歷史。不同的是,新作《碾壓甲骨的車輪》以懸疑來推進故事。作者將故事發生地設置在東北重鎮旅順,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時空在羅振玉的舊居與大云書庫交匯,而歷史與現實的兩條主要故事線凝結于那只碾壓了甲骨的車輪上。羅振玉、王國維、王懿榮、李滿等與甲骨或是車輪有關系的人站在歷史的一邊,“我”、李貴、賀磊等人站在現實這一邊,就像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卻因一只車輪被硬生生拉在了一起。作者主要在第二樂章劃定了小說的歷史時空范圍,“日本戰敗”“蘇軍進駐旅順”“1945年8月”等真實的歷史節點體現出作家對歷史的尊重,這也是“小敘事”結構得以順利運轉的集體場域。而羅振玉收藏、研究甲骨和金石碑刻,編撰《殷墟書契》;王懿榮在中藥材中發現“龍骨”,潛心收藏研究,卻因八國聯軍侵華而不得已變賣家財;小說家劉鶚購得王懿榮收藏的千余片甲骨卜辭進行研究考證,著《鐵云藏龜》等,這些歷史事實正是海登·懷特所說的可能用于重新編碼的“系列事件”。另外,李滿和巧鳳的愛恨情仇、人們哄搶羅家的古董收藏、李滿的馬發狂沖進人群、馬車碾碎了甲骨等,這些故事則屬于具有隱喻意義的“想象的事件”,是文學的歷史書寫中的虛構部分。歷史與現實在文中不著痕跡地交織出現,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小說的敘事空間,提高了作品的可讀性和情節的豐富性,與小說的懸疑氛圍相配合,使人感到和諧而富有吸引力。
(三)小人物與大歷史
在這篇小說中,遲子建仍然秉持著“以小人物書寫大歷史”的文學立場。她曾在訪談中說過,真正的史詩是“能夠不動聲色地把時代悲痛溶入老百姓的喜怒哀樂之中,通過整個人物的描述而令人感動”。她側重于寫人與人之間的日常關系,關注小人物的悲歡離合,以一顆滄桑而溫暖的心去揣摩和貼近人物,在平淡的生活中求真,在冷漠的人性中求暖。在這篇小說中,遲子建從“宿命論”的角度來書寫小人物的命運:李貴本可以踏踏實實靠自己的能力掙錢,卻理所當然地享受著父親的貪污所得,導致最后一無所有;李滿本可以按計劃駕著馬車離開,卻因為貪念混入搶奪羅家寶貝的人群中,這才導致馬車壓碎了甲骨,從而引發后續一系列悲劇。人們無法改變現狀,只能將一切都怪罪在命運的頭上,將一切都歸結于“甲骨的邪性”“車輪的詛咒”。車輪在小說中不僅僅是道具,還是小說中擁有全知視角的第三方,冷著眼看著這些人在與命運的糾葛中痛苦掙扎。陳曉明認為,“小敘事”下,作家熱衷刻畫的是人物性格心理的多面性,并且主要以含混的方式表現出來。生活總是被似是而非的假象所遮蔽,讓人看不到真相。羅振玉、王國維、王懿榮、劉鶚等人是不是受到了甲骨文的詛咒我們不得而知,李滿、李貴一家甚至于賀磊是不是受到了車輪的詛咒我們也不得而知,我們能看到的是歷史表象背后更深刻的人性本質,是作家通過小人物展現的宏大的歷史情懷。
三、結語
正如陳曉明所說,宏大的歷史敘事已經很難在當代小說中出現,特別是中短篇小說,小人物、小敘事、小感覺等“小敘事”構成了小說的基調。因此,文學應該更加關注當下人們的生活情態,關心當下人們的內心世界,以更為敏銳的筆觸探尋人性的本質,抓住生活的真相,從而獲得人生的啟示。“小敘事”是遲子建從創作初期便堅持的寫作原則,更是她創作的舒適區。然而,從這篇新作可以看出,她正在進行新的嘗試,嘗試努力跳出舒適區,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其最大的改變在敘事語言方面。遲子建的小說向來以詩意的語言為標志,充滿日常性的溫情,受到學界的稱贊。她傾向于以溫情的筆觸書寫人生的黑暗面,使人在絕望中仍能感受到一絲希望。但也有人認為她有些時候過分溫情,會阻遏對人性中惡的一面的更深層的探究和揭示。當時,遲子建對此也作出了回應,她認為自己大部分作品的創作基調是偏向蒼涼和憂傷的,溫情只是其中用來潤色的小部分;她也強調自己對于辛酸生活的溫情表達本身沒有錯,只是表達溫情的火候有時掌握得不好。很明顯,現在的遲子建已經能夠很好地掌握溫情的火候了,這份溫暖在她的寫作中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她身為女性作家獨特的情懷與視野,與她的“小敘事”結構相輔相成,為其歷史書寫增添了一份人情味、煙火味。
(華南師范大學)
責任編輯 ?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