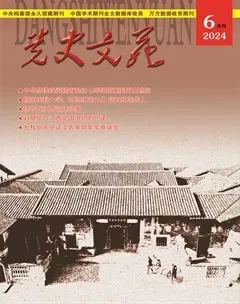淺析延安時期郭沫若文化建設構想
徐昊
延安時期郭沫若的文化建設構想異彩紛呈,作為研究對象具有豐富的內容。本文結合郭沫若生平宏觀考察其文化建設構想產生的歷史背景,并結合郭沫若文化活動具體實踐,對其文化建設構想進行梳理。
一、延安時期郭沫若文化建設構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郭沫若是延安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和文化界人士之一。五四運動時期郭沫若棄醫從文,在日積極投入新詩與白話文的創作,擁護新文化運動,形成《女神》詩集成名于文化界。在長期創作中,郭沫若形成了關于文化建設的構想。
(一)郭沫若文化建設構想的萌芽
旅日時期,郭沫若受到共產主義思潮的影響,選擇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一時期創作了《王陽明禮贊》,將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與蘇俄作對比。1923年,郭沫若回國繼續文藝創作與革命活動,其在文章《泰戈爾來華的我見》中明確表示,唯物史觀是解決時代問題的唯一正確道路,由此其作品轉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次年,郭沫若翻譯完成《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郭沫若多次談到這次譯書的巨大收獲,“弟于社會經濟諸科素無深到研究,惟對馬克思主義有一種信心……弟深信社會生活向共產制度之進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這是必然的路徑。”
(二)郭沫若文化建設構想的發展
北伐戰爭中,郭沫若擔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從事支持大革命的文化宣傳。在此期間,郭沫若深入社會基層,得到了現實的磨煉。大革命失敗前夕,郭沫若發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曝光蔣介石違背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教導,背叛大革命的罪行。后郭沫若參與南昌起義,與國民黨及其文化界擁躉決裂。爾后,郭沫若為逃避國民黨迫害,避居日本,卻遭到日本當局的監控。他并未氣餒,仍對革命持樂觀態度,堅持共產主義者立場。但在失敗與現實的考驗下,郭沫若“從以前的浪漫主義的傾向堅決地走到現實主義的路上來”,以現實主義文風,著成詩集《恢復》。在翻譯馬恩經典著作的過程中,郭沫若深入探索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由此提升了其理論素養,并且能夠將這些基本概念與中國的國情實際結合起來,為其后續的文化和歷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時期他也將興趣轉向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這并非僅出于歷史興趣,也是為了實現對未來社會的期望。郭沫若以辯證唯物論為工具,深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發展,從而開啟了基于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研究生涯。郭沫若通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觀點,大膽研究出土文物、甲骨卜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及一系列考古著作,并以此有力反駁了當時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中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也回擊了“整理國故”之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固步自封,為其文化思想在延安時期的進一步發展作了準備。
二、為抗日現實服務
郭沫若自早年對歌德的研究開始,便強調文學創作與現實的聯系。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為出發點,郭沫若在延安時期的文化建設中為抗日現實服務,開展救亡文化工作。
(一)主持文化工作
盧溝橋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流寓日本的郭沫若擺脫日本軍部的監控,離開妻兒回國參與抗日救亡。在周恩來的提議下,黨中央作出了“以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為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領袖的地位”的決定。南京淪陷后,大量文化界人士、抗日救亡團體遷至武漢,國民政府為塑造尊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象,組建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其成員除國、共黨員外,也有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并設負責宣傳的第三廳。郭沫若憑借在文化界的聲譽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成為陳誠中意的候選人。收到陳誠邀請擔任第三廳廳長時,郭沫若本不想接受,認為在國民黨的控制下從事文化宣傳工作受制于人,并且“一做了官,青年們是不會諒解的”,郭沫若希望加入到邊區和延安的抗戰與建設中去。但在周恩來同志的勸說下,郭沫若遵從了黨組織的意見,接受了第三廳廳長的職務,開展勞軍活動。郭沫若在《對于文化人的希望》一文中指出:“目前的戰時文化是應該注重在宣傳上的……希望目前集中于后方大都市的文化人,更能夠向鄉村間散播。”因此,郭沫若領導第三廳組織開展文化活動,下屬的宣傳隊深入前線、后方勞軍,動員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參與,鼓舞民眾的抗戰積極性。孩子劇團是第三廳中最特殊的一支抗戰宣傳隊,成立于1937年9月,起初在上海,由22名成員組成,后合并為長沙兒童劇團。在敵人的炮火下,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戰區抵達重慶。郭沫若特別關照孩子劇團的生活問題,專門發文:“職廳所屬孩子劇團,工作素稱努力……因經費無著,將不免流離失所,則請準許將職廳擬辦而迄未舉辦之歌劇隊一隊經費移充。”在郭沫若等同志的關愛下,第三廳下屬的抗敵演劇隊、宣傳隊、孩子劇團和戰地文化服務處等都建立了秘密的黨支部或黨小組,接受中共中央長江局的領導,抵制了國民政府的消極抗日、防共等落后思想,更好地實現了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武漢淪陷,第三廳遷渝后,蔣介石改組第三廳,脅迫其成員加入國民黨。在郭沫若的領導下,第三廳文化工作者抵制國民黨阻礙正常文化抗戰運動的決定,集體辭職。國民黨被迫解散了第三廳,但為阻止文化工作者流向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1940年11月1日,蔣介石下令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仍由政治部領導。這一時期,郭沫若通過組織各種文化活動,吸收了包括茅盾、老舍、胡風、陶行知、鄧初民、翦伯贊等知名人士,相當程度上擴大了文化界統一戰線的力量。作為從事文化研究的委員會,雖然無法直接領導和組織進步文化活動,但是在郭沫若的領導下,成員們采用了正確的文化策略,利用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地位,在學校舉辦講座,特別注重在青年學生中擴大影響。
(二)抗日文學創作
延安時期,郭沫若也進行了大量的抗日文學創作,興辦了報刊、雜志。郭沫若主編的《中原》則是其唯一主編的雜志,由群益出版社發行。該出版社的設立是為郭沫若祝壽這一文化界大事后確定的重要工作。“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這一評價確立了郭沫若在文化界的領導地位。《中原》創刊于1943年6月,后至1945年10月終刊,郭沫若領導的《中原》聚集了一批左翼文化學者,形成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創作團隊,為他們在國統區壓抑的學術氛圍里創造了一片寶貴的凈土。這個團隊以郭沫若、侯外廬等人為代表,特別注重對思想史的研究。他們在完成一系列古代史著作的基礎上,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系統審視中國的思想文化,引領了一股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浪潮。郭沫若包括《十批判書》在內的思想史著作大多完成于這一時期,實現了抗日文化宣傳。隨著抗戰形勢的變化,國民黨政府加大防共限共力度,在思想上推崇王陽明,倡導四維八德復古讀經。以所謂中的哲學、力行哲學、種種曲解的三民主義思想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又有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和葉青的唯心論、外鑠論污蔑。在這一背景下,重慶左翼文化學者通過學術研究清算唯心史觀,反對國民黨消極抗日行徑。為滿足這一思想文化戰線斗爭的需要,郭沫若等進步人士選擇以明清時期為研究對象,以史可法等具有民族氣節的烈士反清抗爭,與洪承疇等漢奸的投敵進行對比加以諷喻,展現了學術研究與時代政治的密切結合。
三、吸收傳統文化、建立新文化
(一)正確地認識傳統文化
郭沫若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鐘,不吝溢美之詞。每當中國文化遭遇到外界的挑戰,“反而增加了我們民族和文化的興盛”。他認為孟子的仁德之學、莊子的自由之思、荀子的穩重之說、韓非子的銳利之辯各有卓越之處。在哲學方面,儒道并重;在藝術領域,中國壁畫、音樂、雕刻、田園詩歌皆獨樹一幟。郭沫若對傳統文化也深切體察到其缺陷,認為“周秦之際,初期的學者于實踐理性的探討誠別開一個新面……然于純粹理性方面則不免有偏枯之憾”,并且受到焚書坑儒和佛教的傳入,“致使純粹科學無法誕生”。并且,中國傳統學術“以帝王之利便為本位以解釋儒書,以官家解釋為楷模而禁人自由思索”,限制了文化的發展。最終,隨著中國深厚的文化傳統負擔過重,歷史漫長深遠,人們的思維總是向往歷史,導致面對外來文化時缺乏吸收的意愿,進而缺乏自我更新的意識。
(二)吸收、改造傳統文化
郭沫若認為,要吸收與改造傳統文化,首先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即采取唯物史觀,從生產力與社會關系變遷入手。他認為,正是由于社會變革,才會產生新的法制……法家思想的濫觴也恰好證明,春秋時代中國社會劃時代的變革。在評價歷史人物時,郭沫若以人民為本位作判斷。如他贊美屈原“哀民生之多艱”的詩句,稱其為悲劇的偉大民族詩人,而斥責韓非子的嚴酷律法。郭沫若也有運用辯證法的意識。對于素有暴君之稱的商紂王,他也贊美其“打平東夷,中華民族才能向東南部發展”的功績。在吸收傳統文化方面,郭沫若在《“民族形式”商兌》中指出,“民間形式便成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應活用傳統文化的有益成分,使其以民族形式滿足普羅大眾的文化產品需求。在改造傳統文化方面,郭沫若批判封建文化的迷信、壓迫性,認為它阻礙了社會和人的發展。他主張摒棄封建主義的文化糟粕、玄學,稱其為“玄學鬼”,也反對復孔教、復古讀經的思潮。
郭沫若新文化建設的構想結合中西文化,開辟新文化。其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指出新文化新文學服務于最廣大人民群眾和政治經濟的基礎上,綜合整理中西文化的先進成分。既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完成中國傳統文化與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文化的結合,也就是要結合中西文化的優點,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服務。
【參考文獻】
[1]田亮.略論郭沫若的民族新文化建設構想[J].郭沫若學刊,1992 (02):8-15.
[2]《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5-46.
[3]龔繼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1892-1978)(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1992:375
[4]《沫若文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278.
[5]沈衛威.新發現抗戰期間郭沫若未刊信函一百〇二封釋讀[J].文藝爭鳴,2023(12):39-62.
[6]馬建強,公坤.武漢抗戰時期“政治部第三廳”組建中國共兩黨的政治博弈[J].安徽史學,2023(03):104-112.
[7]《沫若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10-11.
[8]《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93.
[9]《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12.
[10]《沫若文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286.
[11]《沫若文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29.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黃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