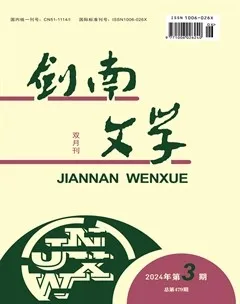天寧寺的圓月
江劍鳴,男,四川平武人,四川省作協會員,四川省散文學會會員,以鄉土散文創作為主,出版有散文集《境界》等三部,小說集《一路風塵》一部,曾多次獲得省市級獎勵,并有作品入選高中語文“新人文”讀本第四冊。
正月十五晚上八點,朋友斌電話邀約,赴城外北山半坡上的天寧寺喝茶,拜訪演普法師。年初第一個月圓之夜造訪山寺,有幾分浪漫,幾分神秘。那輪皓月,有點像特意為我們營造出的一派明凈而清涼的意境。
初春的夜風,裹挾著寒潮的凜冽,迎面吹拂,在耳邊呼呼作響,寒意直往脖子里灌。這幾天寒潮來襲,涪源山區的大山頂上全是皚皚白雪。我緊了緊圍巾,把手揣進褲兜里。路邊的荊棘和草叢里,沒有鳥鳴,沒有蟲奏,山巒、房屋、樹木、荊棘和石頭,一切都酣眠在淡淡的元宵月下。
玉盤似的明月,懸在頭頂,似乎在跟我們一同前行。我感嘆:“今夜的月色金黃。”朋友何說:“月色本就這樣。”我辯駁:“我還見過銀白色的、血紅色的呢。”北山上下,涪江兩岸,對岸的鎮南山樹林,鎮南山背后藥叢山的輪廓,都沐浴在淡淡的清輝里。山下龍安城,燈火輝煌,山上卻聽不見一絲聲音。一路上無聲無息,一派寂靜。整個涪源山區之夜,似乎也一派寂靜。這寂靜,恰與我們拜訪寺廟的氣氛契合。
我是第一次見到演普法師。一襲僧袍,襯托出法師高挑的身影。一頂藍色線帽,簡單而樸素。一副眼鏡,閃爍著睿智和善良。僧袍的袂角,在夜風吹拂中,飄飄欲舞,給人飄逸之感。雙方作揖寒暄后,法師領我們一同享受寺廟的寂靜和月夜的美妙。
相對于山下龍安城里有五百七十年歷史的報恩古寺,天寧寺只是嬰兒。報恩寺在古城中間,天寧寺在城東北的山坡上,依山而建,狀若塔形,故而之前名曰寶塔寺。報恩寺是朝廷命官的獻禮式作品,而天寧寺則是純民間的宗教建筑。報恩寺是國家4A級文物保護單位,不準有僧侶和煙火,老百姓偶爾燃幾炷香蠟燒幾把紙錢,也只能在山門外。報恩寺下轄的十幾座寺廟,早已荒破頹圮。三十年前,老百姓自發募資捐款,舉信眾之力,城外山坡上才有了這座紅墻碧瓦的建筑,也才有了我今夜的寺前賞月之行。
站在寺前小廣場,龍安城夜景盡收眼底。老城區的燈火,明滅閃爍,東皋灣的燈光,整齊明亮。匯口壩的高樓,輪廓上的霓虹燈不停變幻色彩,樓內居民住戶的燈光,或明或暗,異彩紛呈。南橋、飛龍橋和彩虹橋,以及江堤兩岸的五彩路燈,形成三縱兩橫四條明亮的彩色光帶,涪江水在燈光里安安靜靜地緩緩流淌。月光伴著燈光的倒影,在江面上詮釋一個活動著的成語——“流光溢彩”。沿涪江十里,新舊三塊城區,正好形成了一條燈光的巨龍,安靜地躺在涪江岸畔,盡情地享用龍安城元宵夜的一輪明月。
小廣場跟前的佛堂、羅漢堂、大雄寶殿,高大巍峨,聳立在高高的臺階上。畢竟是夜晚,看不清仿古建筑屋脊走獸的雄姿,只能望見翹角飛檐在夜空天幕里的幾幅刀法簡潔的剪影。由于寺廟還在建設中,尚沒有傳統意義的晨鐘暮鼓,飛檐上也沒有風鈴的叮叮當當。除了微微風聲,只余萬籟寂靜,一片安寧。這是佛門凈地應有的氛圍吧!
演普法師帶領我們參觀小魚池。聞見人聲,或者是受燈光驚擾,幾尾紅鯉,遠遠游來,停在我們眼前,張望著我們這些來自紅塵的凡夫俗子,又似在歡迎我們的月夜造訪。透過玻璃的燈光,投映在水池上,有幾分朦朧,幾分神秘。幾尾弱小的生命,輕輕游動,攪動了水面的平靜,為孤寂的山寺添了幾分靈動。我覺得那些小生靈們,似乎也正在賞著這山寺的夜月呢。寺廟里的春梅,應該是白如雪,紅如火,也許還有蠟梅,金黃滿樹,開得正旺,可此時,它們卻隱入了夜的暗里,不示于我們這些不速之客,只是偶爾飄出幾縷淡淡的暗香,傳遞著幾縷令人心曠神怡的音訊。
魚池側旁是一處憩園。磚墻邊種著美人蕉,枯黃的莖葉掩護著蕉根在泥土里冬眠,恐怕它們正在儲蓄新一年蓬勃生長的精力吧。冬眠蟄伏的也還有蟋蟀、螻蛄和蚯蚓吧?一切生物的休眠,都是為了新的生長。幾叢本地品種的篪竹,高潔,茂盛,掩映著半個園子,似乎正在拔節生長。竹葉在夜風中唰唰作響,似乎在輕輕地吟誦,或在贊美這初春的夜月。倘若盛夏炎熱時,走進這里,會頓生涼爽,從肌膚,到腠理,到血脈,到內心。朋友斌說:“取名竹緣吧,諧音園圃,又含緣分。”大家稱妙,另一長于美術的朋友波立刻表態:“哪天我弄塊大石來,刻上這倆字,立在這里。”演普法師作揖:“阿彌陀佛。”
突然想起梁人劉效先的半首詩:“幽人住山北,月上照山東。洞戶臨松徑,虛窗隱竹叢。”南北朝的梁人劉效先,距今已經一千四百多年了,但這些詩句,不正是今晚月夜山寺的寫照嗎?
演普法師簡樸而雅致的茶室,在竹林之下。大家圍坐在茶幾前,他招待我們喝上佳的普洱。那茶幾是一根雕作品,不大不小,簡單,古樸,自然。法師背后正面墻上,掛著一幅美術作品,是國畫,水墨殘荷,透著濃濃禪意。我們背后墻上,掛著一件木刻作品,大悲咒,豎排版,黑底黃字,莊重,典雅。雅致的小黑陶茶杯,深紅的普洱茶水,飄起裊裊輕煙,散發出濃濃的香氣,熏染著茶室,和茶室里的每一個人。我們似乎就籠罩在一派祥云中了。除了窗外偶爾傳過細微的風聲,一切都很安靜。一口暖茶,周身同泰。窗外照明月,室內飲香茶,這是何等閑適的享受啊!
窗外有風聲,但我們在室內,感覺不到寒意。屋子里沒有空調,沒有電爐,沒有生炭火,但主人熱情,我們的談話熱烈,連窗外的圓月,也似乎在羨慕我們這其樂融融的氛圍呢。
我告訴法師,我這六十歲的生涯里,與寺廟有緣。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在磨刀河畔一座掀了菩薩的名叫觀音寺的破廟里,居住了十四年,初中畢業后,才搬離。到讀師范時,又在報恩寺萬佛閣里讀了半年書。可惜,我至今都不是佛教徒。我家里曾有過虔誠的佛教居士——妻的祖母。一個八九十歲的老太婆,居然能夠徒步登峨眉,朝普賢,堅持十多年。后來我坐火車,坐汽車,坐纜車,登上峨眉金頂,尚且感覺勞累不堪。不知道祖母當年的徒步朝拜,是何等艱苦啊!談到這里,我眼前浮現出祖母的形象,親切,和善,簡直就是一尊菩薩。
我讀過幾本書,但算不得儒生。也讀過道教常識,但我不敢說了解道教。我雖然不是佛的信徒,也沒有皈依木魚青燈的打算。我鄙視社會上有些人,項上掛一長串,手里玩一大串,說是佛珠,某處高僧大德開過光,但那項上或者手指上,還同時戴著黃燦燦的俗物,令人感覺不倫不類。有人成天價口不離阿彌陀佛,卻懶惰自私,貪婪成性,恃強凌弱。在我眼里,把玩珠子,念幾句佛經,他們未必真向善向佛,未必能立地成佛。尤其是當今的滾滾紅塵中,許多人迷失了自我,喪失了應有的本性,墮入萬劫塵埃。人心浮躁,邪惡肆掠,魔鬼猖獗,與人類共同向往的和諧幸福,相去甚遠,造成許多莫名的痛苦甚至傷害。
演普法師給我們續上熱茶,茶香繼續在屋子里彌漫。我們還談到了儒家君臣父子仁義禮智的理學,道家陰陽五行順其自然的無為,以及農村的端公和傳統的巫文化。法師耐心地聽我啰里啰嗦的傾訴,而后,他告訴我:“佛無處不在。儒釋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宜截然分割。我們生活在紅塵里,完全擺脫其擾, 不大可能,但我們保持心距,修煉自我,即可成佛。”
是啊,悟出善良慈悲的本性,拂去塵埃,遠離邪惡,回歸善良悲憫本真情懷,尋求內心的清凈,積德行善,是歷朝歷代各個民族各種社會制度所共同倡導的精神目標。在追求三觀認知方面,儒釋道幾趨相同。比如梅花,臘梅春梅,紅梅蠟梅,名字雖異,但都能給人視覺和嗅覺的貢獻。
我曾經造訪過寶光寺、峨眉山、樂山大佛,都是白天去的,在喧囂嘈雜的氛圍里,作為人文景觀的熱鬧參觀欣賞,沒有當是尋求心靈的安慰之行。只有今天,月夜造訪佛門。我已經不把法師當做普通的僧人,而是當做文化上可以交流的一個智者,一個知音。今晚,他的“心距”一說,讓我受益匪淺。他那眼鏡片后面,閃爍著智慧的光芒,給人許多鼓舞,令人難忘。
今夜,淡淡月光下的天寧寺,別有一番風韻,天寧,地寧,心寧,因為這境地清凈無比,因為有我們四個茶客不期而至,因為有演普法師的香茶熱情招待,因為有月夜暢談的快樂。
古人曾經月夜勃勃興致訪戴,沒有訪著,就興盡而歸,居然還說毫不遺憾。今晚,我們四人沒有在家看聯歡晚會,沒有在牌桌上“殺家搭子”。我們乘著金黃的圓月,披著淡淡的月色,造訪寺廟,拜會演普。在清凈之所,有醇香的普洱茶佐伴,庸俗雜念下沉,心佛自然上升,我這六十多歲生命的內心,頓感平和,頓覺寧靜、神爽、氣清。
亥時將過,我們走出茶室,告別山寺,準備下山。北山的寒風已然不再凜冽。燈明亮,夜不黑,心不暗。回望對岸的鎮南山,山下龍安城林立的高樓,一江不息的流水,兩岸的萬家燈火,都沉浸在月色里,好如一幅壯美的巨型油畫:涪江夜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