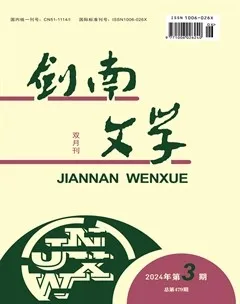回鄉偶書
一
初夏的陽光好像琥珀,溫潤剔透,沒那么照人,尤其是在穿洞溝里行走,空氣中有絲絲涼意,陽光照在身上,反倒感覺溫暖舒適,好像小時候我婆撫摸著我的腦袋。
新修的進溝水泥路和出溝的河水并行著,形成一動一靜兩條引導線,專門負責穿洞溝村的迎來送往。這次回老家,我特地選擇在生日這天。我在這里出生,在這里度過童年,這里有我的根。一大早,我就背上牛仔包,裝上干糧、礦泉水,我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歸來的少年”,要去尋找童年,觸摸舊時光,將內心的某些東西翻騰出來。人活到一定年齡,需要這樣的尋找和觸摸,這也算是賦予生日“各復歸其根”的哲學意義。
沿著河流行走,很多鳥叫聲不斷送來,陽光一會兒照在對面山坡突兀的石頭上,一會兒照在身邊安靜的柳樹上,沒多久又照在了河水里。水是清冽冽的,干凈透明,河底的石頭、泥土、水草全都看得見。有時候河水會撞擊河中的石頭,唱著嘩嘩的歌,形成小塊白色的布,在陽光照耀下,很是好看。河水一定是匯集了整個穿洞山山脈的精華了,我忍不住俯下身去,捧起來輕嘗一口,有絲絲甜味。
忽然想起小時候在河里游泳嬉鬧的情景,游泳在我們那里俗稱“板澡”。七八個男孩子一起“扎猛子”“露屁股”“打水仗”,耍累了,大家相互遞了眼神,光溜溜的全都懂得起。大家倏地一下跳上岸來,旁邊地里“紅癩子”家的番茄、黃瓜又遭大殃了。返回來挺著肚子又一頭扎進水里,卻發現好好的衣服不見了。“啊!”大家不約而同地叫起來,絕對是因為偷吃了人家的瓜果,遭到報復了。果然,我們看見“紅癩子”抱著一堆衣服,趾高氣揚地朝天怪笑。他并不怕我們“修理”他,因為他知道我們不敢光著身子追出來。哈哈哈!現在想起那種尷尬和無奈,真是忍俊不禁。不禁慨嘆時光易老,自己已是人生半百。如果歲月可以重來,我想我們還是要去偷吃番茄、黃瓜,那種清香味,好像還在唇邊。陽光從山梁子那邊斜射下來,被樹葉裁成碎花灑落一地,和“二丫頭”的花裙子一模一樣。
我繼續向前行走,忍不住雙手攏起嘴巴“哦哦哦——”地吼起嗓子,山谷回音,“哦哦哦——”,好像這溝里有兩個我,在互相問候。
二
或許是離開老家太久了,我不知道哪次的離開才是真正的離開。
但我記得我婆離開老家,是因為國家“農轉非”政策。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農民轉為城市戶口即所謂“國家人”,絕對是讓很多人羨慕的。我婆就是讓人羨慕的人,因為我公是國家干部,我婆可以按照國家政策遷移到縣城居住。
那次的“離別”具有空前盛大的儀式感。婆平時為人和善,是一個信佛的人,和村里大人小孩關系都處得很好,村里男女老少都來送她。大家有的站在石磨子上,有的站在石梯子上,有的從河里爬上來,手上還拎了一條活蹦亂跳的魚,紛紛招呼她,“三嫂、三嫂”喊個不停,喊了后再沒有其他語言,等會又不停喊,“三嫂、三嫂”。這種場景表達了老家人對“三嫂”的不舍、祝賀、羨慕。而“三嫂”呢,則不停地揮手,揮手再揮手。“常回家啊,常回家啊!”幺公捏著旱煙袋,帶著哭腔大聲說。我婆已是淚流滿面:“會的,會的”。我婆最終在大家不舍和羨慕的目光中,順著河流往維摩院方向走了,最后消失在凰坡嶺。我想,這一翻過凰坡嶺,她老人家就是“國家人”了。
而我離開老家的情景,則不一樣。我是村里第一個考上師范的,“進入師范門,就是國家人”,畢業就要安排工作,師范生在當時,就是“鐵飯碗”。一旦有了“鐵飯碗”,也就意味著可以和老家“劃清界限”,用我媽的話說,就“脫農皮了”“不用臉朝黃土背朝天地做莊稼了”。
村委會在我上學的頭天晚上,決定放一部電影表示祝賀。我媽為了表示回謝,提出自己出錢加映一部。這樣一來,就要放兩部電影,這就高興壞了四鄰八鄉的人。午飯過后,有人就拿著席子到竹林里面去睡午覺,準備晚上好好享受難得的“文化盛宴”,還有熱心的人迫不及待地站在山坡上,放開嗓子大吼起來,“看電影啰——”山谷回音:“看電影啰——”,聲音在溝里每一個地方回蕩。現在想來,究竟放了什么電影不知道,但我記得我穿了一件軍綠色衣服,像一個小戰士,在人群里跑來跑去。有不少人指著我說:“看看看,就是這個小孩子,他考上了學校,國家人了。”還有人對身邊的孩子說:“你們要向他學習,考上了我們也放電影。”我當時心里有一些小得意。
后來參加工作,我在鄉村小當老師,再后來到區中學當老師,再后來到縣城當老師,再后來就沒有當老師了,轉行做其他工作。變動了不少地方,雖然不算“游宦成羈旅”,但時光卻如同溝里的河水慢慢地流走了,不知不覺將我和老家推得越來越遠,不僅物理上有了距離,更有心理認同上的距離。但究竟是哪年哪月哪日呢,老家竟然變得這樣陌生了,我說不出來,只覺得往事如昨,又恍若隔世,好比房頂乳白色的炊煙,一股一股地冒出來,最終消散在空中,不見了。
三
從老家到縣城,需要經過小墳山、大墳山,然后到達穿洞山頂,再然后順著山梁子一直走,什么時候梁子消失了,縣城就基本上到了。從山下往上看,人在天際線上行走,像卡通片里的動漫人物,非常好看。但我曾經早晨不到五點就起床,打著火把去縣城上學的經歷,卻是充滿艱辛。考上縣城中學那年,我不到十四歲。中學早晨要上早自習,所以天不亮我就得出發。當時沒有電筒,而且村里就我一個人去城里讀書,我媽擔心我一個人走山路害怕,就在山下曬場中央點燃一堆火,讓在山里行走的我隨時扭頭可以看到,以便形成上下“呼應”。我打著我媽精心準備的火把,看到溝下的火堆,感覺媽就在身邊,居然沒有一絲的害怕。
從老家到縣城,如果人多,其實大家說說笑笑,感覺也是很快的。在快到縣城的時候,大家都要停下來休息一下,大人們需要點一袋煙,女人們則需要將頭發用手攏攏,梳理梳理,而我則興奮地看著城里的高樓,內心有莫名的幸福感滋生。興奮和幸福混合一起,我的表情無法描述。我媽問我哭什么呢,原來這個樣子是哭的樣子啊。媽啊,這哪兒是哭呢,我是激動啊。但我究竟在激動什么,自己卻說不出來。一個從小在山溝長大的孩子,見到了“高樓林立”,聽到了汽車鳴叫,理想和現實碰撞起來,內心就產生了夢想的火花。
穿洞溝是根據山的樣子來命名的,山頂有一個洞,遠看好像山的“獨眼”。“獨眼”的大小,其實可以讓一架小型飛機飛過去。老一輩人說,這是當年張獻忠用“牛兒大炮”給轟的,從此這個山就叫“穿洞山”了,而下面的狹長深溝,就叫做“穿洞溝”。在穿洞山變成穿洞山之前,溝里就有人居住,形成了自然村落。我只是始終不能理解,祖先們為什么會選擇這么一個地方來居住,走哪兒都遠,走哪兒都要翻山越嶺,不方便啊。他們是為了躲避戰亂,還是想圖個“清凈”呢?
溝下土地是有限的,大多數在對面高山上。一到農忙,大人們天麻麻亮就得出去,要么吃“早早飯”上山,到了山上天都沒有亮開。有時為搶農時,他們中午顧不得下山,午飯自然是我們這些小孩子送上去。記得有次“搶偏東雨”,曬場里曬滿了糧食,但大人們全都在山上忙農活,面對突如其來的“偏東雨”,他們肯定是無法趕回來收糧食的。我們這些留守在家的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沒有辦法,大家便齊齊地坐在曬場邊上,老天下大雨,我們一起大哭,無奈地、眼巴巴地看著馬上就要曬干的谷物再次被淋濕。我們淋成了落湯雞,冒雨趕回來的大人們也淋成了落湯雞。大人們看著排坐一溜的我們,哭笑不得。他們沒有抱怨我們,只是不停地抱怨天氣:這鬼天氣,這鬼天氣。
四
天氣捉弄我們沒有關系,但不能屈服。這話我記得是我媽說的。
首先不能屈服的是村里的年輕人,他們開始不安分了,紛紛計劃著要外出打工。打工是當時最流行的詞語,這一詞語關聯到廣州、深圳等沿海城市,關聯到我們聽不懂的“南腔北調”。年輕力壯的差不多都出去了,老家漸漸被掏空,人越來越少,少得只留下了老人、孩子。老家需要年輕人換回來真金白銀,也需要他們帶回來先進的發展理念。于是老家漸漸有了樓房,樓房外面貼了白色的瓷磚。陽光照在瓷磚上,樓房在溝里異常明亮耀眼,好像一幅畫的高光。有的孩子被父母接出去讀書了,聽說打工人的孩子,也可以在當地讀書,這是國家的政策。老家,便再次被掏空。
人少了,路就很少有人走。沒有人走的路,草木便要去覆蓋,去占領。曾經到縣城的山梁子,那在當時是多熱鬧啊,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路的痕跡了,那些擔挑子的、背背篼的、拖“板板車”的,全被草木隱藏起來了,消失在歷史的記憶中。
魯迅說過,世間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現在,我們既然無法順著這個山梁子“原路返回”,就只得“另謀道路”。于是大家順著河流的方向,齊心協力新建了一條道路,用水泥河沙硬化了,還可以跑農用車、小客車、摩托車。這對穿洞溝來說,絕對是盤古開天地以來的一件大事。我曾將溝里的河流比喻為臍帶,現在硬化的道路又是一條臍帶了,直接打通了溝里的“任督二脈”,給穿洞溝注入了無窮的活力。
“要想富,先修路”,這道理是簡單樸素的。道路修好后,溝里每個人都說,太方便了,躺在家里摸出手機,只打一個電話,農村客運車沒多久就上門來了,不到半個小時便可抵達縣城,這在以前是想都莫法想、夢都不能夢的。漸漸地,縣城的鍋碗瓢盆、洗滌劑、沐浴露、地板磚、席夢思床墊等運進來了,溝里的核桃、花生、蔬菜、大豆,以及杏子、李子、桃子、橘子等,又源源不斷地被小汽車拖走。“紅癩子”說,村里和城市,建立了一個農貨交換平臺。“紅癩子”和“紅癩子”的兒子,都沒有選擇出去打工,他們專心在家務農,據說他家的蔬菜水果還獲得了“有機認證”,一年可以賣上好幾萬元。我還聽說老家人也可以網上購物賣物了,京東、順風、韻達,他們都懂。互聯網正翻天覆地地改變著這個山溝。
穿洞溝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通電的,說起來在全鄉是比較晚的。電燈亮的一瞬間,整個溝里就鬧熱了,好像一鍋煮開的水,有的人還敲起盆子、點燃鞭炮,大家都說,這是溝里有人居住以來,最輝煌的一次啊,這是要記入村史的。有的老年人哭起來,咿咿的像個小孩,只流鼻涕卻沒有眼淚,村里人用這樣的方式表達內心的幸福感受。
我家是溝里第一個買電視的。電視買回來了,何家大院熱鬧得好像過年,大家白天很忙,所以都期待天黑,天黑了就可以自帶凳子來看電視,按先后順序占領位置,一直看到熒屏上出現“再見”,大家才依依不舍地離開。電視是黑白的,后來有人自作主張買回來彩色塑料紙貼在屏幕上,但由于畫面顯得極為不真實,被我媽給撕掉了。其實,最讓人提心吊膽的事情是“信號”不穩定,“麻子點點”總是一陣一陣的,但大家不急不躁,有人便幫忙制作起天線。找來幾根大鐵絲綁在竹竿上,外觀很像風箏的骨架。很多人高舉竹竿,“風箏”在院子里鬼鬼祟祟地走來走去,有時候還跑到山坡上去了,尋找著空氣中縹緲不定的信號。現在想來,當年放過的好多電視劇都還記得,比如《霍元甲》《陳真》《追妻三人行》等。還有一些廣告詞,比如“月兒明,月兒亮,月光照在酒瓶上……”大家都可以背誦了。但尋找信號的過程卻是充滿樂趣,最難忘懷的。
五
草木情深義重地覆蓋在山上,也沉浸在河水里,水流聲和鳥鳴聲此起彼伏。硬化了的公路確實比較好走,兩邊青山綠意盎然,山坡上麥子使勁地抽著穗,穿洞溝中國畫一般歡迎著我。山村現在的生活多美好啊,我長舒一口氣。這就是我的老家,我曾經千方百計想要離開的地方。而現在,我是多么愿意回來,在小河里去“板澡”,去偷吃人家的番茄、黃瓜,去和大家一起看黑白電視,就算信號不好也沒有關系啊。當初離開老家的幸福,是揚帆起航,天高任鳥飛,那么現在呢,現在是歷經滄海,閱盡千帆歸來。布谷鳥大聲唱著,“布谷——布谷——”,“聽杜宇聲聲,勸人不如歸去”。現在,距離我的何家大院已經不足百米了,“鄉關”就在眼前,我又回到了我人生起航的地方。人生就是這樣,最初和最后都會聯結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不斷盤旋上升,不斷上升又盤旋的環。
不知不覺走到村委會門口了,一根瘦高的電桿上,掛了三個高音喇叭,分別朝著三個不同的方向。喇叭嘹亮地唱著歌,歌曲是劉德華的《今天》,歌詞意味深長,曲子振奮人心。但劉德華沒唱多久就停了,喇叭里那個人清了清嗓子,講起了鄉村振興,之后又講起森林防火、秸稈禁燒。講話的人事先準備了稿子,但很多話都是重復的,像是在強調,怕別人聽不懂,記不住。
河流和道路在村委會門口交匯了。河流和道路一旦交匯,便有了橋。站在橋上,看著河水緩緩流動,好像那些正在逝去的光陰,一去不復返。抬頭看了看穿洞山,太陽剛好靠在山頂,似乎伸手可以觸摸,太陽很大很圓,卻像是被磕出了很多鮮紅的血,涂抹了溝里的天空、草木、河流、房屋。我迎著這初夏的夕陽站立橋上,影子被拉得老長老長,長到了河那邊的田里了,樣子好像恐龍特級克塞號中的機器人,展示了無窮力量。四處望望,村里又新建了不少時髦的房子,也有人叫別墅。外出務工的人,基本上都回來修了小洋樓,似乎有攀比之意。很多舊房子也進行了維修整治,整個穿洞溝村,清清爽爽,有滋有味,儼然一幅濃墨重彩的山居圖畫。
田里有人開著耕地機,來來回回平整土地。溝里的土地大部分都流轉給了承包業主,實行了統一標準的種植模式,主導產業是有機糧油、時令蔬菜,產品專為縣城某些單位、超市生產。山那邊是馬槽溝,正加足馬力推進臨江新區的工業園區建設。按照建設規劃,將會從凰坡嶺前面不遠的地方,鉆通一個隧洞,將馬槽溝和穿洞溝連在一起,這樣,老家人到縣城的惜字塔公園,只有不到十分鐘車程了。柑橘園和溝上灣的堰塘,也承包了出去,由一個愛說“有哪句說哪句”口頭禪的人負責管理。
一群孩子在公路上嬉笑奔跑,有幾個中年人看到了我,多遠就揮手招呼。老家人依然很熱情,真誠發自內心,就是純粹的、自然的。帶了點歲數的人招呼著我的小名,但那些嬉鬧的孩子我卻一個也不認識,他們都笑著問我是從哪兒來的,要找誰,正應了賀知章當年的尷尬:“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我一一和他們微笑點頭,伸出手摸摸這個,又看看那個。距離遠點的我就大聲招呼,喊著他們的輩分稱呼或者名字,歡樂的聲音在溝里回蕩,這樣的親熱讓我幸福無比。
我終于又回到老家了。
【作者簡介】
何源勝,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散文集《火把照亮的歲月》,曾獲第四屆四川散文獎優秀獎、第二屆南充散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