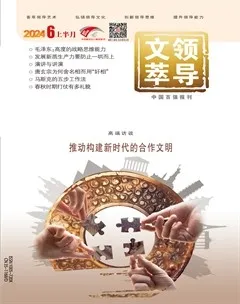楊士奇:具有高超溝通藝術的四朝重臣
陳柏清
楊士奇是吉安府泰和縣(今屬江西)人,曾經輔佐明惠帝、成祖、仁宗、宣宗四代君王,史書稱他舉止恭謹,擅長應對,建言朝政,常常一語中的,深得君心。楊士奇一生宦海沉浮,身為四朝重臣,其高超的溝通藝術備受贊譽。
善于機變,不墨守成規
廣東布政使徐奇統領西南時,贈當地特產與內廷官員,有人將饋贈名單呈給皇帝。明成祖看其中無楊士奇名字,于是召見楊詢問。他回答道:“徐奇奔赴廣東的時候,群臣作詩文贈行,當時恰逢我得病未有參與,所以唯獨沒有我的名字。如果我當時無病,是否有我的名字也未知。況且贈禮都是小東西,應當沒有其他意思。”明成祖于是下令燒毀了那份名單。
這件事情按照常理,既然接受禮物名單沒有自己,楊士奇應該沾沾自喜,甚至有批評他人的機會。但是楊士奇沒有這樣做。他很客觀地告訴皇上自己只是因病沒有參與。言外之意,如果不是特殊情況,自己也可能是名單上的人。然后接著告訴皇上,都是小禮物,不至于造成什么太大的影響。楊士奇這樣做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先站在一個客觀的立場談論這件事,然后又委婉地勸皇上,法不責眾;況且都是小禮物,不必小題大做,節外生枝。這樣既使眾臣感恩自己,增加了威望,又保持了朝廷的穩定。
說不說,說多少,恰如其分
楊士奇的溝通藝術高超,說與不說,說到什么程度,拎得清楚。永樂十四年(1416),朱棣返回京師,稍微聽聞了漢王奪嫡的打算以及其他不軌行徑,于是問蹇義這些事情。蹇義沒有回答,便又去問楊士奇。楊士奇對答道:“臣與蹇義都是侍奉東宮的,其他外人不敢對我倆談論漢王的事情。但是皇上兩次派遣其就藩,都不肯赴任。現在知道陛下要遷都,馬上就請留守南京。這些請陛下仔細考察他的本意。”朱棣聽聞后默然不語,之后起身還宮。過了幾天之后,朱棣了解了所有事情,于是削漢王的兩個護衛營,并安置其到樂安。
在漢王奪嫡這件事,之所以蹇義不回答,是因為做臣子的討論皇帝家事不合適,也沒那個膽量,不回答,又讓皇帝覺得缺乏諍臣的果敢。但是這件事到了楊士奇這里,就變成小菜一碟了。他以實據實地回答皇上,為什么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問題不在自己,是別人不給他們消息源;又說了自己見到的,但沒有說結論,因為結論要皇上自己拿,做臣子的有義務實話實說所聞所見。最后朱棣做出了選擇,而楊士奇既做了諍臣,又避免了直接參與皇帝家事的禍患。不可謂不高明。
敢于直言,毫不含糊
楊士奇高超的溝通藝術還表現在,不含糊、敢直言,深諳有理走遍天下的道理。明仁宗即位后,楊士奇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明仁宗在內閣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老遠望見楊士奇,于是對兩人說:“新上任的華蓋殿大學士來了,必定有正直之言,我們不妨都聽一下。”楊士奇進言道:“皇上兩日前剛下詔減免了歲供,可惜薪司又征棗八十萬斤,這與前詔相矛盾吧!”明仁宗于是馬上下令減免一半。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對于皇上的工作失誤,許多臣子看得見,但有勇氣說的不多。為什么楊士奇敢說?因為楊士奇深諳皇上也喜歡忠臣,涉及國家社稷的事情,明擺著的道理,皇上還是聽從諫言的。所以他敢于直言不諱。這種逆鱗而諫,需要慧眼識別事情真偽,更需要直言的勇氣,令人信服。
據理力爭,不打不相識
高超的溝通藝術是不是就意味著一片和諧?也未必見得。明成祖朱棣剛駕崩,明仁宗朱高熾服制二十七日期滿,大臣呂震上疏請仁宗穿吉服。楊士奇則稱不可,呂震隨即高聲厲叱楊士奇,蹇義見此,兼顧兩人觀點進言。次日,仁宗仍然戴素冠穿麻衣上朝,而廷臣中只有楊士奇與英國公張輔仍然服制如初。罷朝后,明仁宗對兩旁人說:“父親(指成祖)棺木仍然在停柩,我又怎能忍心易服,楊士奇所做的是對的。”之后,明仁宗晉升楊士奇為少保。
明成祖去世后,為什么勸仁宗穿吉服的呂震沒有得到升遷,反而是提倡穿素服的楊士奇?正常來說剛剛登基的皇上肯定都想穿得喜慶一點,隆重一點。這是因為楊士奇的提議符合皇上想向天下人表明自己孝道的心理,也符合禮法,所以此刻的楊士奇不但沒有因為反對皇上穿吉服而得罪皇上,反而得到升遷。不但占領了道德高地,還得到了實際利益。
楊士奇能夠一直得到重用, 與他本身的能力和才華分不開,但更得益于他高超的溝通藝術。無論是上對皇上獻言,中為同僚分憂,下為百姓諫諍,都入情入理。當然,他高超的溝通藝術背后是其高尚的人格。
(摘自《演講與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