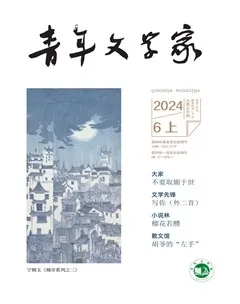一碗麻湯飯
張彩霞


“麻湯飯和小蒜,老婆吃了打老漢!”這是一句流傳于陜北黃土高原的民間俗語。1960年,爺爺帶著全家一路向西。當他們走到猶如“世外桃源”的薩拉烏蘇河畔時,被這里的藍天、白云、沙地、峽谷、草原、牧場,以及清澈的河水、多彩的濕地所吸引。這是個美麗富饒之地,爺爺當即決定放下行囊在此謀生。當然,其中的艱險可想而知。
后來,證明爺爺的決斷非常明智。被稱為“塞外小江南”的無定河流域確實是個魚米之鄉,雖然那時沒有像歌里唱得那么夸張,稻谷飄香,牛羊成群,魚鴨歡騰,但從我記事兒起,從來沒餓過肚子。記憶中,玉米、饅頭、青稞面饅頭倒是經常吃,但因為母親的廚藝好,做得一手好飯菜,就是吃玉米、青稞面饅頭,也沒感覺到多難吃。不過,母親做的最好吃的飯食是麻湯飯。
麻湯飯是我們全家冬日里翹首以盼的美食,在那天寒地凍、北風呼嘯的漫長冬日里,一家人最美的享受就是圍坐在暖烘烘的火爐旁吃上一碗熱氣騰騰、滿口濃香的麻湯飯。在我童年時期的鄉村,母親的勤勞和巧手有口皆碑。原因有二:其一,母親的女紅全村第一,她做的鞋不但穿在腳上舒適,而且美觀大方。母親有一本厚厚的書,里面夾著好多鞋樣,村子里做鞋的婦女經常向母親借鞋樣。她們雖然有了鞋樣子,但做的鞋還是沒有母親做的鞋秀氣、美觀。特別是給女孩子做的繡花鞋,或者給男娃做的虎頭鞋,母親的手藝都是一流的。于是,有些人家就拿了布料央求母親給她們做。不要說,母親做的繡花鞋,那鞋上的花兒活靈活現,好像真的花兒一樣。我的姐姐小時候穿母親做的繡花鞋可艷羨了不少村子里的女孩子。母親給男孩子做的虎頭鞋也是村子里的搶手貨,村子里不少男孩子小時候可沒少穿母親做的虎頭鞋。母親做的虎頭鞋最漂亮,不但鞋幫針腳工整,樣子美觀,而且母親納的鞋底也與眾不同—她會納雙龍戲珠、麥穗、荷花等不同圖案的鞋底。穿著那樣的鞋子走過沙灘、土路,滿地都像一幅幅簡筆畫,煞是好看,人們看到路面上各種各樣圖案的腳印都知道那是母親的杰作。
其二,母親的廚藝好,無論我們想吃什么,都會經她的巧手烹制得色香味俱全。記憶里的麻湯飯就是母親的拿手美食。那飯做得實在是太香了。現在想起來口水都會不由得流下來。我們幾個饞貓更是不識饑飽,吃了一碗又一碗,個個吃得肚子滾圓似鍋,難以坐臥。吃飽了就不想動,犯瞌睡。不一會兒,我們就昏昏沉沉地睡著了,一睡著就醒不來。聽母親說,有一次我們吃了麻湯飯,愣是睡了兩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傍晚被尿憋醒了,才勉強爬起來。現在想來,估計是麻油吃得太多了,是麻油中毒的表現吧!
麻湯飯最主要的是麻湯,顧名思義就是麻子熬制的湯。那時候,我們家每年都會種一片麻子,秋天就會打五六斗麻籽。麻籽又稱火麻籽,是大麻的果實,麻籽大小似高粱粒(比綠豆小一些),灰不溜秋的。麻稈的皮舊時可織布制衣,稱麻衣;可搓繩,叫麻繩。母親就是用它來給我們納鞋底的。
那個年代物資匱乏,不像現在的小孩子能吃到各種各樣的零食。漫長的冬日里我們會央求母親給我們炒麻子,炒熟了的麻子特別香。我現在還依稀記得母親給我們炒麻子的情景,也是這樣一個冬天的上午,一縷陽光從廚房里照射進來,母親開始給我們炒麻子。大鐵鍋燒得通紅,一粒粒麻子就像一個個調皮的孩子蹦蹦跳跳地涌進大鐵鍋,母親一邊給灶火里添柴火,一邊用鐵鏟快速地翻炒著,等到炒出香味,就將調制好的咸鹽花椒水澆在麻子上。此時,柴火香、麻子香將屋里的氣味發酵得熏香而又醉人。待鍋里的水汽蒸干,麻子就炒好了。我們幾個早已按捺不住,等不得麻子冷卻就急吼吼地往自己的口袋里裝。大人們則不讓我們多吃,怕連皮吃了不好消化,但哪能管住一群孩子的手。我每次都會裝上一口袋,避開大人偷偷地吃,把麻子放進嘴里,牙齒輕咬,舌頭卷動,舔出內瓤,吐出外皮,靈活自如。每一次咀嚼,清香洋溢在嘴里,也氤氳在空氣里,讓我陶醉,讓我癡迷。
不過,我們家里的大多麻子是用來榨油的。那些年,都是手工榨油。榨出的麻油我們這里叫青油,因為油的顏色發青綠色。將麻子在大鍋里炒熟,再倒進磨眼里,套上小毛驢拉磨,一會兒,麻子就被磨成了油泥,再將油泥鏟到盆里。待所有麻子磨成油泥,母親就將大盆里的油泥倒入大鐵鍋里倒上水熬制。熬制的時間比較長,記憶里都是從中午開始,一直熬到掌燈時分,母親才停火。等到第二天清晨,一鍋綠汪汪的油花才漸漸漂浮上來。母親細心地將油花收集,再倒進鍋里精煉,基本沒有水分了,清香的自制青油就算做好了。炸年糕、炸丸子、炒菜,就靠它來調味了,彌足珍貴。
油渣沉在鍋底,上面呈乳白色,其中帶有絲絲綠色的漿水,這就是所謂的麻湯了。因為長時間熬煮,麻湯自帶透香的油香。母親是個會過日子的女人,農村人過日子就是過女人,誰家的日子過得熱氣騰騰,那家的女人肯定差不了。精打細算的母親舍不得把那透香的麻湯倒掉。在麻湯里兌入適量的水燒開,加入高粱米、小米、豌豆瓣、豇豆,中火熬制,等到熬至濃稠時,再加入白菜、鹽、辣椒粉、花椒粉。母親比別家麻湯飯做得好吃的秘訣就是,母親還會加入幾味至關重要的調味料:一個是澤蒙,另一個就是小蒜。小蒜又叫野蒜,我們這里叫野蔥,多生長在初春和初秋時節的硬梁土峁上。野蔥的葉子形狀如韭菜,略顯細小;根莖形狀酷似蒜頭,但是極小,其味似蔥似蒜,味道沖鼻,故被人們稱為小蒜。母親從野外挖來小蒜,洗凈切碎后,拌入鮮辣椒丁、胡蘿卜丁、食鹽等腌制后,作為作料來食用。小蒜特別適合拌面吃,其味道濃烈醇香,刺激食欲,很受鄉里人的喜愛。當地有一句贊譽小蒜的俗語:“二八月的小蒜,香死老漢。”
如此搭配,任誰都會想到母親做的這道麻湯飯就小蒜的味道是多么美味!小蒜就是大自然賜予的精品點綴。熱油燒至七成澆入,整個屋子里立刻奇香四溢。每每這時,我們幾個饞嘴貓就被這香味吸引到了鍋邊,像一群雛燕一樣,張著嘴嘰嘰喳喳地說著話,你推我,我推你,手里捧著飯缽子嚷嚷著讓母親給舀一碗。不過,母親才不嬌慣我們這種壞毛病:“每人都給我端端正正地坐到炕桌邊去,還沒了規矩了。”我們幾個只能悻悻地坐回到炕桌邊,不斷吞咽著口水,焦急地看著母親不慌不忙地收拾著鍋臺上的瓶瓶罐罐,不緊不慢地將麻湯飯端上桌,末了還不忘給我們上一盤洋曼莖咸菜疙瘩。每次我們幾人都很難保持母親教育的那樣,坐有坐相,吃有吃相。等到母親在每人碗里都盛上滿滿一碗麻湯飯時,我們幾個就像餓虎撲食一樣吃起來,也顧不得滾燙的飯燙著嗓子,大口吞咽著,嘴里發出響亮的吧唧聲,那吃相估計難看到了極點。
現在想來,麻湯飯與小蒜味道互補、渾然天成,吃起來味道奇香,余味無窮。我們幾個吃得撐破肚子也是情有可原。怪不得那句俗語叫“麻湯飯和小蒜,老婆吃了打老漢”,大概意思是老婆沒吃夠,讓老漢再給添吧!
其實,麻湯飯讓我念念不忘的原因,是母親樂善好施與人為善的感人行為一直溫暖著我、教導著我。
記得那是一個冬日的中午。因為接連下了幾場雪,天異常寒冷。即使到了正午時分,太陽依然躲在厚厚的云層里,天灰蒙蒙的,北風呼呼地叫著,偶有零星的雪粒子落下來,天地一派蕭索冰冷的景象。我們全家因為外面太冷都圍坐在火爐旁邊聽父親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講故事,《牛郎織女》《連升三級》《楊家將》,講了一個又一個,我們聽得分外專注,都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中。不知過了多久,我們的肚子開始咕咕地叫。一上午也沒顧得注意母親,只聽姐說母親上午喂完豬就去鄰居家給我們做棉鞋了,說是劉大拿老婆從娘家帶來了新款鞋樣。此時,我們肚子餓了,就開始尋找母親。這時,一股濃香從廚房傳來,這是我們最熟悉的味道—麻湯飯的味道。家里的麻湯早吃完了,母親是從哪弄來的麻湯?難不成巧手的母親會變戲法?尋著香味我們跑到廚房,只聞到廚房里香氣彌漫,透過水汽,我看到母親正在完成麻湯飯的最后一道工序—油潑小蒜和澤蒙花。只聽滋啦一聲,一股異香立馬竄入鼻孔。我們歡快地問著母親:“哪來的麻湯?”母親說是劉大拿老婆送的。母親歷來與鄰居相處和睦,互換食物的事情經常發生,我們不足為怪。開飯了,我們歡快地擺著碗筷,撈了盆咸菜疙瘩端上桌。
就在這時,門開了,走進來一個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老人。我一眼就認出了這個人,這是經常在村里討飯的乞丐—何處興。因為這人太邋遢了,身上又臟又臭,我們小孩子遠遠見了,都會對著他扔石頭,吐口水。這可怎么好,叫我們怎能吃得下。我看到那人顫顫巍巍地走進來,臉上帶著卑微的微笑。我第一反應就是趕緊將飯桌上的麻湯飯往后屋端,當即決定在里屋炕桌上吃。正當我端著一盆飯往里屋走時,母親從廚房里走了出來,看見眼前的場景明白了八九分。母親厲聲喝住了我:“端到圓桌上去。”我還是沒有回轉的意思,固執地往里屋走,擠眉弄眼地示意母親,家里來了埋汰人飯不能在客廳的圓桌上吃。母親對我的暗示視而不見,迎過來一把奪過我手中的飯盆。然后,母親快步走到客廳放在圓桌上,大聲地招呼著何處興:“何大叔您老好福氣!”轉身又對我說道,“快給你何爺爺打盆水,讓他洗洗手過來吃飯。”
我站著不動,母親又回過頭剜了我兩眼,我才不情愿地給他倒水。老漢沒想到母親會這么熱情,感動得連連擺手說:“不用了,不用了,你們吃,我不餓。”
母親說:“何叔,快去洗吧!哪有不吃的道理,再說我們今天吃的是稀罕飯,您老嘗嘗好吃不?”
老漢的臉上立刻露出欣喜的表情,嘴上不住地說:“好吃!好吃!我老遠就聞著香味了,我是尋著香味來的。”說著,腳步利索地來到洗臉架子旁,開始洗手。我站在不遠處看到這個乞丐的鞋已經破得不成樣子了,整個鞋子好像一張魚嘴,四個腳趾頭幾乎全都露在了外面。看到我在看他的腳,老漢尷尬地把腳往回縮,想把腳藏起來。可是,一雙腳又能藏到哪里去呢?老漢只能又討好地看著我,尷尬地笑著。我厭惡地將頭扭向一邊。
何處興洗完手,被母親請上了餐桌,母親給他滿滿地盛了一大碗麻湯飯。他顯然餓壞了,大口地吃著,還不時嘟囔一句:“好吃!好吃!真好吃!”我們幾人反而沒了食欲,緩慢地將飯送入嘴里,眼睛卻一刻不停地盯著何處興。我從小就有潔癖,實在是沒法兒和這樣一個臟兮兮的人同桌吃飯,就舀了一碗跑到里屋去吃了。等到我吃完一碗再回到客廳時,盆里的飯已經見底了。哥哥給我伸出五根指頭,轉而又指了指何處興,我立刻秒懂了,這個乞丐一口氣吃下了五碗麻湯飯。此時,他顯然是吃飽了,滿足地打著飽嗝。
飯后,我們幾人原本以為那個乞丐這下該走了吧!沒想到,當母親看到他露著腳趾的鞋子時,又生出憐憫之心,硬是讓他將破鞋脫掉,從里屋的柜子里找來一雙嶄新的棉鞋遞給他,還一個勁兒地讓他穿上試試。此時的何處興顯然非常感動,只見他的嘴唇輕微地抖動著,干癟的眼眶里閃著點點淚光。“好人啊,大好人呢!您的大恩大德叫我怎么回報!”他反復說著這些話。
我記得,何處興在我們家住了好些日子,母親給他從里到外換了一身行頭,還給他理了發。等他的侄子來尋他回去過年時(他無兒無女,據他說,平時靠討吃要飯過活),都有些認不得他了。何處興走后,我們幾個對母親如此對待一個乞丐很是不理解,都七嘴八舌地數落著母親,笑話母親對那個人就像對待自己的親爹親娘一樣,有什么用呢!他都落魄成那樣了,會給你什么好處。母親聽了十分生氣,很嚴厲地批評了我們。她說:“看他多可憐,無兒無女的,做人要有愛心。想當年,我和你們外公外婆逃荒到這里來時,要不是村里這些厚道、善良、樸實的鄉里鄉親,我們怕早餓死了。人到難處拉一把,強似修廟蓋塔。咱們少吃一口飯,少穿一雙鞋,什么都少不了,可是對于那些可憐的人也許就能救他一命。學校天天教育你們學雷鋒做好事,看來都白學了。”聽了母親的話,我們幾個都羞愧地低下了頭,深刻地體會到了母親是天下最善良的人。母親樸實的人生哲理像一盞指路明燈照耀著我們,更像潤物細無聲的春雨滋潤著我們。
汪曾祺曾說:“四方食事,不過一碗人間煙火。”母親做的這碗麻湯飯里,蘊含著愛,蘊含著慰藉,蘊含著善良,蘊含著人世間最真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