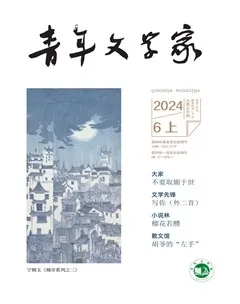放逐
胡家英
周末,我和娟帶著各自的七歲兒子,至大寺森林公園游玩。娟說大寺游人多,旁邊的小寺別有情趣,值得一去。
行至大寺森林公園景區處右拐,進入一條小路。路旁有一道極淺的小溪曲折迂回,溪上有一座低矮的石橋,溪水從石橋上漫過,從錯雜的石縫里涌出,被石頭凸起的棱角修成一條條玉掛,泠泠作響。水簾下面匯集成一個小水池,幾只白鴨在戲水。看來,大山深處也有人家,此處并非世外桃源。
一米高的瀑布,三米寬的水潭,實在難以稱得上勝景。鳥鳴聲傳來,如雨落塵埃,似風拂山岡,額頭皺紋頓平。“時時聞鳥語,處處是泉聲。”風景要去感受,才可以引發思考、領悟,從而愉悅。實際上,我眼前的瀑布與李白看到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不過是幾十米的差距。眼前的潭水與散文家筆下“仿佛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著”的潭水比起來也毫不遜色。戲水的白鴨與鷗鷺同為鳥類,并無貴賤之分。若能極盡夸張,霞思云想,何處不是勝景?
小路兩旁長滿各種樹,叫得出名字的和叫不出名字的,隨意生長。樹木干曲枝虬,胖瘦高矮,各具形態,像初學毛筆字的稚子拿出全身力氣畫出的豎。樹葉染上秋意,或深或淺的黃與紅,在綠的底色上任意暈染,鋪陳季節轉換的華章。秋陽不燥,把斑駁的樹影印在滿地黃葉上,把光與影的織錦披在我們身上。落葉的綿軟沿腳底流向全身脈絡,撿一片在手,撫摸生命輪回的痕跡,秋與我有了具象的聯結。
我們追隨溪水,溯流而上。小溪懷抱樹影,躺在鋪著藍天白云的床上,慵懶地曬著太陽。水落石出,高高低低的鵝卵石沿著小溪排開,消失在山坡的另一邊。青苔蓋上鵝卵石,鋪滿溪岸,蔓延至樹下,直到占領樹干,入侵至兩旁的坡地。整個河谷在朦朧的綠意中,心也被染上了綠色,沉靜下來。混著泥土氣息的花草香醉了身心,不再追求或磅礴,或綺麗,或婉約的詩意,只隨意走著,看著,聽著,嗅著。
行至一處稍大些的水洼,一群水拖車瞬間漂移,擾了水的美夢,水面抖動起一層皺紋,俄而平靜。一只翠色的螳螂,胖胖的,伏在一塊大石頭上,我看著它,它看著水中的自己。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好久不動,是在回顧夏日的輝煌,還是在恐懼即將到來的寒冬?抑或在享受這刻暖陽下的悠閑?我無從得知。一旁開著紫花的益母草上,停著兩只黑色的蝴蝶,它們對我的拍照不屑一顧,立在小小的花上,輕輕踩住時間,在它們小小的世界里繼續寂寞,繼續獨立,繼續相伴。
它們是閑適、安然,或是哀嘆、孤寂,只不過是我給它們的預設,我無法走進它們的世界,如同它們也無法理解我們為何飽食終日依然傷春悲秋。我在石頭上坐下來,和螳螂、蝴蝶一起發呆,任時間靜靜地在身旁流淌。溪水清亮、晶瑩、秀美、澄澈,水底的砂石干干凈凈,連魚蝦都嫌無趣,不肯屈就。青色的天臥在水底,樹影壓不住散漫的薄云,索性放縱它任意西東。四周秋蟲啁啾,不知是喜是悲,抑或無悲無喜,只在證明生命如滄海一粟,卻真實存在著。我們“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不預設將來,不留戀過往。終將與這溪水有一樣的歸宿,融于蒼穹,寂寞空曠,復歸于無。
孩子們的嬉笑聲傳來,方覺我們是真實的,天地是真實的。以不變的觀點看,萬物與我皆是這天地間的永恒。“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慢下來,享受這秋日的美好時光吧!我和娟沿著小路繼續向前,我們踏著黃葉靜靜走著,不說話。最舒服的關系,是我在你身旁,就好。孩子們被一只散步的小黑羊吸引,一個臉蛋兒黑紅的村童被孩子們吸引。路旁松林下,一群農民在種當地特產黑松茸。林間的鳥雀蹦蹦跳跳、嘰嘰喳喳,過著它們的小日子,一只柴犬斜看我們一眼,晃晃尾巴,繼續曬太陽。
無須夸張,無須想象,只有自由,只有真實,把我的心放在這里治愈。山也好,水也好,人也好,心靈的疲憊和壓力經過放逐,消散在小寺這片天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