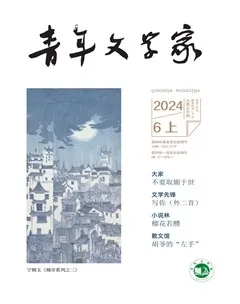寫給父親(外二首)
閆桂娥
冬至前夜的一場狂風
裹挾了您的身影
我頂著風雪追出十幾里
父親還是沒能躲過料峭的寒冬
那天的夜? 像棺槨一樣沉重
天上沒有一顆星星
我點起一支支陪我流淚的燭燈
天空哭了
淚水潑灑在無盡的天穹
冷風抬遠我聲嘶力竭的哭聲
任風的手指來回撥動
讓我的夢境
永遠纏繞著您的戎馬倥傯
還有窗外那黃葉
一片一片悲切地飄零
故鄉的水土和飆風
喚起十五歲青年的覺醒
您的腳步踏過歲月的泥濘
向著太行山一步步攀登
車站夭折? 流水無蹤
浴血的戰場正響著槍聲和炮聲
十幾枚軍功章啊
記錄著您曾經的從軍歷程
部隊首長發現您手巧心靈
您十八歲時
被調到軍械所
您用青春和精明
擰成一股結實的韁繩
在擺滿槍支彈藥的孔孔窯洞
精心修造? 晝夜拼命
您用槍口和準星
喚醒山谷的黎明
您用閃亮的刺刀
提醒一度迷惘的人們
在當年的黃崖洞保衛戰中
與敵人斗智斗勇正面交鋒
黃崖洞軍械所的那盞燈
至今還燈火通明
您當年的故事
就像漫山遍野的楓葉啊
散發著詩行的癡情
一句一句填滿窯洞的裂縫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軍工
您脫下軍裝
去完成工學院全部的課程
跟隨黨的號角
莊嚴而神圣地開進河北的省城
記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國際形勢變幻莫測
您已觸摸到
邊陲夜空的那片朦朧
篤定烏云定會在天空倒下洶涌
您主動請纓
二次重返太行
籌建新的三線軍工
靠山隱蔽的軍工廠
林中的雪花掩蓋了樓層
一片雪壓著一片雪
一道冰蓋著一道冰
山里的冷風一口口啃著無盡的冰凌
您用不再粗壯的雙臂
推開大山的隆冬
您用經驗和教訓
逼迫困難發出斷裂的悲鳴
您的掌心緊握計量的余溫
收割著檢驗工具革新成功的春風
幾十年過去了
工廠已搬出大山
但至今單位仍沿用著
您創建的計量方式和標準
軍械部領導親自為您頒獎
前沿陣地的風景
曾因您而生動
父親? 我知道
因為我下鄉插隊
一度留給您一道深深淺淺的印痕
此刻? 不知道您會不會
在我無聲的文字里蘇醒
聽我在沙沙的落筆聲中
書寫您到一中為我送飯的情景
清明的雨下個不停
隱隱捎著縷縷凄情
巍巍太行又刮起陣陣狂風
我好像聽見父您那悲壯的歌聲
“我們在太行山上……”
我又一次潸然淚下
只為悼念天國的您
我的父親
淚水洇濕昨日的情書
初秋的風劃過陡峭的山巒
落在此起彼伏的深谷
它銜著一封遠方的情書
霎時
溫暖了那年大山的深處
至今我還記得
那散落在秋風里的愛慕
在他的筆下涓涓流出
照片上那雙清澈的眼眸
流淌著無限的純樸
此時? 她如同林中的那只小鹿
飛越一切障礙
奔向心中向往的幸福
葉子出走的那天上午
山谷曉風擠在送行的隊伍
它們扇動著年輕的翅膀
眼神流著粉紅色的情愫
她有著優雅的舉止和談吐
纖細的脖頸兒與白皙的鎖骨
就像冬天的暖陽
夏日的清風
那不食人間煙火的清冷
真稱得上人間尤物
葉子追隨秋風的音律且行且舞
走了很遠很遠的路
他始終認真駕著小舟
搖著手中的擼
終于在一個叫晉陽的城市停下腳步
青春就是一本倉促的書
轉眼? 他們攜手二十幾個春秋
她執一支瘦筆寫著風花雪月的詩
做著賢良淑德他人的婦
一首首纏綿的詩行在筆下流出
時不時飄在省級報紙和刊物
記得那兩年兒子讀高中
他們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陪讀
在那些漫長的隆冬夜晚
她如同水和冰縫在一起
認真陪伴兒子伏案溫書
她的床頭也放著一摞摞的書
還是時不時豎起耳朵
聽兒子筆落紙上
如細細蟲鳴嚙咬著寂靜的夜空
她稱這是他們童話中的小屋
自從他仕途未卜當起顧問
衣著開始講究? 談吐越發粗魯
從此? 小屋開始揚起塵土
秋就像一瓶墨汁
越來越讓葉子看不清楚
那年的秋非常寒冷
飄忽的黃葉就像樹上流下的淚珠
冷風一口口啃著歲月的骨頭
她把無人言說的痛深藏心底
陪著兒子堅定地守在出租屋
信念就似鐵軌般駛向既定的藍圖
記得來年一個春日的下午
他們一起回到自己家的住處
在空曠的庭院栽下一棵石榴樹
幾枚鮮艷的花骨朵兒還掛著盈盈雨珠
他突然雙眉緊皺? 似三秋的迷霧
“我還差一棵海棠……”
葉子沒有開口
蕭瑟的秋風一只大手狠狠鉗住
葉子的下頜骨
秋風趁著夜色
在墻上鑿了一個洞
消失在深秋的夜幕
他的雙眼像閃著蠟燭
終于掙脫了小屋的束縛
風急促地吹向江南
卻在一棵草芥前駐足
野草扭著低俗的腰肢
向風吐著縹緲煙霧
慶幸自己捕捉到了蟲獸中的鴻儒
他似被下了蠱
很快飄忽了回家的腳步
我看見那高懸天際的明月
被風毀得體無完膚
白晝的星辰
被風化捏成冰柱
出租屋不再是溫暖的童話小屋
她把冰塊含在嘴里
繼續寫著溫暖的詩
城郭依舊
小屋依舊
張愛玲的“蚊子血”“白玫瑰”經典依舊
秋風依然嫌棄成熟的稻谷
腰肢沒有彎到他要求的弧度
那化不開的傾訴
似冰錐刺向她的心谷
那散落在秋雨里的淚
終于洇濕三十年前那封山谷情書
他們都在等待日出
但再也曬不干那封被淚水洇濕的情書
多年后
她還在詩行里質疑愛情的虛無
還記得那棵掛滿花蕾的石榴樹
呼嘯的秋風在睡夢里
又劃過那條深深的峽谷
夢里明月伴海棠
太陽的影子躺在校園的海棠
把溫暖灑向那條悠長的小徑上
我似一只懶散的小鹿
坐在印著斑駁樹影的石凳上
沉浸于雷抒雁新寫的詩章
他向長廊走來
一副風景無限的青春模樣
他說弱不禁風的女生筆落黑板
淌出流淚的詩行
卻把殘留的粉筆頭甩向教室的南墻
也濺潑到我心底最柔軟的地方
那是1968年初春的早上
一位十八歲青澀懵懂的大男孩
在海棠樹下表白
此時? 沒有人能阻擋玫瑰綻放
一年后
命運暫時關上我們求學的門
卻打開那扇廣闊田野的窗
而他參軍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
分別那天
月光在海棠樹上溫柔地搖晃
他的雙眼閃著明月般的光芒
月光糾纏著我稚拙的手指
惹得雙眼流出一串串滾燙
轉眼? 鴻雁傳書三年以上
詩就像天上彎曲的風
我摘一行放在風的翅膀
詩和遠方真的很有分量
我把一畝一畝的思念
一頃一頃的斷腸
一起掖進信封寄向他的營房
有一種甜蜜的苦叫相思
我把它潑灑在生產隊的棉田上
把東張西望的棉朵
以掃蕩的速度收進自己飽滿的布囊
當夜幕撕破田野的滾燙
我登上屋頂
向著遠方張望
田野的月亮似乎缺了氧
慢吞吞爬上知青的房梁
再沒有李白筆下的那種輕狂
時光荏苒? 跌跌撞撞
我堅強地挺過一次次考驗和風浪
偶爾也會像一片草葉
失落地被風吹向村口那棵棗樹上
月亮從遙遠的地方
不聲不響爬上我的房梁
潛入我的夢鄉
恍惚間
我在用筆尖流淌著憂傷
夢里捕他入詩行
我用女人最好的年華等他
幾年后參加了高考
離開青春蕩漾的村莊
誰說疼痛沒有重量
它一次次壓痛我的心房
我把疼痛揉搓成末
放在海棠花里收藏
月光把我深情的詩歌積攢起來
移到編輯部主編的書桌上
突然? 邊境傳來凜冽的槍響
槍聲直接撞擊到我的心臟
夢里? 我們并肩上戰場
我相信他會像奧德修斯一樣
浴血在自衛反擊戰的沙場
一年又一年春日的陽光
灑在校園的海棠
一年又一年十五的月亮
圓了又缺? 缺了又圓
他卻像失蹤了一樣
不知是誰說
海棠的花期并不長
歲月是它致命的傷
海棠哭了
用一種叫淚的水
開始澆灌自己那個叫“心”的地方
我曾一次次將書信寄向遠方
都被一次次退回
并蓋著“查無此人”的印章
那時我才明白
人世間? “愛情”的羽衣很夸張
一旦穿上就會沉溺迷茫
我整整尋覓了十年
詩歌纖弱的手
永遠擋不住戰爭的流血和殘傷
我開始慢慢嘗試兩個字“遺忘”
燒掉信箋
收起過往
今年暮春同學聚會
大家沉浸在“老白干”的喧嚷
有個男生冒了一句? 我見過他
滴酒不沾的我喊著“干杯”
扯著哭腔
我像找回了丟失的故事
飽滿的詩行
我掏盡衣兜所有好看的詞句
殷勤地獻給李白筆下
那輪明媚的月亮
走出酒店? 我搖搖晃晃
摟著路燈當月亮
踉踉蹌蹌? 竟找到校園的海棠
海棠園的月亮坐在大樹上
就像五十五年前一模一樣
石凳上坐著一位白發老人
佝僂的背彎成歲月的模樣
他的雙眼盯著我
突然發出光亮
我倆的視線隔了半個世紀
終于相撞
他蹣跚地走過來
右腿發出金屬的聲響
一聲“對不起”
老眼泛起渾濁的淚光
隱約聽到他的嘴巴在講
熟悉的鄉音帶著些許悲壯
女詩人的詩
已被我鑿刻在老山的石壁
實在不忍心用我殘傷的勛章
勉強丈量你的詩行
月下的海棠
努力尋找月光的翅膀
原來
他把所有的擔當
全部扛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就像暮色中那輪蒼茫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