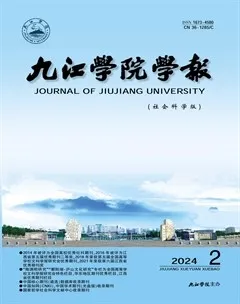抗戰時期農民的生存困境與抗爭
摘要: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在湘黔邊區實施征兵、征糧、禁煙、統制汞業等政策以動員更多的資源支持抗戰。然而,因各級官吏的徇私舞弊,欺凌橫生,國民政府的戰時施政嚴重侵蝕了農民的生計利益。為了爭取生存資源,湘黔邊區的農民以“不抽兵”“不納糧”“公開種煙”相號召,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黔東事變”。“黔東事變”中,農民圍攻縣城,摧毀鄉鎮保甲地方行政機構,沉重打擊了貪贓枉法的官吏勢力,并迫使政府修正相關政策以利抗戰。但是,“黔東事變”也破壞了社會秩序,造成了社會動蕩。“黔東事變”表明國難背景下戰爭動員與民力供應之間的緊張關系,詮釋了中國抗戰的艱難與復雜。
關鍵詞:黔東;湘西;抗爭
中圖分類號:K26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4580(2024)02-0057-(08)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2.011
1942年8月至1943年6月,湘黔邊區的漢、苗、侗各族民眾以“不抽兵”“不納糧”“公開種煙”相號召,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黔東事變”。“黔東事變”以貴州鎮遠、施秉、松桃和湖南晃縣(現為新晃縣)為中心,涉及貴州的三穗、臺江、石阡、江口、劍河、玉屏、雷山、岑鞏、天柱、錦屏、凱里、銅仁、黃平、思南、沿河,湖南的鳳凰、芷江、辰溪、洪江等縣。事變中,民眾圍攻縣城,摧毀鄉鎮保甲地方行政機構,震動西南大后方,國民政府調動逾萬兵力,“剿”“撫”兼施,最終平息了“黔東事變”。
對于“黔東事變”爆發的原因、過程及善后情況,事變主要處理者、時任第一行政督察專員的劉時范在事變結束后所寫的《黔東事變紀要》一書中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載。1943年6月,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情報部報告了1942年大后方民變情況,其中,有六項涉及到“黔東事變”。改革開放后,經過廣泛調研并遍訪“黔東事變”親歷者,1986年12月,施秉、鎮遠黨史辦編輯出版“黔東事變”首輯;1987年12月,黔東南州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出版了“黔東事變”專輯;1990年12月,銅仁地區文史資料委員會也編輯出版了“黔東事變在銅仁”專題。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貴州通史》(第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貴州歷史》(第1卷)等著作也都陳述了“黔東事變”的相關情況。在學術研究方面,何長風、歐大榮、石中光等學者敘述了“黔東事變”的全過程,梁家貴、任牧、桑文軒等學者則闡述了同善社與“黔東事變”的關系。在民族賡續存亡的抗戰時期,湘黔邊區的農民為何發動“黔東事變”?國民政府的戰時施政是如何影響農民生計的?如何客觀認識在當時引起廣泛關注的“黔東事變”?本文擬利用第一手史料,以戰時農民的生存困境為切入點,在湘黔邊區特定的經濟社會環境下探討“黔東事變”爆發的原因及其性質,以期對上述問題有一客觀認識。
一、戰時征兵舞弊及苛虐壯丁造成社會對兵役的恐慌
抗戰時期,為了將豐富的人力資源轉化為抗戰所需要的兵員,國民政府在大后方普遍推行征兵制度,凡是符合兵役條件的男子都必須服兵役,如果逃避或者反抗兵役,就要受到法律制裁。為了征兵的順利推進,貴州實行軍師團管區制度,設省軍管區主管全省兵役業務,其下轄貴節、安興、鎮獨、遵烏四個師管區及貴陽、畢節、安順、興仁、獨山、鎮遠、遵義、思南等團管區,由團管區所轄的各縣市遵辦具體的征兵事務。雖然國民政府構建了一整套兵役法規體系,確立了“平均”“平允”“平等”三平原則,貴州省也頒布了地方性兵役法規,但征兵過程中各級兵役人員的徇私舞弊,以及對被征服兵役者的虐待,造成了社會對征兵的恐慌,減損了農民服兵役的熱情。
抗戰初期,貴州省征兵實行攤派法,各縣將應征兵額攤派到各鄉鎮,各鄉鎮攤派到各保甲。各保甲長或由出丁戶出錢買人頂替,或者上下其手,賄賂公行,層層剝削,民多苛擾。后來,貴州省實行“三步抽簽法”,通過抽簽來決定壯丁服兵役的順序。但是,各縣辦理征兵抽簽極欠公允。在劍河縣,凡是與鄉鎮保甲長有關系者或有錢有勢者,或者抽簽前賄賂兵役人員者都可以逃避抽簽,而被抽中者多是無依無靠的貧苦農民;甚至有的鄉鎮保甲長專門抽征獨子及維持一家生計者以勒索錢財。“現今鄉政府辦理兵役之方法,即捉拿、監禁、捆縛、押解等。縣令一到,即由保長率領鄉丁捉拿壯丁、而捉拿又多在夜間,如捕匪然,鳴槍是為,閭里驚駭。”[1]鄉鎮保甲長為了完成征兵任務甚至使用武力到處拉人頂替,以致人心惶惶,社會秩序騷然,人民痛苦不堪。
“辦理之保甲人員,則以弱者可欺,有利可圖,以致有勢有力者,縱有應征之子弟,亦公然逍遙法外。而無勢無力者,縱系單丁獨子,亦難遂其幸免。”“強拉硬派,假公濟私,甚至交相報復,或輾轉放賣,流弊所及,以致一般農村中之平民,因此釀成空前之恐怖。且有視役政為苛政而猛于虎者,其結怨人民之深,實匪言可喻。”[2]1940年銅仁縣征兵,各級兵役人員罔顧兵役法令,以致估拉壯丁、買賣壯丁之事層出不窮。
壯丁被征后所受的苛虐使社會聞兵役而色變。為了防止壯丁逃跑,兵役機關將被征送的壯丁用繩子捆綁在一起,由持槍軍警押解,如同押解犯人。壯丁被送入“新兵招待所”后,也被禁閉于一室之內,如同監犯失去人身自由。而從“新兵招待所”轉送各師團補充團訓練的壯丁,食不飽,衣不暖,生病得不到醫治,因饑餓、疾病、虐待致死者眾多。時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蔣夢麟視察貴州、廣西、湖南紅十字會醫務工作,途經獨山、鎮遠、貴陽,“我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拴在營里,為的是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東西,更是少而粗劣,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沿途所見落伍壯丁,骨瘦如柴,或臥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狀若行尸,踟躕山道,或倒斃路旁,任犬大嚼。”[3]馮玉祥將軍在貴州視察部隊情況,“從貴陽到遵義看隊伍,新兵穿的衣服破爛極了,都跟叫花子一樣。我講話的時候就栽倒了幾個人。我下了臺,到新兵跟前一個一個地仔細看,有的把肉皮子凍得發青,有的在那里打抖。”他詢問當地士紳對兵役的印象,“這些老先生說,就是征兵的辦法太壞,亂捉兵,待遇又不好,他們都痛恨這個辦法。”[4]在社會對兵役普遍恐慌的氛圍下,應征壯丁逃匿以規避兵役,視兵役為畏途;而狡黠強悍之徒,鋌而走險,以武力抗拒兵役。“榕江、下江、畢節各地先后發生之民變,殆有由來也。”[5]1938年春,湖南會同縣楊國雄聚集千余人,自稱“湘黔邊區抗日后援軍自衛游擊司令”,發動湘黔邊區的農民抗兵、抗租、抗糧。1944年3月,都勻縣春季征兵,“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壯丁未發出征費,內有獨子負家庭生計者,有以公報私者。更有多子不抽,得錢賣放,張冠李戴,搜奪金錢,武力強迫,亂抓壯丁等情況。”[6]都勻民眾因憎恨兵役不公而發動了反對兵役的“都勻事變”。
二、戰時沉重的糧額負擔加劇農民的生計危機
抗戰期間,為了保障糧食供應,國民政府加強了在大后方各地征糧的力度。為了穩定糧食來源,減少因物價上漲而對糧食供應造成的沖擊,增加財政收入,從1941年6月起,國民政府推行田賦征實制度,將田賦由原來征收貨幣改征實物,農民負擔不斷加重。黔東和湘西因地處戰略要地,國民政府在此駐有大量軍隊,這些軍隊的糧食很大一部分仰仗于貴州和湖南供給。1941年實行田賦征實后,貴州省應繳軍糧尚差138萬市石,貴州省乃實行“以鹽易谷”辦法,來完成軍糧任務。位于黔東的第一行政督察區1941年征購軍糧為228900市石,1942年征購軍糧則增加到254500市石,比上年增加25600市石。為了田賦征實制度的順利進行,第一行政督察區規定田賦征實稅率為每元折合稻谷兩斗,交通不便的縣份按每斗折合法幣六元的標準征繳法幣。其中,鎮遠等十四縣征收稻谷,總計征收137589市石6斗1升;松桃、沿河、石阡、錦屏等縣因交通不便而征收法幣計3852230.64元。如果將1941年征收的稻谷折合成法幣計算,其總額為1940年的35倍。而該區各縣農民賴以應急的積谷卻微乎其微。據統計,自1936年至1941年止,該區各縣積谷僅81720市石,若以該區總人口2066078人計算,平均每人僅有積谷3市升,只夠一日的口糧,這與政府征購糧食過多有關[7]。銅仁產糧甚少,只能以特產桐油來繳納田賦,但因桐油價格低落,農民入不敷出,無力完納田賦。所以,有的農民因繳納不出田賦而遭受政府沒收桐樹的處罰。
“征實完納手續,農民受苦最深。距離征收機關較遠之地之農民,往往因路途遙遠,負擔所納糧食至所交納之地,費時甚多。而又不能隨到隨征,以至其旅費之消耗,常超過其所納糧食價值數倍以上。”[8]田賦征實前,農民完納田賦,只需繳納糧款即可,而在改征實物之后,農民則需要將糧食挑運到指定地點繳納。而戰時人力昂貴,一擔稻谷,動輒需要十余元,路遠者三四十元不等,以致運送糧食的人工費用超過應繳納田賦者有之,稻谷送到交糧地點多天還不能按時收納者有之。農民所繳納糧食的價格也遠低于市場價,農民因此承受相當大的損失,田賦征實無疑增加了農民的經濟負擔。
糧食問題為“黔東事變”之主因[9]。國民政府大規模征糧使農民生活更加貧困,加劇了農民的生存危機。在1941年的田糧征購過程中,劍河縣民代表上書貴州省動員委員會請求減免軍糧配額,其文如下:
為陳明購辦軍米困難情形仰祈核準豁免示遵由。
竊于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奉本縣動委會通知,召開討論軍糧會議。關于軍糧之籌集,在平時已屬重要。值此抗戰時期,其需要之迫切,當千倍于往昔。自應本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糧出糧之原則,努力以赴。抑況依照行情給價,又何樂而不為?無如劍河曾于去歲奉令征調民工五千,前往天柱修筑穗靖公路。彼時正值春耕時關,只以公路關系國防交通至巨,不能不忍痛拋棄農事,計征調各級壯丁到段工作者,為時數月。查本縣壯丁,計僅八千余名,而征調者過半,以致田多荒蕪,收成歉薄。加以黃河水利委員會清水江流域工程處員工數百人,所需食糧均仰給于劍河。又機械化部隊暨企業木業公司等先后采購,約在六千大石以上。因之,入夏以還,食糧即告匱乏,環顧劍民,大多挖蕨延命,熬粥過活。近益以旱魃為虐,抗旱作物無望。重重演變,形成米價激增。每米一斗由十元售至二三十元不等,所有一般貧民,食米之未下咽者,一月或兩月有余。即向稱中產之家,亦多半蕨半米,摻食度日,哀鴻遍野,良用撫然。逖聞采購軍糧,莫不咋舌相向。在會人等深知軍糧之重要,惟此次攤購軍糧四千大包,掃劍河現有之谷米,猶恐不及半額。以故當會議場合,均各噤若寒蟬,呆若木雞。良以四千大包軍糧,為數過巨,輾轉籌劃,委實無法辦到。劍民等對于應征應調,罔敢后人,無如報國有心,籌糧無法。擬懇格外體恤,府準豁免,抑或準俟新谷登場后,再行認購。
謹呈貴州省動員委員會
劍河縣公民代表何德、楊儐卿、洪余哉、龔曰三、何憲綱、丁叔仁、丁伯華、吳昌銳、王伯榮、潘定光[10]
全面抗戰爆發后沉重的兵糧負擔使湘黔邊區的民眾苦不堪言。“黔東事變”主導者吳宗堯發布的《為除暴安良告民眾書》指出“人民負擔日重”“民生凋敝已達極點”“天人共怒,有口皆碑。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時者也”[11]。1939年7月,劍河縣保警隊隊長韋善長在該縣南洞司聯保催收兵工糧款及區保經費,用殘酷手段摧殘農民引發眾怒而發生農民武力抗征的“南洞司事件”。
三、戰時的禁煙侵蝕農民的生存利益
湘黔邊區的鴉片種植已有近百年歷史,鴉片已成為農民生計的重要來源。民國以后,西南各軍閥因爭戰頻繁而大開煙禁,抽收關稅以籌軍政費用,以致種煙者多,吸食者也多。在貴州,“無論老少婦孺,咸多喜吸食鴉片,即婚喪燕爾,買賣交易,鴉片為招待媒介。甚至男婚女嫁,家長煙槍燈較多之家為中選,吸食者之多,可以想見。”[12]為了消減鴉片對中國人身體的戕害,南京國民政府1935年開始實施為期六年的禁煙計劃。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繼續戰前的禁煙政策,且抗戰時期的禁煙實屬必要,具有特殊意義:第一,由于長期吸食鴉片,民眾身體孱弱,征選合格兵員困難。貴州省第三行政督察區共有32萬壯丁,其食鴉片者竟達1/3。出于兵源上的考慮,禁煙也就成為了戰時國民政府的一項要政。第二,由于種植鴉片一本萬利,“常常種稻田土,僅供一人;改種煙苗,足資十人。煙價昂者,獲利尤厚。”[13]而政府的禁煙措施愈嚴,煙價愈貴,偷種者也愈多。農民因此減少糧食作物的種植而偷種鴉片。貴州省第三行政督察區可耕地面積約750萬市畝,其中,7/10以上被種植鴉片。為保障戰時糧食生產,國民政府需要嚴厲禁煙。第三,“土匪與種煙是相依而存的。土匪靠包庇種煙的收入而生存,而擴充,而又以其力量包庇或壓迫人民去種煙,以是匪煙的關系不可分。”[14]為了穩定湘黔邊區的社會秩序,必須肅清湘黔邊區的土匪;要肅清土匪,必須禁止種植鴉片以斷絕土匪的經濟來源。
根據國民政府的禁煙部署,貴州省政府施行四年禁煙計劃,從1935年10月開始至1939年10月止為完全查禁煙毒時期。禁煙期間,在城鎮,禁止偷運、偷售與偷吸鴉片;在農村禁止種植鴉片。但在禁運、禁售、禁吸過程中,官吏與警察徇私舞弊,營私發財。鴉片一經查獲,就以假換真,或者據為己有,或者倒賣;煙販被捕,出重金即開釋,如敲詐不成,即予處死。
戰時禁煙措施中禁止種植鴉片對農民生計影響最大。湘黔邊區歷來為種植鴉片的重要區域,湘黔邊區因此成為貴州和湖南禁煙的重點區域之一。“無論任何地方斷斷不容有一苗一葉一花一苞發現,否則一經查出,不問種者包庇者均一律按法槍決,斷不姑息!”[15]為了徹底禁止農民種植鴉片,各縣市組織鏟煙隊查鏟煙苗。但是,在查鏟煙苗過程中,地方官員巧取豪奪,狼狽為奸,假禁煙之名,行一己之私,致使“禁煙者庇煙,鏟煙者分煙。年年禁煙,年年種煙,年年收煙”[16]。面對上級嚴厲的禁煙政策,湘黔邊區的農民大多采取觀望的態度,因觀望而違農時。“既種而查鏟,既鏟而再種者有之。查則壅土以掩蔽,查后則揭土以培植者亦有之。”“坐是之故,地多閑曠,民鮮生產,食糧不足,荒象立現。其種而幸得者雖立致巨富,仍難于得食。種而不得,則難免饑寒,鋌而走險。”[17]戰時嚴厲禁煙斷絕了農民賴以生存的經濟來源,而政府又無適當的措施來彌補農民因禁煙所受的經濟損失,使農民本就十分窮苦的生活雪上加霜。特別是各地在鏟煙過程中各級官吏對農民的苛虐行為激起了農民的憤怒,農民不得不以武力抗拒鏟煙。1940年2月,貴州臺拱縣(1941年并丹江縣,改為臺江縣)保警隊在該縣第五區黃泡、岑斗寨、小木等地暴力鏟煙,燒毀農民房屋,農民因此與鏟煙部隊發生武力沖突,死傷甚多。1942年3月,由銅仁、松桃、江口三縣聯合組成鏟煙隊在三縣邊區聯合鏟煙。但鏟煙過程中,鏟煙隊敲詐勒索,縱火燒屋,濫殺無辜,激起了松桃縣農民的公憤,松桃農民聯合起來武力抗鏟。“鎮、施十一縣之種煙地區,幾悉為黔東事變之酵母。”[18]“黔東事變”倡導者提出的“公開種煙”就是利用農民反對禁煙的心理煽動事變。1943年3月開始,發生于貞豐、望謨、鎮寧、關嶺、紫云、普定等縣的“黔西事變”與“黔東事變”一樣,也與禁煙官吏的貪贓枉法有關。1944年4月,黎平縣銅關、雙江等地農民,為反對保安團隊燒殺擄掠的高壓禁煙手段而釀成了農民攻陷縣城、劫持黎平縣長和行政督察專員的“黎平禁煙事件”。
四、戰時汞業統制下農民生計步履維艱
貴州、云南、湖南、四川是我國汞礦主產地,而湘黔兩省汞礦產量最大。湘黔邊區汞礦分布于南起湖南新晃縣,北至湖南乾城及貴州松桃,綿延幾百公里的區域內,主要涉及婺川、三都、丹寨、玉屏、銅仁、松桃、思南、印江、江口、黃平、鎮遠、省溪、晃縣、鳳凰、乾城等縣。礦廠主要有晃縣所屬酒店塘、三牛灣、向家地、砂坪,玉屏縣屬田壩坪,省溪縣(1941年撤銷,并入玉屏、石阡兩縣)屬萬山場,銅仁縣屬巖屋坪、茉莉坪、大硐喇,鳳凰縣屬茶田、猴子坪,乾城縣屬霧神寨、麻潘坡,松桃縣屬鴉砂塘、落塘坳等。
湘黔邊區的汞礦開采與冶煉始于明初的洪武年間,原來主要由各省設局或由民間自行開采。近代以后,曾由英法合辦的英華公司開采,一戰期間,年產量最多時達三四百噸。后來因時局不靖,產量日益衰微。抗戰軍興,鑒于汞礦為戰時軍事工業急需原料,1938年6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接管萬山場、巖屋坪、大硐喇等地汞礦廠。1939年1月,資源委員會與貴州省政府成立貴州省礦務局和貴陽水銀煉廠,統制貴州省內汞礦開采。5月,湖南省成立湖南汞業管理處,負責湘西汞礦開采。
戰時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對汞礦的統制是維持抗戰持久進行的必要措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其一,為抗戰軍工生產提供原料;其二,汞礦產品作為重要的戰略物資出口盟國以換取抗戰急需的外匯;其三,避免汞礦產品走私落入日本人之手以制造武器。然而,分布在湘黔邊區崇山峻嶺之間的大大小小的幾十個汞礦廠,歷經幾十、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開采,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成千上萬的農民以開采汞礦為生。政府對汞業的統制,無疑剝奪了民間汞礦開采權,農民迫于生計,不得不靠拾撿荒砂度日。“汞苗微薄者為之‘荒,一般人民,即將荒石檢出提煉,每日收入可四五角或一元不等,故所有田園不愿耕種,而轉營此業。”“人民樂此業者當在三分之二以上。”“所謂全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營汞業者,全系幫工或檢荒,每日所入,只勉強維持生活費用。”[19]同時,為了防止汞礦產品走私,國民政府規定民間的汞礦產品只能按照官價統一售賣給政府,否則,以漢奸罪論處;而政府的收購價格卻遠低于市場價。國民政府對汞礦的統制侵蝕了農民的利益,這自然引起了農民的不滿。湖南省檔案館保存有一張省溪縣農民要求開采汞礦以維生計的漫畫,其所配文字如下:
省溪縣朱砂水銀各地都出現,因此數年都是民商辦。民商辦起都可煉,貧人專靠煉砂來吃飯。不料,礦局來到打破碗,一般民商喊皇天。朱砂水銀不可賣,要歸礦局賣。如果賣送別人,他說是漢奸。民商喊一天罵一天,有的氣心腸斷。罵不完,不覺來到一年滿,民商游行示威才脫難,仍就把廠辦。[20]
另外,丹寨縣李雙發因汞業統制而致生計斷絕,不得不向上級請求救濟,其困苦情狀由此可見一斑。
貴州丹寨水銀礦廠荒民李雙發呈請救濟案由。
貴州省丹寨縣水銀礦廠荒民李雙發等為生計斷絕,呺天作主,救濟民命事。竊荒民等既無職業,后無家產,向來生活全靠在水銀廠翻檢荒砂,日獲數錢數兩不等。此乃廠主所棄余砂,并請備荒灶自行燒煉,照章上課,稍搏升斗,養活生家。自從水銀統制以來,規定翻檢荒砂,不準自行燒灶,若檢獲稍些,必須待上統制公灶方準燒煉。既成水銀,又只給每公斤價值法幣二十五元,除日食外,得不償失,窘迫日至。竊思民等,貧苦已極,為生計所驅,乃不惜泥中出,風夕月夕,百耐勞苦,作此下乘活計,養活生家,茍且度日。今一旦受此奇窘,不只驅老弱于陷阱,罹窮民于荼毒。欲改業則苦無資本,欲移徙則無處可歸。輾轉思維,徒坐待斃。洋洋千言,類若游魚。處此生路危已之時,救命心急,乃不避斧鉞之誅首,呺天乞救之請。請求鈞長一視同仁,援救貧苦,準民等仍舊翻檢荒砂,給與相當價值,藉此度活。真生死人而肉白骨,生當銜環,死當結草,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呈荒民代表 李雙發三十一年二月七日 [21]湘黔邊區地瘠民貧,田地稀少,很多農民依賴開采汞礦為生,國民政府施行汞業統制政策時,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補貼以汞礦為生的農民的生計,這加劇了農民的生存危機并引發農民的反對。
五、動蕩不安的環境與崇尚武力的傳統催生農民的抗爭行為
美國學者裴宜理在研究近代華北地區農民的抗爭行為時指出,農民的抗爭在地理上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只有在一些特定地區,才不斷地反復爆發。對于這種反復發生的現象,人們必須要仔細研究這種現象發生發展所依賴的地方環境才能給予合理的解釋。“黔東事變”的發生還與湘黔邊區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及崇尚武力的傳統相關聯。
湘黔邊區崇山峻嶺,交通不便,各縣縣城距離各省省會,近者在八九百里,遠者在千里以上,各省政府對邊區各縣鞭長莫及,政府控制力薄弱,經濟文化教育也相當落后。芷江縣,“民心頑固,風氣未開。婦女纏足蓄發,纏足者約有十分之四,蓄發者約在十分之七,男子蓄發結辮者亦尚有十分之一。”[22]會同縣,“民性強悍,好械斗,健訟,但勤樸耐勞,豪俠好義,亦有足多者。”[23]在臺江、劍河等縣,“不識字的民眾實在太多。例如國幣到各縣使用時,有許多人對上面的數目字也不認識,布告更無法認識,其他一切政令那能說得上有順利的推行。”[24]
湘黔邊區長期游離于政府治理體系之外,邊區民眾形成了爭強好斗、崇尚武力的傳統;自清末形成的匪患,根深蒂固,有“兵民匪三位一體”之說。民國以后,軍閥混戰,“兵匪相尋,民間之槍支流轉既多,恣睢暴戾之風長,往往擁槍自豪,尋仇報復,流為匪類而不自知。因之,社會意識逐漸輕法而重武。”[25]如以縣城被土匪攻陷次數而論,鎮遠縣城自1911年至1942年“黔東事變”發生時,先后被攻陷十二次。施秉縣城于1921年、1922年、1929年被土匪攻陷。三穗縣城于1918年、1923年、1926年被土匪攻陷。1912年,臺江縣城被土匪攻陷,民間損失甚巨;1924年,土匪再次攻陷縣城;1925年和1929年,土匪又先后兩次攻陷縣城并將縣城洗劫一空。“匪患實在是慢性的沉珂,這個慢性的沉珂,那時正以急性發作的姿態表現在湘西。”“在我到任前不久,有龍云飛部發動的‘乾城事變,有吳恒良部的‘革屯軍在永綏一帶的騷動。”[26]全面抗戰爆發初期,湘西土匪,“群然蠢動,一時盜賊蜂起,行旅戒途,甚至軍用車船亦遭搶劫。”[27]
軍閥不斷爭戰、政府控制與治理能力的衰弱使湘黔邊區成為化外之地。全面抗戰爆發后,湘鄂川黔邊區既是抗戰的后方基地,又是拱衛陪都重慶、捍衛西南大后方的前哨,在軍事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但湘鄂川黔邊區政治社會狀況復雜、經濟貧弱、交通閉塞。為了穩定湘鄂川黔邊區,構筑捍衛大西南和重慶的戰略屏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于1938年7月,成立鄂湘川黔四省邊區綏靖主任公署,加強對邊區的控制與治理。綏靖主任公署除清剿邊區土匪,維護邊區治安外,還配合貴州和湖南省政府在邊區修筑公路,開發礦產,整頓保甲,組訓民眾,改良基層政治等等。同時,在軍事上,國民政府軍政部還在湘鄂川黔邊區的重慶、綦江、芷江等地設置有第一、第二、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第二十五、第三十二等補充兵訓練處,補充兵訓練處除接收與訓練新兵外,還有監視邊區社會治安,維護邊區社會穩定的目的。但是,因交通不便,政治力量難以延伸至鄉村,縣以下行政機構不健全,官員貪腐并欺壓農民,國民政府加強湘鄂川黔邊區開發、治理與控制的效果甚微。由于湘黔邊區長期動蕩,一般民眾受“草莽英雄思想遺毒,不安分者大有人在”[28]。湘黔邊區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和歷史上所形成的崇尚武力的傳統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黔東事變”發生的社會心理基礎。
六、結語
抗戰時期,農民承擔了沉重的兵糧稅費,由于財政困窘,國民政府卻又無力向農民提供更多的生計保障;加之官吏的腐敗、欺凌、壓榨與殘暴,農民痛苦不堪,湘黔邊區農民為了生存群起抗爭。“取消苛捐雜稅”“派兵拉夫豁免”“軍食公買公賣”等口號表達了農民爭取生存權益的訴求。董必武1945年3月在延安所作報告《大后方的一般概況》中指出,大后方民變大都是反對官吏貪污舞弊,反對兵役、糧政等辦理不善,全是自保性質[29]。但是,“黔東事變”發生在抗戰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其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社會秩序,造成了社會震蕩。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1943年5月2日和5日發表《鞏固后方》《鞏固國內團結》兩篇社論,社論指出:“鞏固的前線,更有賴于鞏固的后方,沒有鞏固的后方,就難有堅強的前線。”“誰破環后方的秩序和安寧,誰就破壞了抗戰,違背了民族的利益,違背了人民的意志。”[30]1943年6月,周恩來在《關于大后方民變問題致中央情報部的電報》中,分析了民變發生的原因、民變的性質,也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民變擴大實乃抗戰中不幸,亦由于抗戰情緒低落,特務橫行,經濟困難,政治腐敗等等所致。”“而且這多半是自發性的。”“我們對此事來表示堅決反對的態度,決不幸災樂禍。指出事變發生的原因,及其落后危險性。”[31]
雖然,農民通過武力抗爭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但是,飽受日本侵華戰爭之苦的農民也深明民族大義,他們深深懂得他們的苦難是日本侵華戰爭造成的,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罪惡;戰時的征兵、征糧、征稅、禁煙與汞礦統制等政策是抗戰必需的,具有相當的正義性,農民對所遭受的痛苦與付出的犧牲是可以理解和忍受的。這也正如《鞏固后方》社論指出的那樣:戰時的征兵、征糧,“這些辦法都是必要的,為了抗戰的勝利,全國人民應該熱烈的擁護,而且也是在熱烈的擁護著的。”[32]抗戰期間,湘黔邊區人民和全國人民一樣,在極其困苦條件下,貢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如修建黃平機場,服務于國防軍事工程,保障軍糧供應,三穗、天柱、鳳崗等縣編組志愿兵團開赴前線殺敵等,為抗戰勝利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黔東事變”表明了國難背景下戰爭動員與民力供應之間的緊張關系,詮釋了中國抗戰的艱難與復雜。
參考文獻:
[1]國民政府訓練總監部和軍委會政治部派員視察西南各省及協助兵役宣傳事宜附視察報告[B].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七七二,目錄2,卷宗957).
[2]四川省臨時參議會第四次大會紀錄[M].成都:《新新新聞》報館印刷部,1941:65.
[3]蔣夢麟.西潮與新潮[M].北京:中華書局,2017:391-395.
[4]馮玉祥.我的抗日生活:馮玉祥自傳2[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58.
[5]貴州省臨時參議會第一次大會記錄[M].[出版者不詳],1939:78.
[6]陸軍炮兵學校政治部呈報貴州都勻因役政辦理不良激起民變情形[B].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七七二,目錄2,卷宗604).
[7]貴州省第一行政區縣政參考資料:第二輯[M].貴陽:貴州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出版年份不詳]:72.
[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財政經濟(2)[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222.
[9]財政部貴州省田賦管理處關于抄送松桃縣糧政事變問題主因供參考的公函[B].貴陽:貴州省檔案館(全宗M008,目錄1,卷宗02883).
[10]貴州省動員委員會關于對劍河縣民眾代表何德、洪余哉等呈報購軍米困難情形以求豁免示遵由[B].貴陽:貴州省檔案館(全宗M005,目錄1,卷宗0020).
[11][17][18]劉時范.黔東事變紀要[M].貴陽:[出版社不詳],1943:16-55.
[12][13]水深火熱之貴州煙禍[J].拒毒月刊,1929(33).63-64.
[14]湖南省政府公報室.湘政一年[B].長沙:湖南省檔案館(全宗22,目錄3,卷宗1145).
[15]禁絕煙毒與民族復興[N].大公報(重慶版),1940-06-02,(03).
[16][31]陳俊杰,傅順章.抗戰時期鎮遠專署關于銅、松、江三縣鏟煙部署,周恩來關于大后方民變問題致中央情報部的電報[J].銅仁地區文史資料,1999(1):49-135.
[19]貴州省省溪縣概況一瞥:省溪縣社會概況[B].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十一,目錄2,卷宗1623).
[20]何玉衡關于匯報調查統制萬山各商礦銀砂收買情形給貴州礦務局的報告[B].長沙:湖南省檔案館(全宗M121,目錄1,卷宗00099).
[21]貴州丹寨水銀礦產荒民救濟案[B].臺北:臺灣省史館(全宗M003,目錄010303,卷宗0625).
[22][23]教育部戰區中小學教師第九服務團.湘西鄉土調查匯編[M].沅陵:合利益群印刷所,1940:8-19.
[24]貴州省政府、滇黔綏靖副主任公署聯合視察室徐實圃報告“黔東事變”情形座談會記錄[B].貴陽:貴州省檔案館(全宗M001,目錄2,卷宗00742).
[25]劉時范.行政督察經驗錄[J].服務月刊,1940(5):6.
[26]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94.
[27]湖南省政府秘書處公報室.湘政二年[M].長沙:[出版社不詳],1941:60.
[28]雷山縣地方概況調查報告[B].貴陽:貴州省檔案館(全宗M008,目錄1,卷宗00282).
[29]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五):抗日戰爭時期(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1.
[30][32]鞏固后方[N].新華日報.1943-05-02,(02).
(責任編輯 胡安娜)
*基金項目: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抗戰時期農民的生存困境與大后方民變研究”(編號22YJA770007)。
收稿日期:2024-03-13
作者簡介:龔喜林(1967—),男,博士,九江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