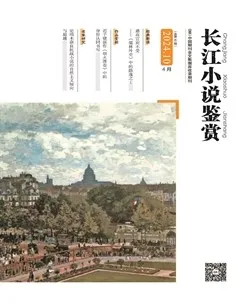論端木蕻良抗戰小說的自然主義傾向與超越
劉京典
[摘? 要] 端木蕻良在創作后記中曾論及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左拉,其抗戰小說《大江》在“癥候式”的描寫特征與“實驗式”的寫法上都存在自然主義傾向。然而這些相似性背后,二者在思想主題與情感態度上都存在深層差異。端木蕻良出于民族情感與對民族前途的希望,形成了將個人力量與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獨特命運觀,從而完成了對自然主義消極的命運決定論的批判與超越。本文通過對端木蕻良抗戰小說中所呈現的命運觀的分析,幫助讀者理解其抗戰時期的思考線索,為探索中國作家對自然主義思潮的復雜態度提供了代表性的例證。
[關鍵詞] 端木蕻良? 抗戰小說? 自然主義文學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10-0080-04
端木蕻良在其抗戰時期小說《大江》的后記中寫道:“我以為把一個人的一生無條件地交給一種情欲去受無限地統治,這種描寫也必然要遭受抗議。”[1]這是其筆下少有的談論創作中關于命運與情欲看法的文字。這段討論中,他將莎士比亞、巴爾扎克和左拉進行對比,直接表達了對以上三位作家的批判性看法。端木蕻良論及的左拉是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左拉吸收實證主義哲學與遺傳理論的思想,提出了一套命運決定論的創作理論。抗日戰爭時期,戰爭給中國軍民帶來深重的苦難,戰爭環境下,人們有朝不保夕的心理體驗,中國作家的抗戰小說中出現了大量關于命運母題的討論。端木蕻良研究者王富仁教授曾用“生命活力”對端木蕻良抗戰時期小說的主題進行精煉的概括,該提法包含了“野性力量”“本能欲望”“時代命運”“反抗主題”等一系列豐富的主題情感表達[2]。本文以西方自然主義文學創作的特征對端木蕻良抗戰時期創作的小說進行分析,研究其中的自然主義傾向,進而探究這種相似背后所包含的內容主題與情感態度上的巨大差異,以此說明自然主義思潮與中國左翼作家群之間的聯系與分歧。
一、端木蕻良抗戰小說中的自然主義傾向
1.對底層人物的“癥候式”描寫
自然主義創作理論中對社會病態和人性赤裸的紀實描寫容易使人聯想到文學上的“癥候式”分析方法:“以文本的各種悖論、含混、反常、疑難現象作為突破口,在尋找原因的過程中,尋找這些現象的意義。”[3]這種對文本中反常現象的關注恰與自然主義的批判目的類似,都為證明或分析出關于人性或社會的結論。端木蕻良抗戰小說中,有大量與人們的正常生活情景相異的反常情節。
端木蕻良小說對農民的苦難生活有詳細的描寫。例如小說中出現了走投無路的窮人女性出賣自己的身體以換取食物的形象。《科爾沁旗草原》中,淫蕩的丁三爺作為管事的地主,經濟上掌握了受雇農民的生計,因而對草原上的農民有絕對的支配權。他以女孩家庭的生計來源為籌碼逼迫女孩順從,強占民女。窮苦的女孩充滿恐懼卻又討好地成為其玩弄的對象。此類描寫在端木蕻良的成名作《鴜鷺湖的憂郁》里也有出現。端木蕻良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分配極度不平等的封建土地制度。這種制度下,農民是地主的幫工,兒女還要受地主的羞辱。端木蕻良在創作中追求真實,常用表情特寫或內心獨白表現女孩處于地位極不對等狀態下的卑微、恐懼、羞恥卻又順從的矛盾心理。在作品閱讀中,這類使人感到不適的特寫可以作為文學“癥候”進行分析。
2.社會環境對人物的影響
左拉在《實驗小說論》中論述了“環境”的重要性:“我還認為環境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人不是孤立的,他生活在社會中……甚至我們最重大的課題就在于研究社會對個人、個人對社會的相互作用。”[4]可見,左拉認為人無法逃脫所處的社會環境的影響。
端木蕻良筆下的土匪形象能很好地體現出社會環境影響人物行為,他們做出搶劫、殺人這類反社會行為;另一方面,在反侵略的時代背景下,土匪又常常自發地拿起武裝反抗日軍,具有很強的斗爭性和戰斗力。一個普通人由于社會逼迫無奈變成匪,再到被正規武裝改造成抗日隊伍中堅強的兵,這一整個轉變過程恰好可以很好地反映壓迫與斗爭兩大主題,進而成為描寫的常例,典型代表就是《大江》中李三麻子和《科爾沁旗草原》里的老北風。
該轉變過程中,人物經歷了兩次轉變:首先是從民到匪的階段,這是一個從懦弱無力的被壓迫者到殘暴有力的反抗者的過程;第二次從匪到軍的階段是一個從無序暴力到回歸正義的過程。
3.實驗式的寫法嘗試
《實驗小說論》中左拉借用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建立了一套獨特的“小說實驗”理論。他認為:“我們應當像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研究非生物及生理學家研究生物那樣,去研究性格、感情、人類和社會現象。”[4]具體的操作方法是:“小說家既是觀察者又是實驗者。作為觀察者,他建立使人物活動和展開想象的堅實場地。然后,他作為實驗者出現并進行實驗……使人物在具體的情節中行動,通過情節指出,事件連續的發展過程完全如研究對象的決定因素所要求的那樣。”“然后研究事實的內在關系,通過改變情況和環境來影響它們,但永遠不能偏離自然規律。最后,從人物的個人行動和在社會中的活動認識了這個人,這是科學的認識。”[3]從中可解讀出以下信息:其一,小說創作者在建立實驗前必須有已選定的主題作為要探索的“真理”,即預設;其次,創作者也就是實驗者僅是建立供人物(實驗對象)活動的情境,然后去觀察其中人物的活動是否符合預設主題;其三,由于實驗中作家只是采集事實,故要求如實記錄以保證實驗的真實性;其四,通過實驗探究一般的規律,即為了證明預設的主題。探究的規律是關于人與社會的關系的規律,由此得到的結論或規律具有科學性。
《大江》后記中,作者這樣表述:“不但看見表面,而且要深入內部,研究組成部分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先把每一個組成部分隔離起來,研究它的發展過程、它的形成歷史之后,再去看環境對于事物的影響及事物對于環境的影響。然后再回到這對象的發生、變化、進化和變革,一直到這對象最后的影響。”[1]端木蕻良在對此部小說的寫法嘗試中體現了以下幾點:其一,要全面地探討問題,事物內外的、不同時間的都要研究;其二,與實驗的控制變量法類似,在討論問題時需將問題的組成部分分別拆分再研究;其三,關注環境與事物間的相互關系。
主人公鐵嶺的獵人窩棚被洗劫,隨后獵人群體散伙,他面臨第一次選擇:上山當土匪、投奔義勇軍、流亡到關內、回鄉種地,這也是失去生計的百姓所能作出的全部選擇。端木蕻良在此通過其他獵人的口詳細展示了這些選擇,且將在整部小說中將它們逐一排除。這時的鐵嶺選擇回鄉種地,端木蕻良像觀察記錄一般描述了鐵嶺復雜的內心感受:“羞愧,悲哀,失望,幻滅,惱恨,憤怒,都接待了他。”[1]第二次選擇發生在鐵嶺決定離家入關的時候。他回鄉種地的選擇落了空,于是選擇從軍。這時鐵嶺是迷茫的,直到他直面死亡,這使“他的求生的愿望更強起來”[1],最終他逃出生天。這時鐵嶺已經完成了從“懦弱的民”到“迷茫地流浪”再到“勇敢的兵”的轉變。小說中與鐵嶺形成對照的土匪角色李三麻子出場即土匪,這部小說也完整地講述了他由“懦弱的民”到“殘暴的匪”再到“勇敢的兵”的轉變過程。
于是端木蕻良將所有選擇都進行了講述,他所設置并觀察的角色全都走上了從軍抗日的道路,若將這樣的設置比喻成一次實驗,那么完全符合他對寫法嘗試的表述。首先,預設“怯懦者如何才能變成大勇者”的論題。接下來,設置多個角色互相對照,通過不同角色的經歷,把每一種選擇分開講述,并記錄下這些角色心理的轉變過程。最后,通過對比得出結論:人出于求生本能的覺醒,才逐步轉變為“大勇者”。由此可見,端木蕻良在小說《大江》中對小說敘事寫法上的嘗試,都與左拉在《實驗小說論》中所倡導的“實驗小說”主張具有相似性。
二、欲望觀與命運觀的分歧
綜觀上文,可見端木蕻良在抗戰時期的創作在描寫特征、寫作方法、問題探究等方面與左拉在《實驗小說論》中所倡導的“實驗小說”高度相似。然而,端木蕻良在《后記》中將莎士比亞、巴爾扎克與左拉對比,發現他們觀念的巨大差異。端木蕻良認為筆下人物受命運支配最甚者是莎士比亞:“他的結論依然把沒尾巴的猴子(人)拴在命運的車輪后邊,在那后邊卻有個頑皮的孩子,在那得意地狂笑。”其次是巴爾扎克:“一切英雄都有一種特殊的情欲,這種情欲對于他本人成為一種生理上的命運……巴爾扎克的小說是凱旋的情欲的紀事詩。”再以巴爾扎克對比左拉,他認為左拉“害怕那些幾千種復雜原因,這些原因決定著人的行為,影響著人的情欲”[1]。端木蕻良關注的是命運的決定論問題。莎士比亞從古典主義的悲劇論出發,使人完全成為命運的奴隸;巴爾扎克筆下人物的命運則是由于欲望(情欲)的一步步生發而造成的,他會給予人物成長變化的過程,看情欲是如何成為人物命運的主宰的;左拉則不愿意討論情欲生發的原因,只將人物機械地引向命運的結局。在這個光譜之中,三個作家全部被端木蕻良歸結于命運決定論的一側,只是在程度上有區別,他最傾向這種決定論程度最輕的巴爾扎克。于是,端木蕻良在對比之后便得出了“我以為把一個人的一生無條件地交給一種情欲去受無限地統治,這種描寫也必然要遭受抗議”[1]的結論,這便可看出端木蕻良創作理念與自然主義思潮間的巨大差異。
端木蕻良討論命運與欲望的關系的目的在于強調民族文化中的野性力量:“他們(鐵嶺和李三麻子)都成了英勇的戰士,而他們的原始的野生的力,表現在這個當兒,反而更能看出我們這個民族所蘊蓄的力。我在這里說的命運并不是什么宿命論的玩意,我說的是大時代所加給他們的任務。”[1]而且“他(李三麻子)所遭受的命運反而改變了他的情欲”[1]。這里端木蕻良非常清晰地講述了他的命運觀。其一,個人與民族的命運相通,命運是時代賦予個人與民族必須走的路;其二,個人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其三,不是欲望的生發決定了命運,而是命運的展開激發了人物善的欲望(求生),克服了惡的欲望(情欲)。在命運與欲望的相互作用之中,作者關注的是“民族救亡的力量從何處來”的問題。
三、對自然主義文學的態度與超越
1.相似與接受
從哲學思潮上說,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受科學主義與實證主義發展的影響。若考察此流派產生與興起的社會背景,可認為自然主義文學產生于對于十九世紀末法國社會的猛烈批判。當批判的目的與科學主義的寫作主張結合,就形成了一種以極其寫實與追求客觀性的獨特寫法。在對人性全然悲觀的態度影響下,自然主義作家徹底拋開了道德顧慮,在人性批判與社會批判的道路上狂飆,“真正做到了讓任何一切都可以進入文學作品中”[4]。
而端木蕻良在小說中盡可能追求真實地描寫苦難,其目的一是批判,二是同情。出于左翼作家的立場,端木蕻良批判將人壓榨致死的土地剝削制度;以東北流亡作家的立場,他以關外文化中野性剛強的一面去批判關內文化的腐朽軟弱;出于民族身份的立場,他批判侵略戰爭中殘酷的殺戮與掠奪。可以說在追求批判性與真實性的特點上,端木蕻良的目的與左拉的目的是相似的。而另一方面,作為一位故土淪陷的中國作家,他同情筆下那些承受苦難的人物,卻也無法回避民族積弱的事實,以至于無法不去思考民族衰弱的問題所在,無法不去思考可以使民族為之一振的力量源泉。換言之,端木蕻良的寫作本身帶有一種“問題意識”。
而自然主義小說家出于對自然科學實驗方法的模仿,必須在寫作前提前預設并要求論證的問題,也使得其小說創作自然帶有一種“問題意識”。因此,自然主義小說家的“問題意識”催生出了“實驗小說”主張;同樣帶有解決問題目標的端木蕻良也選擇了一種探究式的寫法。于是,這就能夠解釋兩者在寫法上出現的相似之處。而這相似之處背后的情感態度上卻有區別。在批判目的所反映的對民族現狀的失望之外,端木蕻良對問題的思考則是出于希望民族振興的目的,這是中國左翼作家的文學傳統。
2.分歧與批判
若分析自然主義文學思潮在中國的歷史,會發現端木蕻良的創作與自然主義作品的相似之處正是左翼作家所希望借鑒之處,而其在情感態度上與自然主義思潮相異之處,也正是自然主義文學在中國遭到批評的原因。
自然主義中科學主義的哲學基礎與五四運動中宣揚“賽先生”(科學)的主張非常相符。有學者指出,自然主義思潮在中國受到賞識的原因有二,一是“求真”,如沈雁冰(茅盾)就認為自然主義重視客觀性的程度超過現實主義,這適用于揭露世間丑惡;二是題材上開創性地關注到工人與平民的生活。這兩點分別對應了前文提到的端木蕻良追求真實性描寫的目的:批判與同情。
然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對自然主義文學的態度發生了全然轉變,批評自然主義的理由有三:第一,有過于濃重的機械決定論傾向;第二,過于強調客觀性,專注批判卻不能給出解決方案[6];第三,是自然主義對科學精神的要求需隱去作者的情感,但當時的作者被時代要求著進行價值選擇,提出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判斷[7]。第一點反映在端木蕻良的作品中便是本文討論的命運觀差異問題;第二點反映的是本文討論的“問題意識”的差異問題,端木蕻良所持的觀點在其作品中體現;涉及作者自身價值判斷的矛盾問題的第三點印證了端木蕻良宣揚“野性力量”的主題與自然主義的達爾文主義內核之間的矛盾。這三種矛盾背后的更深層原因,是自然主義對社會與人性全然悲觀的態度與中國左翼作家力求民族救亡的積極態度的不同。
參考文獻
[1] 端木蕻良.大江[M]//張中良.1931—1945年東北抗日文學大系 第三卷·長篇小說.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7.
[2] 王富仁.端木蕻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3] 藍棣之. 現代文學經典:癥候式分析[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4] 柳鳴九.法國自然主義作品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5] 馮昊.民族意識與淪陷區文學[D].濟南:山東大學,2007.
[6] 于啟宏.實證與詩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自然主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7] 樂黛云.比較文學簡明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特約編輯 劉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