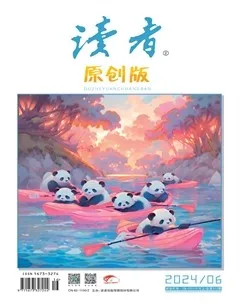少年的什錦包
蟠桃叔

一
當年,我們報社和某研究會聯手搞小學生征文大賽。我負責此事,因此和這個研究會的某人有了工作上的接觸。此人就是湯嘉禾。
那次活動,評委都是掛名的,到頒獎現場亮個相即可。什么雜七雜八的活兒都是我們報社以及研究會抽出來的幾個蝦兵蟹將干的。
那段時間,我們報社這邊和研究會那邊都是在網上接洽的,所以我和湯嘉禾彼此都沒見過,連電話都沒通過,直到頒獎那天,我們才見面。我大吃一驚,因為此前我一直以為湯嘉禾是個小姑娘,因其聊天工具的頭像是只萌萌的小白貓,把我給誤導了。湯嘉禾其實是個干瘦的漢子,比我大十來歲,穿黑色的中式對襟衫,戴黑框眼鏡,留胡子。
我一見湯嘉禾就嘿嘿笑了,湯嘉禾說我可真“喜辣”。“喜辣”是陜西土話,就是喜氣豐盈、笑臉迎人的意思。這就算認識了,我叫他老湯,他叫我小楊。
當天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頒獎結束后,人基本散去,在禮堂門口,我看見老湯半彎著腰,雙手合十,給一個女的賠禮道歉。那女的氣哼哼地翻著白眼,旁邊站著一個小個子男娃,手里捏著一張獎狀,嘴角抿著,眼珠子滴溜溜轉,看一眼湯嘉禾,再看一眼那女的。
那女的質問老湯:“你是不是耍我呢?我不忙嗎?一攤子的事撂下,一個班48個娃撂下,跑過來讓你當猴耍……”
湯嘉禾百口莫辯,臉憋得通紅,只會說:“高老師,高老師,你聽我說……”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出啥岔子了,趕緊上去詢問。見我過來,那女的身子一擰,踩著高跟鞋走了。
我問老湯啥事。原來那男娃是老湯的娃,那女的是老湯娃的老師,姓高。老湯的娃這回得獎了,高老師以為她也能得一個輔導老師獎,所以化了妝,踩了高跟鞋,牽了老湯娃的手,興沖沖地來了。這高老師準備評職稱,就缺這么一個獎。結果,他學生領了個銀獎,她啥都沒有,于是臉色就變了,向老湯興師問罪。
來之前,這高老師就知道老湯負責這活動,還專門問過有沒有輔導老師獎,老湯拍了胸脯,說有,因為按照一般慣例確實是有的,可偏偏我們報社頭一回搞這個事情,沒經驗,就沒想到這一茬。老湯和我那段時間各忙各手頭上的事,沒有仔細溝通過。但凡他提一嘴,我們這邊就把這個獎加上了,順手的事。
老湯沒有跟我們報社這邊提輔導老師獎的事,也沒提他兒子參賽的事。老湯兒子得獎,那是真刀真槍拼出來的,文章寫得確實不錯。我記得老湯兒子寫的是《記一次難忘的春節》,說親戚送了七八條魚,活的,一時吃不了,就養在衛生間的一個洗澡盆里,春節期間慢慢殺了吃。文章的結尾是“魚吃完了,洗澡盆空了,我知道,年過完了”,給人一種悵然的感覺,有一種和作者年齡極其不符的憂郁。我覺得這篇文章又高級又不應該,想了想,給了個銀獎。就憑老湯事先沒有給我打招呼說他兒子參賽了這一點,我就覺得老湯這人品性不錯。
出了這事,我很自責:“哎呀,老湯,你看這事弄的,現在要補個獎狀也來不及了。”
老湯搓手,說:“我補救一下吧,買些啥,今晚就去看一下高老師,誠懇道歉。”
二
那次頒獎典禮結束后,我和老湯居然常能見到。
半個月后,西安有個作家開新書發布會,報社安排我去采訪。去早了,現場沒幾個人,一眼看見一個穿黑色對襟衫、戴黑框眼鏡、留胡子的人,湯嘉禾,他坐得端端正正,正捧著一個小本子低頭默默地看。我走過去,和他挨著坐了。他半天才一抬頭,反應過來是我。我們兩個都笑了。
活動中,顯然是有安排的,話筒遞給老湯了,他站起來發言,拍了三分鐘的馬屁。雖然是脫稿,但可以聽出是經過精心準備的。
活動結束,我悄悄問老湯走不走。他說不急,一會兒還要合影,還要聚餐,勸我吃了再走。我急著回報社趕稿子,就走了。
沒幾天,在長寧宮參加一個活動,和穿黑對襟衫的老湯又遇上了。我真懷疑那件黑色對襟衫是他參加活動的戰袍。
活動結束,照例又是聚餐。我們媒體的記者坐在一桌,老湯和另一批人在一個桌子上。那次,坐我旁邊的兩個兄弟媒體的同行邊吃邊聊,說到高興處哧哧偷笑,我問他倆笑啥,他倆說在數今天來了幾只“會老鼠”。
文化圈的會多,不管你到什么會上,總會遇到幾張熟面孔。他們辛辛苦苦參會圖什么呢?圖領份禮物、混頓飯。這類人就是“會老鼠”。
他倆又偷偷指給我看:“你看,那個穿黑衣服的就是。”
說的就是老湯。我遠遠見他黑黑的身影,也不和鄰桌說笑,只是認認真真吃飯,站起身去夾盤子里的肉丸子。
三
后來,我換崗做了編輯,不外出采訪,于是不再能見到老湯了。我覺得,這回是真把緣分給切斷了,不想,人生何處不相逢。
有一天,是周末,我閑逛,在大興善寺門口的舊書攤上亂翻,感覺有人拍我肩膀,我一回頭,愣了一下,三秒后才反應過來是老湯。黑框眼鏡、胡子都在,但是沒有穿黑色的對襟衫,我差點兒認不出他了。
好幾年不見,我們都有些老了,都開始懷舊了,于是親熱起來,捉住手扯到一邊細細詢問彼此的近況。
老湯說他家就在附近,真心實意邀我去坐坐。我左右無事,就去了。
那是一個老舊的小區,院里多七葉樹,多斑鳩。一進門,就見一個圍著圍裙的半大小子在客廳包包子。那半大小子我幾年前在那次征文比賽的頒獎現場見過,那時還是兒童,幾年過去,已出落成少年。
少年起身喊我叔,我驚呼少年還有這本事,問是什么餡兒的。
少年說:“胡亂做的,清理下冰箱的剩菜,一把韭菜,一根茄子,一點兒豆腐干,還有半節蓮菜,剁碎了,加點兒昨天吃炸醬面剩下的肉渣渣,就包上了。”
我說:“哦,什錦餡兒的包子啊。你是個會過日子的娃。叔給你點贊。”
少年一笑,端了包子進廚房蒸去了,讓我等著,說一會兒就好了。
老湯拉我進他房間說話,還說午飯就在他家吃,嘗嘗他兒子的手藝。
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家里是沒有女主人的。而老湯也說起了他家的情況。
原來,老湯最早在高校教書,他媳婦是英語導游。后來老湯媳婦把工作辭了,去了美國,想讓老湯父子也過去。老湯辭了工作正準備走呢,沒想到媳婦出事了,人沒了。
此事后,老湯就老了,美國也不去了,一個人拉扯兒子。兒子才5歲,往幼兒園一放,老湯去掙錢。沒單位了,才知道掙錢真難。百無一用是書生,老湯也沒有啥大本事,只能在民辦高校臨時代課,也是有今天沒明天的,還抽空帶了個學生娃的家教。后來,老湯陰差陽錯進了一個研究會。研究會是個民間團體,不發工資,但是可以打著研究會的旗號掙錢。只要拉得下臉,腿勤多跑跑,見人多笑笑,還是能糊口的。說到底,老湯吃的是碗江湖飯。于是,白天就跑跑場子,打打秋風,啥活動都參加,該發言就發言,該鼓掌就鼓掌,晚上回來繼續寫稿子掙點兒稿費……
讓老湯欣慰的是,兒子是個來報恩的。說是老湯養活他,倒不如說是他養活老湯。才上小學,還沒有掃把高,就把家中大小的活兒全包了。也沒有人教,被褥臟了知道拆洗床單、枕巾、被罩,晾衣服知道沿著衣服的線縫搭,用電熨斗熨衣服知道出熱氣的口對著外面。做飯,先是會做蛋炒飯,后來就會搟面條,再后來,包餃子,蒸饅頭,蒸包子……一般的菜,西紅柿炒雞蛋、炒洋芋絲、紅燒肉什么的,那就不用說了。老湯干脆把掙來的錢都交給兒子,反正菜是兒子買的;衛生紙、牙膏、垃圾袋、襪子、褲頭,還有老湯刮胡子的刀片,也是兒子買的;家里添置個柜子、家電什么的,也是兒子做主;過年給親戚家娃包紅包,包100元還是包200元,還是兒子操心。兒子的家庭作業需要家長簽字,他自己就給自己簽了,仿老湯的筆跡,龍飛鳳舞地寫上“湯嘉禾”三個字。老湯看見了,跟兒子開玩笑,說下輩子他當兒子,讓兒子當爸。兒子笑著點點頭,同意了。
說起兒子,老湯唯有感嘆,說別人家的娃會彈琴,會編程,會外語,他娃會包包子,說著又念了幾句《紅燈記》里的唱詞:提籃小賣拾煤渣,擔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我說:“老湯,不是恭維,我看你這公子身上有靜氣,難得,以后要成氣候的。”
正說呢,少年喊開飯了。我們出來,桌子上已經整整齊齊擺上了一葷三素四個家常菜,主食是米飯,自然還有剛出鍋的包子,騰騰冒著熱氣。
我嘗了,包子好吃,菜也好吃。
我們都動筷子了,少年還在廚房忙著裝飯盒。十幾個小飯盒,熟練地裝了米飯和菜,整整齊齊地凍進冰箱,這才出來吃飯。
老湯告訴我,兒子上中學,忙,平時沒有時間下廚,就在周末給他父子倆提前準備一些飯菜凍在冰箱里,要是趕時間,拿出來在微波爐上一熱,就是一餐。
吃完飯,老湯裝了一袋包子讓我拿上,我沒敢拿,我怕這也是父子倆的預備糧,就撒了個謊,說我一會兒要去拜訪個老師,提著包子登門去拜訪,不合適。推來讓去,我只拿了一個包子,想拿回家讓我媳婦嘗一下少年的什錦包,再給她講講老湯父子的故事。
臨走的時候,少年邀請我去他房間“看個有趣的”。一進房間,看少年的書柜塞得滿滿當當,可知這是個愛看書的娃。他小學時作文得了銀獎,那句“魚吃完了,洗澡盆空了,我知道,年過完了”我還記得。問他還寫文章不,他點點頭,一笑。
少年到底是少年,原來是要我看他窗臺外空調外機上的斑鳩巢。那天,我見到了一只斑鳩,閉著眼睛似睡非睡,臥在巢里孵蛋,時不時咕咕幾聲。遠處是一排開花的七葉樹,再遠處是無云的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