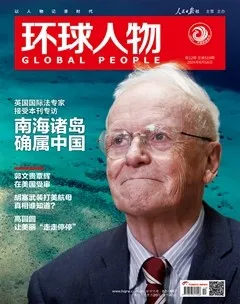追弧光的“女焊將”
許曄

胡奉雅
胡奉雅有不少“雅號”。有人叫她“焊接一姐”,因為在鞍鋼集團(以下簡稱鞍鋼),她不僅是鋼鐵研究院焊接與腐蝕研究所的副所長,也是焊接實驗室里唯一的女性。有人叫她“女繡才”,因為她曾將鋼板比作“布”,焊槍比作“針”,她研究的焊接技術則相當于為橋梁、船舶等工業(yè)重器“量體裁衣”。還有人說她是“女焊將”,業(yè)務能力強,而且特別拼。
5月初,在胡奉雅獲得“中國青年五四獎章”后,《環(huán)球人物》記者和她第一次通了電話。電話那頭,她的聲音有些嘶啞。此前半個月,她一直在出差,白天要參加封閉培訓,晚上要處理日常工作,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其間還抽空去廈門參加了一場比賽。她說:“很多研發(fā)工作不能等,不能因為我出差就拖慢進度。”等出差任務圓滿結束,她已累到講不出話來。
正式采訪是在這次通話的一周后。此時,胡奉雅已經(jīng)“滿血復活”。她在辦公室里常備速溶咖啡和保護心臟的保健品,笑著對記者說那是自己的“續(xù)命神器”。聊到工作趣事,她直言焊接時產(chǎn)生的弧光“太傷皮膚”。“我們天天穿的工服,都會因為弧光而變得發(fā)黃或者發(fā)烏。衣服都這樣,何況是皮膚呢!所以我平時就只能多擦點防曬霜。”
盡管嘴上“吐槽”,但如果再選一次,胡奉雅依然會堅定地選擇把青春與強國建設“焊”在一起,“做有意義的事,做有用的人”。
攻克世界性難題
2015年,胡奉雅在鞍鋼參與的第一個項目是國家“863”計劃課題——鈦鋼復合板的開發(fā)。這種板材兼具鈦的耐蝕性能和鋼的力學性能,同時價格只有純鈦價格的1/4,應用前景十分廣闊。
然而,在生產(chǎn)出鈦鋼復合板后,胡奉雅發(fā)現(xiàn)真正限制其應用的是焊接。“焊接時溫度高達兩三千攝氏度,鈦和鋼便會發(fā)生劇烈的化學反應,從而產(chǎn)生裂紋。通俗點說,鈦鋼復合板彼此之間焊接不上。”
2018年,正當胡奉雅一籌莫展時,一個機會擺到了眼前:鞍鋼派她去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習。“領導跟我說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其實非常猶豫。那時,我的孩子還不到兩歲,太小了。但家里人非常支持我去,婆婆和媽媽都愿意幫我?guī)蕖币灰а溃钛艣Q定抓住這次機會。孩子過完兩歲生日的第二天,她便遠赴英國,開始為期半年的訪學。她加入了英國皇家工程院、科學院雙院士負責的課題組,并多次拜訪著名的英國焊接研究所,結果發(fā)現(xiàn)在鈦鋼復合板的熔焊問題上,他們也沒有實質(zhì)性的技術突破。
胡奉雅并未因此卻步。回國前一晚,她在手機上寫下一句話:“閃耀的弧光只為鋼鐵強國!”她下定決心要突破技術難題,讓鈦鋼復合板能真正實現(xiàn)應用。立項評審時,有專家勸胡奉雅放棄:“既然基本不可能成功,你何必浪費時間和精力?”胡奉雅說:“即便不成功,我也想知道為什么不能成功。我還是想試一試,萬一就成了呢?”
此后,從研發(fā)新型焊接材料,到改造焊接平臺裝備,她和團隊一點點摸索,然而上千次的實驗都以失敗告終。一名團隊成員對她“抱怨”,連夢里都是鈦鋼復合板“啪啪”斷裂的聲音。“我們對失敗幾乎麻木了。等到成功的那一天,我們感覺好不真實,甚至懷疑是否只是一次偶然的成功。”經(jīng)過反復驗證,她終于確認她和團隊確實攻克了這個世界性難題。此時,距離立項已過去了1022個日夜。
夢想起于鳥巢
胡奉雅被很多人問過同一個問題:當年為何選擇研究焊接?
故事要從2008年講起。當時,她正在上高中,看了一部關于北京奧運會主體育場鳥巢的紀錄片。畫面中,一位焊接工程師指著一條焊縫說,這需要工人頂著高溫、連續(xù)不斷焊接38小時才能完成。胡奉雅被深深震撼:“他們太厲害了!我感覺那位工程師介紹的時候,眼睛里都有了光。”后來她又想,自己能不能去研發(fā)更先進的設備、更好的工藝,讓焊接工人可以不那么辛苦?
抱著這樣的想法,胡奉雅決定報考哈爾濱工業(yè)大學的焊接技術與工程專業(yè)。同學不理解,調(diào)侃說:“你瞅你選的專業(yè),年輕時是小焊工,中年時是大焊工,老了是老焊工,多不好聽。”家里人也多持反對意見,覺得一個小姑娘就算想學工科,也該學個“更體面”的專業(yè)。“但我的性格比較‘軸,一旦目標明確,就不會輕易放棄。”胡奉雅沒有理會外界的聲音,向父母堅定地表達了報考焊接專業(yè)的想法。“我父母沒有反對。他們都是高中老師,對我一向是‘散養(yǎng),永遠給予我絕對的信任和支持。可能也是這個原因,我比較自信,并不懼怕失敗。”

胡奉雅(右)和團隊成員在觀察焊接效果。
在哈工大學習期間,胡奉雅愈發(fā)意識到,想做好焊接工藝,就必須懂焊接裝備。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后,她前往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學習機電一體化,然而開局并不順利。第一節(jié)課,一位六七十歲的老教授站在臺上講機器人原理,講得唾沫橫飛,可臺下的她全程沒聽懂。課后,她一遍遍聽錄音,慢慢消化課堂內(nèi)容。靠這個“笨辦法”,她碩士畢業(yè)時,拿到了專業(yè)第一的成績。
導師想留胡奉雅繼續(xù)讀博,還推薦她拿斯坦福的全額獎學金,研究方向是微流體技術。但這“與做焊接的夢想離得比較遠”,胡奉雅放棄了,選擇回國入職鞍鋼,因為“這里能接觸到各個領域的大國重器”。今年6月,胡奉雅團隊全程參與的深中通道海底隧道預計將實現(xiàn)通車。此前,她和團隊成員還參與打造了我國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chǎn)權的三代核電機組“華龍一號”的安全殼。
這些年來,她始終記得剛來鞍鋼時,聽到一位老專家說,他的夢想是退休后走遍所有用他生產(chǎn)的鋼板建造的橋梁。“我就希望等我老了的時候,也可以自豪地對我的后輩說:看,這些都是我參與建造的!”
有遺憾,卻無悔
在追夢的過程中,胡奉雅也難免有遺憾。讓她一提起來就心酸哽咽的,是她在劍橋大學訪學期間發(fā)生的事情。孩子想她,卻又總見不到她,于是在視頻通話時賭氣對她說:“我不喜歡媽媽了。”她回國的那天,孩子見到她的第一反應是拽著外婆的衣角說:“阿婆阿婆,我媽媽從手機里出來了!”
“回國之后,單位給我拍了一個視頻,對我出國訪學之前準備走的過程進行了情景還原。孩子從來不讓我看那個視頻,我問他為什么,他說一看到那個畫面就疼。我問他哪兒疼,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兩歲多的孩子還不明白原因,只是‘疼了就自己偷偷抹眼淚……”胡奉雅講到這里,眼里不禁含淚。
當年和她一起學焊接的女同學,如今大多轉(zhuǎn)崗了,但她仍在堅持。她說,即便過去有遺憾,也從未后悔過。她試著更好地平衡事業(yè)和生活。不出差的日子里,她每天下午加班40分鐘,5:40準時離開單位,趕在6:05左右到家門口,等孩子從校車上下來,然后一起回家。在孩子晚上9:30睡覺之前,她所有的時間都用來陪他。孩子睡著之后,她再加班三四個小時到凌晨。
這樣的付出往往不為人知。但作為一名焊接工程師,胡奉雅已經(jīng)習慣“藏”在成果之后。“其實焊接工程師都這樣。比如大家知道雅萬高鐵的建設很難,但有多少人知道那些百米鋼軌的噪聲極低,而這些鋼軌都來自我們鞍鋼一個焊接團隊的努力研發(fā)呢?”在她看來,大眾關注不關注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崗位上作出應有的貢獻。
“我國在焊接工藝方面很強,但在高端焊材這個領域,和國外先進水平還有差距。我的目標就是打破‘卡脖子難題,爭取早日把焊材這塊做強。”如今,胡奉雅已將精力投入到深海裝備配套焊接材料和工藝的開發(fā)中。
“我最近做的一個項目,不方便對外透露具體信息,又陷入了當年做鈦鋼復合板時的狀態(tài),反復失敗。”說到這里,胡奉雅有些煩惱,但旋即又恢復信心。她說自己的人生信條是“天道酬勤”,堅信“努力比聰明更重要”。失敗了,就再試一次、兩次、三次……能戰(zhàn)勝失敗的,只有永不言棄的自己。
編輯?蘇睿/美編 苑立榮/編審 張建魁
人物簡介:胡奉雅,1990年出生于安徽,現(xiàn)任鞍鋼集團鋼鐵研究院焊接與腐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多年致力于焊接材料和工藝的研發(fā),成功破解鈦鋼復合材料無法熔焊的世界性難題。今年5月,獲得“中國青年五四獎章”,受到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