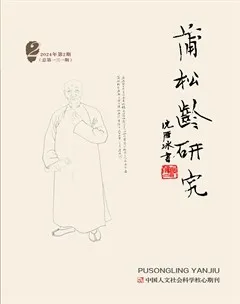論《聊齋志異》節慶意象書寫
收稿日期:2023-08-01
基金項目:山東省教育教學研究青年課題“國學經典中的民族精神融入高校課堂的方式研究”(編號:2023JXQ01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漢魏六朝雜傳敘錄”(編號:19YJA
751045)
作者簡介:李永添(1994- ),男,山東聊城人。文學博士,德州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小說史與文獻、中國古代傳記與文獻研究。
摘要:節慶,是指在某一時間節點,人們圍繞特定活動主題而組織的約定俗成、世代相傳的綜合性社會活動,屬于民俗學范疇。作為生活中較為常見的時間刻度,節慶亦會頻繁地映射在文學作品中,并在文學作品中承擔起一定的敘事功能,具備一定的文學內涵,進而上升為“節慶意象”。《聊齋志異》中有38篇文本描寫節慶意象,涉及清明上墓、上元冶游、中秋團聚等15個節慶活動,除少數僅作為“背景”一筆帶過外,多數在敘述過程中承擔了一定的敘事功能。蒲松齡善于抓住節慶意象的出游和宴聚兩個興奮點展開敘事。在《聊齋志異》中,節慶意象在主題凸顯、故事情節、人物塑造、把控節奏等方面承擔起了一定的文學功能。《聊齋志異》中的節慶民俗是蒲松齡在淄川地區節慶日習俗的基礎上,經過其他地域文化成分的合力,最終通過文人化的寫作筆法呈現出來的結果。
關鍵詞:節慶意象;《聊齋志異》;出游;宴聚;文學功能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志碼:A
節慶,是指在某一時間節點,人們圍繞特定活動主題而組織的約定俗成、世代相傳的綜合性社會活動,屬于民俗學范疇。傳統的民俗節日很多,不僅包括如春節(古時以立春為春節)、上元、寒食、端午、七夕、重陽等歲時節序,還包括一些宗教性的或地方性的節日,如浴佛節、盂蘭盆節、老子誕辰、碧霞元君誕辰等。一般而言,節慶活動多蘊含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雜糅著歷史、文化、經濟等多方面的要素,正如楊義在《中國敘事學》中云:“(中國作家)把節日視為人類與天地鬼神相對話,與神話、傳說、信仰、娛樂相交織的時間紐節。” [1]169-170節慶作為生活中較為常見的時間刻度,亦會頻繁地映射在文學作品中,并在文學作品中承擔起一定的敘事功能,具有某種文學韻味,進而上升為“節慶意象”。
節慶習俗在中國古代小說中亦是多有呈現。學界注意到此點,站在節慶角度對中國古代小說進行綜合性或個案式研究。如李道和先生《歲時民俗與古小說研究》一書,上半部分對寒食、上巳、端午、七夕、重九五個歲時節令進行考辨,下半部分論述歲時民俗生發出的小說母題。[2]熊明先生亦對唐人小說的節慶習尚與其小說功能做出了詳細闡釋,并稱“唐人在節慶中的各種習俗,在唐人小說中構成了一幅幅特有的民俗意象畫卷” [3]190;王平先生亦將明清小說作為研究對象從民俗視角進行考察,其中歲時節日是其重要部分,稱“從年初的春節、元宵節,直到歲末的臘八節、除夕,在古代小說中都經常出現,成為刻畫人物、組織情節的重要手段” [4]11。
《聊齋志異》作為中國古代小說史上著名的小說集,呈現了多樣的山東民俗風貌,其中共有38篇文章涉及節慶意象,涉及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神壽節、浴佛節等15個節日描寫。以節慶民俗的視角審視《聊齋志異》、管窺作者敘事動機、考察明清社會風俗,是聊齋學研究的重要角度。基于《聊齋志異》節慶意象的研究現狀,筆者嘗試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從整體的角度考察《聊齋志異》中節慶的時間節點及其所蘊含的民俗內涵和敘事策略。
一、《聊齋志異》中的節慶民俗風貌
《聊齋志異》中節日描寫豐富多彩,38篇涉及節慶意象的作品中既包括春節、上元(元宵、元夕)、上巳、寒食、清明、端午(端陽)、七夕、中秋、重陽、中元等傳統節日,還包含佛教的盂蘭盆節、浴佛節和地方性民俗節日的神壽節、天壽節、海神節等。其中,清明、上元和中秋出現頻率較高,分別為12篇、5篇和5篇。
(一)清明上墓
“清明”作為二十四節氣之一,最初只是作為節令符號存在,本與墓祭無關。墓祭最初分為春、秋兩祭,只是貴族小范圍內的家庭活動,并未形成風俗。經過南北朝時期,墓祭逐漸與寒食聯系起來,形成“寒食墓祭”的風尚。《唐會要》卷二三:“開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世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用拜埽禮,于塋南門外奠祭撤饌訖。泣辭,食余于他所,不得作樂,仍編入禮典,永為常式。”同樣,《舊唐書》卷八《玄宗》亦云:“(開元二十年)五月癸卯,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恒式。” [5]198可以發現,在玄宗時期,寒食墓祭的習俗最終以國家政令的形式確定。由于寒食、清明二節在時間上緊密相連,民間習慣性地將二節的習俗混淆,故而清明與墓祭掛鉤。唐時已出現寒食、清明時期墓祭現象,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云:“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壘壘春草綠。”唐后,清明墓祭的風俗才逐漸興盛,如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七載:“寒食第三節,即清明日矣。凡新墳皆用此日拜掃。” [6]626南宋吳自牧《夢梁錄》中亦有相關記載:“官員士庶,俱出郊省墳,以盡思時之敬。” [7]148明清時期,清明日上墓的習俗延續了宋以來的傳統,清人潘榮陛在《歲時帝京紀勝》中云:“清明掃墓,傾城男女,紛出四鄰,擔酌挈盒,輪彀相望。” [8]16
清明上墓的習俗在《聊齋志異》中也多有反映。① 蒲松齡在運用清明上墓習俗講述故事時,正是借用了中國傳統的鬼魂信仰,保留了傳統意義上的“事死如事生”的紀念儀式,寄希望于清明特殊時節將陽間所發生的事情告知于墓前,以便于去世的親人知曉。卷二《紅玉》中馮生與衛氏產子后,“抱子登墓” ② [9]278;卷二《蓮香》狐女蓮香產子病逝后,燕兒視之“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另外,清明上墓還蘊含了慎終追遠的觀念,卷七《鞏仙》中尚秀才“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值得玩味的是,在蒲松齡筆下,不僅人類有清明上墓的習俗,動物亦然。《海大魚》和《于子游》兩篇則是記述了海中大魚在清明時節上墓的傳說,《海大魚》篇云:“相傳海中大魚,值清明節,則攜眷口往拜其墓,故寒食時多見之。”而《于子游》篇則是在大魚清明節上墓傳說的基礎上生發出秀才與魚妖于子游相遇的奇妙故事。
(二)上元冶游
上元,又稱“元宵”“元夕”,與七月十五(中元)、十月十五(下元)并稱為道教“三元”日。上元張燈的習俗由來已久,或可追溯于民間開燈祈福的美好愿望,隨著中古時期佛教、道教等元素的摻入,上元節逐漸被賦予了更豐富的文化內涵。一直以來,人們傾向于上元的夜晚要素,或燈或月,以至于上元節被稱之為“夜節”。明清時期,人們在上元節不再拘束于夜間賞燈的單一活動,元宵逐漸形成了白日出門冶游、夜間賞燈猜謎的一種全天候的娛樂節日。
《聊齋志異》中的上元節涉及多次出游描寫。其中,《嬰寧》中所寫的王子服遇嬰寧的情節較為典型,其云: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游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仆來招吳去。生見游女如云,乘興獨游。
可見,王子服在母親管教之下“尋常不令游郊野”,而正是在上元節特定的時間節點,給與了王子服出游的機會。同樣,蒲松齡又通過王子服的視角看到上元節“游女如云”的熱鬧景象。而《陸判》中講述了中元節“游人甚雜”的背景下,吳侍御之女在游覽十王殿時被無賴賊尾隨,最終被殺;《封三娘》中上元節水月寺舉辦佛事盂蘭盆會,“游女如云”同樣寫出了當時出游人數之多。眾所周知,上元節為平日足不出戶的女子出門冶游提供了契機,亦為男女相遇埋下了伏筆。賞燈看花是上元冶游的重要目的,人們為了“出彩”,往往別出心裁吸人眼球。《放蝶》則是記述了于重寅在上元節為討好太守制造出“以火花爆竹縛驢上,首尾并滿”的“火驢”,最終導致“爆震驢驚,踶趹狂奔;又飛火射人,人莫敢近”的故事。當然,蒲松齡創作《放蝶》原意并非側重上元節煙花,但是通過于重寅制造“火驢”也不難揣測人們在上元節燃放、觀賞煙花的熱鬧情景。除了游玩賞燈之外,人們還喜好聚集成堆,觀看特定時期組織的“游戲”,如《王成》講述了上元節民間“鶉人”相聚于大親王府參與“斗鶉”的游戲。
(三)中秋團聚
中秋源自于古人對天象的崇拜,是上古時期秋夕祭月的風俗演變而來。中秋普及于漢,興盛于唐,宋后諸代因襲之。在中秋節演變的歷程中,“祭月”“拜月”等宗教韻味較強的儀式逐步退卻,“賞月”“玩月”等趣味性活動占據主流。中秋之夜,月亮圓滿,意為團圓,故而家人團聚是中秋的又一重要主題。中秋節除了家人團聚,吟詩賞月之外,亦會通宵達旦歡祝慶典,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八云:“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玩月。絲篁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云外。閭里兒童,連宵嬉戲。夜市駢闐,至于通曉。” [10]814
《聊齋志異》中的中秋節多以團聚為主題,將中秋節的景觀聚焦于親友歡聚的場景描寫。《褚生》中陳孝廉、劉天若在中秋節小聚場景,云“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又“過水關,則老柳之下,橫一畫橈,相將登舟。酒數行,苦寂。劉顧僮曰:‘梅花館近有新姬,不知在家否?僮去少時,與姬俱至,蓋勾欄李遏云也”。描繪了一幅中秋時節他們在小船內把酒言歡、美人歌舞的場景。無獨有偶,《彭海秋》亦是描寫了中秋月夜彭好古、彭海秋與邱生宴聚聽曲的故事。《彭海秋》描寫了中秋一夜置身兩處的宴聚描寫,最初,三人在彭好古家中,邀請西湖女唱曲,“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掖坐。衣柳黃帔,香溢四座”;后又在彭客邀請下,置身西湖泛舟賞月,“但聞弦管敖嘈,鳴聲喤聒。出舟一望,月印煙波,游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真西湖也。客于艙后,取異肴佳釀,歡然對酌”。蒲松齡巧妙地將現實中秋聚會過渡到西湖賞月聽曲,呈現出中秋夜客居在外的好友相聚的場景。《素秋》中俞恂九與俞慎中秋宴聚,其中俞恂九宴請俞慎的理由便是中秋賞月,其云“中秋月明如晝,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在宴聚中,素秋剪紙做人招待,“頃之搴簾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媼托柈進烹魚”。此外,《聊齋志異》還有《阿英》描寫中秋節夫妻“狎宴”,《郭秀才》精怪與郭秀才的中秋集會之約,都涉及中秋宴聚的風俗。
除了清明、上元、中秋之外,還有其他節慶民俗,如《偷桃》春節“演春”習俗,《吳令》神壽節“集會游行”,《恒娘》上巳節“踏春”,《晚霞》端午節“斗龍舟”,《鬼作筵》《顛道人》重陽節作“茱萸會”“登高”等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齡在描寫節慶時,并非完全按照現實生活中的面貌進行等比復制,而是經過文學加工,在敘事節奏上有急有緩,有張有弛,進而將現實生活中的節日、節令進行文學再加工,使之在呈現、表象和敘事上發揮特定的功能,上升為一種文學理論化的節慶意象。
二、出游與宴聚:《聊齋志異》節慶書寫的兩大敘事興奮點
節慶日,是一個充滿全民性和儀式性的活動節點,其間舉辦的“狂歡活動”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社會層級和原有秩序。反饋到市民階層,古人習慣于在節慶日淡化世俗倫理秩序投入到節慶盛典中來,人們或熱衷于走出家門,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參與到節慶所帶來的儀式中;或在家庭內部舉行宴會,聚集一堂,圍繞某一主題紀念節慶。
蒲松齡在描寫節慶意象時,并非是原汁原味的等比復制,而是抓住節慶意象的精髓和重點,在呈現時著重強調和刻畫出來。檢視《聊齋志異》中節慶意象書寫,不難發現,出游和宴聚是蒲松齡在描繪節慶意象的兩大敘事興奮點。在節慶的出游和宴聚中,蒲松齡為角色提供相識、相遇的機會,讓節日本身富有獨特的敘事意義。
(一)出游:
出游,通俗解釋為“出門游覽”,一般可以分之為兩類:一是游覽自然風光,如踏青、登高等;一類是游覽人文景觀,如逛廟會等。無論是觀賞自然風光,還是參與人文活動,節慶賦予了不同層級的人們外出的理由,為各種故事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契機。《聊齋志異》中關于節慶出游的現象較為普遍,以至于“游人如堵”(《偷桃》)、“游人甚雜”(《陸判》)、“游人甚眾”(《神女》)、“游女如云”(《嬰寧》)成為了節慶小說中較為常見的字眼。
明清時期,人們逐漸熱衷于上巳、寒食、清明、重陽等節慶日走出家門,進行踏青、登高等出游活動。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特意抓住人們外出冶游的時間節點,為小說中的人物創造相遇的機會,進而生發出一系列的故事。平日里受禮法或性格拘束而不喜外出的人物,也會在蒲松齡“刻意”安排下走出家門,其中《阿寶》中的孫子楚和《嬰寧》中的王子服便是此例。孫子楚是清明節被同社數人強邀外出;王子服被母親拘束“尋常不令游郊野”,上元節被“吳生邀同眺矚”。正是在蒲松齡利用節慶的便利條件,順理成章地使孫子楚、王子服外出冶游,為遇上心儀之女奠下基礎。由于外出冶游,為人物僅提供一面之緣,并不足以支配二人的感情走向,蒲松齡有時還會在文本中二度描寫節慶出游鞏固愛情。孫子楚初次見阿寶神魂顛倒,“希幸一再遘之”,此后,蒲松齡再次描寫浴佛節這一宗教性的節慶,為二人提供現實世界里第二次相遇的機會。
人們在參與節慶時期人文景觀時,則有不同。蒲松齡習慣于借助節慶時分的宗教空間來構建故事情節。作為宗教空間——一個可以短時間內聚集大量信眾舉行“狂歡”活動的地方,屬于公共空間。宗教狂歡活動一般發生在節日期間一些較為著名的宗教空間。信眾、香客人數眾多,社會身份復雜,不分高低貴賤、不分性別地聚集在一起。[11]186-195此類活動在《聊齋志異》中也有著多處體現:《阿霞》云“祠內外士女云集”慶祝海神壽,《桓侯》中“村中歲歲賽社于桓侯之廟”,《吳令》中“居民斂資為會,輦游通衢。建諸旗幢,雜鹵簿,森森部列,鼓吹行且作,闐闐咽咽然”慶祝城隍神壽節。蒲松齡將特殊節日期間的宗教空間作為一個敘事興奮點,利用公共屬性下的宗教空間作為故事發生和展開的場景進行敘事。
(二)宴聚
一般而言,宴聚是節慶日不可或缺的環節,人們通過宴聚促進感情的交流,增強節慶日的儀式感和認同感。無論是春節、中秋等象征團圓的節慶,還是清明、寒食等具有悲情色彩的節慶,宴聚都會在其中發揮舉足輕重的功能。宴聚,不僅僅是促進親友內部的一次情感交流的機會,有時也由于外人(如歌姬、舞者等)的介入,給宴聚增添別具一格的風采。蒲松齡便擅長這一寫法,通過宴聚的特殊參與者為文章增添神異光環,進而形成“親友宴聚—特殊參與者介入—主人驚奇”的敘事模式。
蒲松齡筆下的節慶宴聚,往往以節慶為由頭發端。如《素秋》俞恂九宴請俞慎的原因便是“中秋月明如晝,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闡明中秋月圓美景,寓意團圓,激起赴試入都、背井離鄉的俞慎濃郁的思鄉情感,從情理角度說服俞慎。此外,《褚生》中的劉天若亦是如此,其云:“居數日,忽已中秋。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游人甚夥,當往一豁積悶,相便送君歸。”由此可見,陳孝廉、劉天若宴聚的主要原因便是中秋節已至,而心中“積悶”和“送君歸”則是至于次要地位。《彭海秋》中的彭好古的表述則更為直白。彭好古于中秋節時,由于“讀書別業,離家頗遠”,又“岑寂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月既上,倍益無聊”,百無聊賴間邀請邱生共赴中秋之宴。可以說,唐王維“每逢佳節倍思親”式的朋友宴聚多是以節慶為發端,以節慶為理由舉辦宴聚儀式。
宴聚過程中特殊參與者的介入,更是給宴聚增添了神異色彩。《彭海秋》中彭好古和邱生宴聚期間,突遭奇異人物彭海秋打斷。通過彭海秋施展法術,三人乘仙船穿越至西湖。其中,蒲松齡將仙船接引三人的情節描繪的極為細致:
無何,彩船一只,自空飄落,煙云繞之。眾俱登。見一人持短棹,棹末密排修翎,形類羽扇,一搖羽,清風習習。舟漸上入云霄,望南游行,其駛如箭。逾刻,舟落水中。但聞弦管敖嘈,鳴聲喤聒。出舟一望,月印煙波,游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真西湖也。
彭海秋的出現為二人宴聚增添了諸多樂趣,同時,也極為吸引讀者注意,使人讀之驚奇。不僅《彭海秋》如此,《素秋》中俞恂九、俞慎宴聚期間,突然出現的素秋和青衣婢(帛剪小人)亦是讀之驚艷。
由于特殊參與者的介入,通過施展奇異的法術往往會使宴會的主人產生驚奇之感。無論是《素秋》中的俞慎、《彭海秋》中的彭好古,亦或是《褚生》中的劉天若皆是在特殊參與者施展法術之后流露出驚愕的情緒。而《褚遂良》中的舂藥翁最為有趣,趙某與其妻狐仙“值端陽,飲酒高會”,由于白兔(舂藥翁)的介入,并施展了白日飛升的方法,與會眾人在驚愕的同時也流露出懷疑猜忌、乃至扼腕嘆息的情緒。
出游和宴聚皆是節慶時期人們喜聞樂見的活動,蒲松齡將現實中的生活經驗獨具匠心地運用在文學作品中,并藉此作為敘事的“興奮點”。蒲松齡作為生活的體驗者,也只有對節慶民俗的現實經驗考察入微,才能創造性地“點石成金”,巧妙地運用節慶意象中的出游和宴聚進行敘事。檢視《聊齋志異》中的節慶意象,幾乎所有的篇目均與出游和宴聚相聯系,并由此構建故事情節、塑造人物形象等,承擔起不可或缺的文學功能。
三、《聊齋志異》節慶意象的文學功能
《聊齋志異》中的節慶意象,取源于生活,而又不局限于生活,是蒲松齡在深刻地領悟現實生活中的節慶基礎上,運用才子之筆、才子之思構建出的節慶意象。換而言之,蒲松齡筆下的節慶意象并非現實節慶生活的等比復制,而是在文學作品的主題凸顯、故事情節、人物塑造、把控節奏等方面承擔起了一定的文學功能。
蒲松齡將節慶意象作為深化主題的工具。郭沫若先生在為蒲松齡故居題楹聯,稱《聊齋志異》“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聊齋志異》中不少篇章針對當時社會風氣進行諷刺和鞭撻。如《吳令》中在神壽節“居民斂資為會,輦游通衢。建諸旗幢,雜鹵簿,森森部列,鼓吹行且作,闐闐咽咽然”,針對現實生活中淫祀風氣和鋪張浪費亂象進行無情鞭撻。《放蝶》亦然,蒲松齡描寫于重寅視生命為草芥、溜須拍馬未遂而自食其果,主要依賴于上元節放煙花的習俗。蒲松齡將于重寅制作“火驢”的故事放置于上元節可謂順理成章,巧妙地借用上元節放煙花的習俗使于重寅弄巧成拙,深化了故事本身的諷刺和抨擊力度。另外,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中評價說:“聊齋非獨文筆之佳,獨有千古,第一議論醇正,準情酌理,毫無可駁。如名儒講學,如老僧談禪,如鄉曲長者讀誦勸世文,觀之實有益于身心,警戒頑愚。至說到忠孝節義,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為有關世教之書。”《王成》通過描寫王成于上元“斗鶉”離奇致富的情節諷刺了上層社會的驕奢淫逸,并在文末提出勸世之言:“富皆得于勤,此獨得于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節慶意象還是《聊齋志異》故事情節起承轉合的轉捩點。首先,節慶意象作為故事情節的發端,如《陸判》中吳侍御之女在上元節游覽十王殿時,而被潑皮無賴尾隨并殺害。這與十王殿構成一組陰森恐怖的意象,也正是在此環境之下為吳女被尾隨提供了可能,引起后文吳女被殺害、陸判破案等故事情節。《阿寶》中的孫子楚與阿寶初相識便是在清明節踏青之時。孫子楚在同社數人慫恿下出游,參與進“輕薄少年”的隊伍,初相識阿寶便神魂顛倒、如癡如醉。清明節踏青活動為“癡人”孫子楚出游提供了合理化的契機,為后來靈魂出竅的癡情行為埋下了伏筆。諸如此類者并不罕見,如《云翠仙》中梁有才泰山廟會初見云翠仙,《大力將軍》查伊璜清明節寺廟展才等均是此類。其次,節慶意象也會成為故事情節發展的轉折點。范十一娘在盂蘭盆會偶遇封三娘并為之傾倒,“傾想殊切”“日望其來,悵然遂病”,正在范十一娘一籌莫展、問路無門之時,重陽節時分封三娘再度出現,成功地將故事邏輯線補充完整。再如《阿寶》孫子楚于浴佛節再見阿寶,《夜叉國》徐某天壽節接天王,其中節慶意象為人物的再度相遇或敘事邏輯的補充提供了合理化的依據。最后,節慶意象有時還會出現在文末,來收束故事,交代故事結局。《鞏仙》則是通過魯王“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暮”來收束故事,最終發冢,知其蟬蛻。
節慶期間,形形色色的人物紛紛登場,人物的行動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蒲松齡還習慣于利用節慶意象來塑造形態各異的人物。《云翠仙》便是記述了泰山岱廟四月份時節廟會的盛況,“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眾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在不分階級、不分性別的民俗活動中,給予登徒子以可乘之機。梁有才騷擾翠仙的場景極其具有畫面感,“詐為香客”“偽為膝困無力狀”見其狡猾,“以手據女郎足”見其下流,“亦膝行而近之”“亦起,亦出履其跡”則是體現其無賴。梁有才的一系列動作描寫,與莊嚴的宗教活動顯示出極大的行為反差。在光天化日之下,梁有才騷擾翠仙這一短時間內的場景描寫充分展現了其不怕因果報應、嗜賭好偷、無情無義的潑皮形象。《阿寶》和《嬰寧》中的孫子楚和王子服形象同樣經典,同樣是在節慶出游之際遇見心愛之人,前者“至家直上床臥,終日不起,冥如醉,喚之不醒”,后者“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蒲松齡通過兩組戀情故事的發端,活脫脫地刻畫出“為情而癡”的書生形象。
法國敘事學家熱拉爾·熱奈特根據故事時間和敘事時間的關系,將敘述運動分為四種速度:省略、概要、場景和停頓 [12]59。蒲松齡用詩意的語言描繪出的節慶意象,除了少數運用概述性的語言簡單提及之外,多數在描寫節慶意象時運用了場景式的描寫手法。敘事者在有意識地描摹節慶時期所發生的人、事、景,來延長敘事時間。《彭海秋》中眾人宴聚之際,苦無人唱曲歌奏,彭海秋召西湖女前來時,便主要運用了場景和停頓兩種敘事手法:
客默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掖坐。衣柳黃帔,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唯。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于西湖舟中喚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幸郎曲,大佳,請再反之。”女歌云:“薄幸郎,牽馬洗春沼。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空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歡會少。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客于襪中出玉笛,隨聲便串;曲終笛止。
不難發現,大部分運用了場景式的敘事手法,偶爾運用停頓。其中,敘事者通過彭好古的視覺和聽覺感觸西湖女的外在形象,此段即為停頓,或稱之為白描。蒲松齡通過細致地敘寫節慶時分所發生的人和事,使人讀之若身臨其境。
蒲松齡熟練地利用節慶意象進行寫人和敘事,可見其對于節慶民俗理解至深。筆者認為蒲松齡很大程度上受到明清時期淄川地區民間信仰的熏染以及崇尚祭祀的風尚有關。然而,蒲松齡對于節慶的理解和感觸又不局限于淄川地區,如《吳令》中的神壽節、《桓侯》中的鄉村社戲、《阿霞》中的海神壽以及《云翠仙》中的廟會等均是淄川之外的節慶民俗。可以說,《聊齋志異》中的節慶民俗是蒲松齡在淄川地區節慶日習俗的基礎上,經過其他地域文化成分的合力,最終以文人化的寫作筆法呈現出來的結果。
參考文獻:
[1]楊義.中國敘事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李道和.歲時民俗與古小說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3]熊明.唐人小說與民俗意象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王平.明清小說與民俗文化研究[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6.
[5][后晉]劉昫,等,撰.后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6][宋]孟元老,撰.東京夢華錄箋注[M].伊永文,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7][宋]吳自牧.夢梁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
[8][清]潘榮陛.歲時帝京紀勝[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9][清]蒲松齡,著.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M].張友鶴,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0][宋]孟元老,撰.東京夢華錄箋注[M].伊永文,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11]李永添.明清小說中宗教空間的文化蘊涵與敘事策略——以《聊齋志異》為例[J].中國傳
統文化研究,2021,(1).
[12][法]熱拉爾·熱奈特,著.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M].王文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90.
The Writing of Festival Images in Liaozhai Zhiyi
Li Yongti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Dezhou University,Dezhou 253023,China)
Abstract: Festivals refer to comprehensive socia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people around specific activity themes at a certain time point,which are conventionally established and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y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folklore. As a common time scale in daily life, festivals are also frequently reflected in literary works and play a certain narrative role in literary works, possessing certain literary connotations and rising to the level of “festival imagery”. There are 38 texts in Liaozhai Zhiyi that depict festive imagery, involving 15 festive activities such as the tomb of the Qingming Festival,go sightseeing of the Shangyuan Festival,and the Mid Autumn Festival reunion. Except for a few that are only briefly mentioned as “background”,most of them play a certain narrative role in the narrative process. Pu Songling is adept at capturing the two exciting points of festive imagery,travel and gatherings,to unfold her narrative. In Liaozhai Zhiyi,festival imagery plays a certain literary role in highlighting the theme,plot,character shaping,and controlling the rhythm. The festive customs in Liaozhai Zhiyi are the result of literary writing style,which is based on the festive customs in the Zichuan region and combined with other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Key words: festive imagery;Liaozhai Zhiyi;go sightseeing reunion;literary function
(責任編輯:景曉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