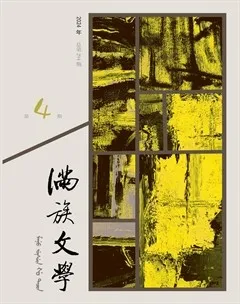工業題材小說創作與工業文化
張祖立
在當代文學作品長廊,盡管也有過一些較好的工業題材作品出現,但相對于鄉土小說寫作,工業題材小說的創作,總體成就并不如意,創作者和評論者對此難免有些焦慮。制約工業題材小說提升的瓶頸是什么,人們曾進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我認為,寫作工業題材小說時多考慮如何與工業文化融合起來,或許是問題的關鍵,至少是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我說的這種有文化的小說,不是一度被渲染過的“文化小說”,以簡單的文化符號和簡單裝飾過的格調寫就的那種小說。工業題材小說要有工業文化,是說小說應該在一種彌漫著工業領域的獨特氛圍和環境、能對生活于其中的人物的精神、心理產生深刻影響,并形塑人物的獨特文化模式和心理性格的小說。當然,有時這種工業文化甚至對小說文本形式都會有一定影響。在這一點上,鄉土小說的成功給我們以有益啟示。優秀鄉土小說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與鄉土文化的有機融合。鄉土文化的深厚底蘊,賦予了作品豐富的內涵,也給予人們寬廣的闡釋空間。如此,成功的鄉土小說,刻印著深摯的文化印記。但簡單說來,大致就是文化精神、文化模式、文化載體。小說《白鹿原》是將敘事比較“完型”地融進一種農業文化之中的寫作。在傳統的鄉土中國,“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秦暉《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與其變革》,第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白鹿原》的豐富文化載體或符號如關中的風俗、生活圖景、語言、建筑乃至白鹿的傳說等,不僅僅給讀者帶來閱讀上的美感——當然這也很重要,更浸潤著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具有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息。其中由朱先生擬寫、族長白嘉軒帶頭遵循的“鄉約”,大家議事聚集的祠堂,作為傳統文化的具體形式和符號,深深影響制約著白鹿原上的鄉民,體現著鄉土中國的宗法形態。“緩慢的歷史演進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為鄉約族規民俗,滲透到每一個鄉社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族,滲透進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結構。”(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2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鄉民有著作為人的個性,也有著明顯的“鄉約”影響下的一些相同的穩定的心理趨向,也折射著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文化模式。中國農民的文化心理躍然紙上。在文化精神表現方面,作者不做簡單回答和判斷,而是通過呈現儒家傳統在白鹿原的影響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忠實執行與不斷被撕裂解構的糾纏狀態,體現著作者對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命運的深層思考。再如沈從文的小說,故事多是發生在儒家文化未能深入影響到的湘西世界,在那里,作者看重的是真正自然狀態下的生命形式,是對原始生命力持有的肯定態度。他認為生命首先應是健康、自然的,人在生存過程中,要擁有生命的根本權力如獨立、自由和忠貞愛情等。在這種精神影響下,相互愛戀的湘西人在大自然中的約會,自然發生性關系,釋放著健康的生命本能和生命之光。同樣他們也會為愛情、自由輕易去死,展現出“生命的一種最完整形式”。在這些特定的湘西文化世界中,每個人物都演繹出令人心靈震撼的行為和精神。汪曾祺的《大淖記事》《受戒》等也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文化氛圍中出色完成的敘事。這些優秀作品,無不蘊含著獨特的地域文化,或者說鄉土文化。故事情節、人物性格、作品主題等等,都與一定的文化模式息息相關。
文化模式是需要格外關注的。文化模式概括說來是一種共同文化之下的長期存在的、各成員普遍接受認同的文化結構。在一種文化中,人們往往選擇有共同社會價值趨向,這些趨向性的選擇包括對待生死、婚姻、家庭等的方式,關于生活、社會各個方面的規矩、習俗、禮儀等。文化模式能夠通過社會制度、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體現出來,也能夠在工作習慣、飲食、服裝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表現出來。因此文化模式在一個相對特殊、獨立的環境和領域中,往往可以通過其中的人物具體、生動地演繹出來,最終成為一類人物的特殊文化心理和精神。人類有史以來的文化模式大致先后經歷了原始社會的文化模式、傳統農業文明的文化模式、現代工業文明的文化模式、后工業文明的文化模式。農業文明模式以經驗主義為基礎,充斥大量豐富的農耕社會的經驗、常識、習慣、習俗等文化要素,同時還殘留、延續著原始社會的一些圖騰崇拜、萬物有靈觀念的碎片和記憶,因而具有獨特的敘事上的“返魅”效果。中國作家最有心得的寫作是鄉土文學,這是因為他們對農業文明懷有的深厚感情和經驗積累。現代工業文明的文化模式以理性和科學為基礎,更多地體現著人類的理性精神、契約精神、人本精神。后工業文明的文化模式則是對處于急劇變化的、以知識和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時代的一種概括,反映了人類普遍的、極其復雜多變的文化心理。由于工業化、后工業化推進的時間、推行方式及中國特殊國情諸原因,中國的作家普遍未能形成關于工業和后工業文明的文化模式,或者說,人們對于工業文化的理解遠沒有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理解那么深。依此,回望一下中國工業題材小說創作,對工業文化的忽視或弱化,是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工業文化的精神是什么?這種精神之下的文化模式是什么?文化模式在體現特定的工業領域或工廠里,是如何影響著工廠里的人,形塑著工人的文化心理或職業性格?在小說中如何描寫各類工業文化符號(機器、廠房、車間、工作場面、家庭生活場景等)并能讓這些符號、景觀與人物塑造形成有機的對應關系,或者能形成敘事上的修辭效果?這些都很值得細致思考。
在談論工業小說時,陳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那篇《一天》被嚴重低估或忽略了。作品寫了工人張三一天的上班經歷。天還沒亮,上班的張三半閉著眼睛,帶著媽媽準備的飯盒,穿戴著父親留下來的棉襖、圍巾,走過竹頭樓梯,走在弄堂石頭路上,走到前面馬路轉個彎有軌電車的軌道。這時女人們拎著小菜籃出來買菜了。張三一直走到廠門口,看看門房間里的電鐘,知道自己今天早了十二分鐘。他把沖床又揩了一遍,坐在當初師傅留給他的光滑的高腳凳上,賣力地沖起別針頭子來。他從來不貪得太多而沖出壞的別針頭子來。吃完中飯后上過廁所就回到高凳上坐上一會兒,很高興地看著滿筐的別針頭子。徒弟把他從高腳凳子上拉起來。大家敲起鑼鼓送他離開工廠了。大家在閣樓上他家坐了一陣,吃了根香煙就下樓了。兒媳婦回來了,在做小孩的衣裳。他把老婆照片上的灰揩了一揩。父親活著的時候告訴過,沖床工到老了還有十只指頭是非常難得的。想到這張三高興起來了。在寫張三一天上班的過程時,小說在不同敘事環節進行了時間切換。如寫女人們拎著小菜籃到菜場買菜時,轉換成自己妻子買菜的情境,寫“早了十二分鐘”一下子轉換到眼下上班的最后一天,寫退休回家時寫到兒媳婦做衣裳和他抹老婆的照片上的灰。于是,張三的一天上班經歷就成為他一生的經歷。當初人們更多是從小說技巧和手段方面進行評價,若從小說與工業文化關系的視角看,我們能從中看出一些很值得今天格外重視的東西。小說中大量重復性的寫作,似乎體現著一種荒誕,但也是對工廠工人一生工作特點的高度濃縮和提煉。也許有人會說是寫出一個人一生的平淡和無聊,但若理解了工業文化的深刻內涵,我們會對“小人物”產生不一樣的理解。英勇豪邁的行為固然是英雄,但一個人能一生堅持著簡單和重復,何嘗不是一種豪壯!張三和那個不停地往山上滾巨石的西西弗斯一樣,具有重要的修辭意義。陳村曾說在《一天》中,“我想寫時間對于人的意義,想寫人由于時間產生的某種感覺”。這是對工業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一天》的敘述瑣細繁復,一直和固定的時間、地段聯系,寫出了工廠工作節奏和工業文化的某些本質特點。以機器為載體的工業文化聚集的關于時間、節奏、紀律規定,深深烙印在老工人張三心里,形成一種自覺和穩定的心理趨向。張三到老了還有十只指頭,這是對一生敬業、紀律嚴明的工人特殊心理與性格的真實寫照。斑宇在《盤錦豹子》中寫的一個場面很有深意。在印刷廠上班的姑父孫旭庭,沒有規范化操作,被他親手組裝的印刷機卷進去半個胳膊,“當時像被電打了似的,腦袋是蒙的,也不知道疼。整個人在空中翻了半圈,像一位吊環運動員,向后翻騰一周半再接轉體,最終優雅地倒在紙槽里,半邊臉貼在尚未裁剪的書頁上。他聽見旁邊很多人在喊叫,因為不知是死是活,也不知骨折的具體位置,沒人敢輕易搬動,他就以如此奇異的姿態在紙槽里待了大概二十分鐘。他說,那是他第一次認真閱讀自己每天印的都是什么東西,那段文字的標題是《為什么他們會集體發瘋》,里面記載的是一個叫帕爾托的法國人……。這個故事他沒有看全,孫旭庭后來遺憾地跟我說,他很想知道帕爾托和約瑟的結局,也想知道到底為什么發瘋,但故事的下半部分已經超越他視力能及的范疇,而當時他的胳膊還在機器里,沒法翻頁,而脖子又實在是無法動彈。”一場事故畢竟是悲劇,原因是工廠效益不理想,妻子不安心與其生活,導致姑父精神不集中。但這段描寫分明有喜劇和荒誕色彩,姑父在幾個連貫類似體操動作之后,竟然以受傷之軀在尚未裁剪的書頁上認真閱讀紙上的故事。一個曾經有過理想抱負、屢屢遭受挫折卻依然認真對待生活的工人的精神狀態和心理,通過此種滑稽而辛酸的場景深刻揭示出來。機器是人組裝的,應該受人的控制,但人需要按照機器的節奏工作,否則人就無法控制機器甚至被機器弄傷。小說在人與機器的關系描寫中表現人的工作狀態,進而探尋人的精神世界,把工業文化成功融入了進來。也因此成就了小說。
雙雪濤的小說《心臟》也值得研讀。“我”的父親是位噴漆工,工廠倒閉之后,換了一家工廠做噴漆工。父親家族有心臟病歷史,是隔代有病。父親每天早起練功兩個鐘頭,睡覺前再練一次。在臥室,一次一小時,招式順序沒有變化,時間誤差不過兩分鐘。不打拳的時候心里走拳,睡覺的時候都在打拳。最后一次發病時,醫生診斷說,父親的心臟應該已經無法工作了,人應該已經沒了,但他竟然還活著。在駛往北京的救護車上,父親左手上埋著針頭,一動不動,右手食指夾著一個夾子,連著顯示屏。他用拇指把食指上夾子褪掉,然后五根手指依次敲打著床沿,一遍一遍,像彈鋼琴,沒有停下來的跡象。緊接著反過來,從小指開始,最后到拇指,如此這般十幾遍,然后試圖把食指放回。凌晨五點多醒來,說,今天還沒有打拳,從被子里鉆出來,站在地上開始打拳。打了二十分鐘,坐了下來,說,后面的忘記了。他說,我的一生就這么過去了。你扶我一下。他順勢抱了抱我,在我耳邊說,再見了,我們就走到這兒吧。路上小心。說完,他躺平,伸手把被子給自己蓋上,發出了兩聲輕微的咳嗽之后,停止了呼吸。父親的心臟病是一種宿命,但他沒有向命運妥協低頭,一生當中以意志和恒心在和命運博弈。他冷靜沉著,不慌不忙,一輩子用持之以恒的重復運動,去贏得生命的延續,顯示出一種超然的偉大。不能不說,父親這個形象,與經過歷練的工人階層或工人群體,在文化精神方面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
寫工業題材小說,意味著對工業文化載體符號的關注,這是營造顯示氛圍和工業文化的基礎。對于工廠和工人的工作、生活環境的方方面面的景觀和符號,作家都要細加留意。新中國成立初的工業文學曾一度熱衷于對濃煙滾滾的煙囪、轟鳴的機器以及熱烈的勞動場面的描寫,體現著對現代化符號或載體的新鮮而陌生的心情。同時核心故事往往聚焦于某一具體工程、項目和任務完成過程的敘述,急切直接強化著對于工人的群體精神風貌的呈現。八九十年代的工業題材小說,突顯出對一些工廠的特殊場面的描寫傾向,如企業家在會場上的慷慨激昂講話場面,如工人參加工廠知識競賽場面,如數千面臨下崗的工人聚集一起討要說法的場面,以及新世紀以來的荒蕪的廠區、銹跡斑斑的工廠大門、工人家屬所住的冰冷住屋,等等。但總體看,對工業風景和符號的描寫多停留在表面上,沒有真正與工業文化緊密聯系起來。寫工業題材小說,意味著對工業文化模式的深度關注。如前所說,這種文化模式具體到特定環境,就是能描寫出體現出工人群體的特殊文化心理和性格,寫出工人形象的神韻,寫出工人性格的獨特性和魅力。而作品所要揭示的文化精神,更多滲透在作品的所有敘述之中,通過人物行為、故事內涵、文化符號的書寫體現出來。
【責任編輯】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