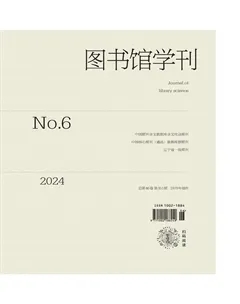圖書館基于數字化轉型的文化主體機制研究

[摘 要]隨著數智化時代的到來,圖書館的文化認同主體機制因數字化轉型而發生較大變化,表現為借助 AI及其大模型技術實現嵌入社會文化網絡結構的自我重新定位,確立了文化傳導的新型主體關系運行機制,通過三維價值賦能促進文化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的整體提升,使數智化圖書館成為社會文化網絡中的關鍵角色。
[關鍵詞]文化主體 圖書館 數字化轉型 機制
[分類號]G250.7
*本文系遼寧省圖工委2024年度項目“圖書館基于知識組織的文化傳導機制研究”(項目編號:LTB202405)的研究成果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到“十四五 ”時期要大力發展文化事業時,特別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激發文化創造力,不斷提高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和國家文化軟實力。《“十四五”文化產業發展規劃》也特別強調增強文化主體作用的重要性。基于當下的時代背景,筆者從數字化轉型的圖書館主體視角,以文化傳播論和文化空間論來把握文化傳播與認同的機制,厘清了文化沿著復制(模仿)、改變(創新)和選擇(新組合)這一基于承載主體間的傳導邏輯,指出了基于數字化轉型的圖書館文化認同主體機制,其中內含了文化認同體系的空間路徑選擇和價值提升的決策流程。旨在為中華文化的認同發展從圖書館數字化轉型的文化服務視角,探索文化認同的新機制與路徑,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提供決策參考。
1 相關文獻梳理總結
1.1 文化主體機制研究
文化主體性是建立在特定場域的文化結構關系體系,其社會文化基石在于文化的自我認同。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是指被某一群體接受并認同這一群體的象征意義和文化規范,是特定群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1]。以往人們一般認為文化群體的認同是明顯而穩定的,而今天則更多地認為其具有場景性,依賴于文化主體關系結構的時空變化。比如在中華文化的認同問題上,隨著國內外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呈現出不同的意見。早期針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化認同危機,認同派主張以文化國民的視角給予歷史文化以尊重,因為這是我們走向文明社會的基石[2-3]。至20世紀后期,強調中西文化自我認同上的差異性,主張文化秩序與道德價值的“內向超越”,人們正在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4]。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大國地位能否也在文化認同上得以確立,備受關注。一方面,有人認為大國經濟力量并未帶來文化的適時崛起,反而在全球化的文明沖突中面臨著競爭力和吸引力的考驗[5-7];另一方面,文化自信以“文化熱”和“國學熱”的形式長期以來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強烈要求通過復興中華文化來重建中國人的自我文化認同[8-9]。但是,如何增強文化的認同感,需要站在文化主體關系演化傳導機制的角度,沿著文化演進的同化、記憶、表達、傳播四階段發展路徑,通過新事物的創造性過程與傳承模仿過程相調和,來實現文化的有效進化[10]。尤其是在網絡技術及其網絡文化所帶來的行為模式及學習模式發生大變革條件下,適應新行為范式的“和諧-滿意-認同”文化傳導機制更具現實意義[11]。綜上所述,隨著新技術變革的文化演進,傳導機制對文化主體功能的有效性具有較好的解釋力,文化主體機制實際上是在對文化繼承基礎上的協同創新發展過程。
1.2 圖書館在數字化轉型的文化空間場域中的主體功能研究
根據空間三元理論[12]、第三空間理論[13]和數字空間理論(Grieves,2002)的觀點,圖書館在數字化轉型的文化空間場域中其服務職能將不再僅僅體現在物理層面,還需打通精神空間、社會空間和虛擬空間,進而實現文化價值和情感價值的統一。為了更好地滿足用戶及社會需求,圖書館需要探索創新資源的組織和共享方式,豐富文化和精神內涵,增強互動和交流屬性,提升空間的體驗感和吸引力,使其成為一個集知識、學習、文化和社交于一體的空間開放主體,釋放更大的知識價值和創新潛力。伴隨著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等現代科技應用的擴展與深化,促成了數字文化空間的形成,并逐步以新的數字技術范式,構建了有別于傳統物理空間的虛擬文化空間,這種文化空間的結構性大轉型推動了文化服務供給的大轉換,使圖書館的文化服務主體模式不斷創新[14-16]。隨著數字化轉型的深入,從圖書館社會文化空間價值出發,要求圖書館員的空間服務管理能力不斷增強,包括空間知識維、空間方法維和空間實踐維的服務素養,以期以新的數字化視角促進圖書館重構其文化主體功能和空間價值定位[17-18]。數字化時代,圖書館以數字賦能實現基于數字技術的服務設施升級、服務體驗升級、服務方式升級和服務范圍擴展,能夠實現多維度提高用戶體驗價值的目標[19]。從國家文化空間治理優勢培養角度看,圖書館應該在參與文化公共空間建設、擴大文化空間輻射范圍、基于第三空間理論創新文化服務內容等方面強化服務功能[20]。與此同時,城市轉型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現為文化軟實力的提升。承載著城市文化系統的秩序格局和活力源泉的諸多載體,以物質、交互和精神3個層面立體展開,其中圖書館數字化轉型的城市文化節點價值越來越重要[11]。特別是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整體環境變化,使得高校圖書館急需適應新文科、新工科、新商科等新型學科發展趨勢,致力于打造多元文化空間、跨界融合的“圖書館+”的合作模式,構建高校圖書館數字資源共享生態系統及其生態位[22]。
2 主體機制理論模型的構建
數字化轉型后的圖書館在文化主體的認同機制中處于核心地位。眾所周知,“文化空間”或“文化場域”(Culture Place),是指在一定的時空尺度中文化要素及其互動作用的體系,或者稱之為一定周期的文化活動領域,是一種時空伴隨的文化實踐復合體。文化空間運行機制是由不同文化承載主體間協同有序的活動過程,其中包括物質要素、關系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結構化協同演進。隨著圖書館數字化轉型的進展,必然產生數字虛擬空間的活化與重整,實現虛擬文化空間的充實與擴展,進而豐富文化空間中結構、情感、交互等的多元互動與融合,形成特定的文化魅力和生活活力。基于“文化傳承-數字化賦能-圖書館特定主體空間功能演進”的理論框架,作為文化內核的“優秀文化基因”成為互聯網、數字化時代一個活躍的媒介。自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互聯網技術尤其是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中國元素”的文化“基因”在圖書館數字化轉型中得到了廣泛而深遠的傳播,形成內容與途徑優化匹配的高效傳導機制。作為文化認同場域主體之一的圖書館,也在自身的數字化轉型中不斷強化在中華文化認同方面的功能創新,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空間效應。基于相關理論及圖書館數字化轉型現實,筆者構建了一種基于數字化轉型的圖書館主體視域下文化傳播、認同機制的邏輯框架。
2.1 數字化轉型前后圖書館的身份定位
數字化技術的大發展及其創新應用,導致人們的行為模式和學習習慣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也導致圖書館自我身份認定上的躍遷。具體而言,可以歸納為六大方面的根本性轉變(見表1),分別是主體角色、服務對象、服務流程、功能性質、資源性質和目標設定。主體方面從原來的局限于單位內的獨立主體轉向社會網絡關系中的主體嵌入,今后會側重于自我的社會定位;對象方面不再局限于內部對象,還要面向外部或社會對象;流程方面不再是傳統的圖書資料信息的匯集提供這種固化服務流程,而是個性化、多維度的數字化服務流程;功能方面不再是簡單的輔助學習研究功能,而是旨在賦能學習、研究、解決問題的創造性功能;資源方面不再是單位占有的封閉性資源,而是開放共享的社會性資源;目標方面不再是傳統固化的單一服務目標,而是基于問題的價值驅動下的多元化目標。
2.2 圖書館基于數字化轉型的文化主體機制理論模型
圖書館數字化轉型前主要擔負著信息、知識的匯集、提供角色,而數字化轉型后這一傳統角色將發生重要變化,從原來的信息、知識中介角色轉變為數據、信息、知識、思想的交流變現樞紐角色。與此同時,圖書館的文化傳播、認同主體地位也日益凸顯,構成文化主體機制中的核心主體之一,進而形成了圖書館的文化認同傳導功能和文化賦能價值功能的統一,即圖書館基于數字化轉型的文化主體機制模型。傳統的圖書館文化主體傳導機制與數字化轉型后的圖書館文化主體傳導機制的對比演化見圖1。
數字化轉型后的圖書館主體傳導機制由三大功能模塊構成:第一個是技術工具的基礎模塊,構成數字化的技術基礎;第二個是交互體驗的應用模塊,構成數字化的行為生成;第三個是精神提升的價值模塊,打造數字化的目標體系,旨在優化認知境界。三大模塊功能體現了圖書館數字化轉型的垂直一體化服務流程,實現從數據到知識、再到文化、直至思想品質的全生命周期學習目的。基于這種數字化轉型后圖書館垂直一體化服務傳導功能,遵循文化認同傳導中“認同-滿意-和諧”的“知行”合一進路,達成“共情的認知同化”“學習感知記憶深化”“影響表達的行為內化”“關系傳播的空間化”這樣的系統機制,并以此實現文化空間價值的有效開發。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圖書館在發揮文化傳播、認同作用的同時,擴展和深化的文化空間價值開發,可強力地反饋和作用于圖書館這一核心主體,二者之間通過這樣的互動分享實現相互賦能,并伴隨著數字化的未來發展,使圖書館在文化傳播、認同層面的功能地位不斷得以強化。
3 案例驗證:國家圖書館與百度的戰略合作
隨著數字化社會轉型時代的到來,圖書館數字化轉型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數字圖書館身份的確立,實現圖書館傳統身份的轉換,更多體現為互聯互通的公共服務功能的開發與拓展。這種文化主體機制運作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國家圖書館與百度的戰略合作運行機制。為了實現圖書館在數字化時代公共文化服務的主體功能,建立起圖書館與社會公眾密切交流的網絡,借助百度的AI技術應用能力,增強大語言模型在推進圖書館智能化應用服務,提升公眾文化服務品質,促進國家級文化資源和知識服務智能化,強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能力。具體而言,這一合作模式主要是基于圍繞數字化共生戰略的文化主體協同機制(見圖2)。從國家圖書館的文化主體機制角度來看,國家圖書館借助百度“文心一言”的大模型學習能力,以其豐富的國家級館藏數據深挖文化資源,通過基于技術的基礎模塊,實現理解、生成、邏輯、記憶、共情的文化傳導效應,為文化傳承、社會進步發揮自己的文化主體力量。通過與百度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相互賦能,共享優質資源與技術,讓AI技術與圖書館深度融合,激活圖書館的文化資源價值,使國家圖書館在更大的社會空間尺度上成為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智慧的主導者角色。
圍繞國家圖書館這一文化主體作用機制,我們看到圖書館數字化轉型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的使命,一定要適應未來數智化的大勢所趨。在國家圖書館與百度的戰略合作案例中,可以梳理出其中的文化傳播、認同傳導機制。首先是戰略設計要求,即數字化戰略要求圖書館數智化體系與AI應用的企業服務平臺進行深度戰略合作。其次是相互賦能,發揮各自的優勢,在圖書館方面形成智慧圖書館體系,強化其組織、加工、存儲、傳播及服務的五大主體功能;在企業方面(市場化技術開發主體)就是增強生成式AI的全社會體驗能力,也就是理解、生成、邏輯、記憶這四大核心能力。最后是共同實現對社會公共文化價值的開發,形成文化認同,打造和諧社會,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
4 結論與展望
數字化時代的圖書館已經從傳統圖書資料和數據信息載體向知識服務的數智化主體轉型,在國家文化治理環境中處于特殊的核心主體地位。首先,挖掘優秀傳統文化并肩負起文化認同的責任,是圖書館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增長點。作為新時期社會文明發展標志的優秀文化認同,其主體推動力離不開圖書館的主體作用機制。其次,圖書館的文化認同功能在今天的數字化時代得到新的發展,表現為借助市場化主體的數智化技術賦能,通過數字化轉型后的數智化圖書館垂直一體化服務功能,深化并拓展社會文化價值的空間開發。再次,通過社會文化網絡的主體間合作,遵循文化空間傳導機制的運行規律,已經形成了具有指數增長趨勢的文化傳播與認同成效,技術與精神維度上的互動促進機制得以不斷成長和成熟。最后,以數字化轉型的圖書館系統性價值服務為業務流程,建立起文化傳播、認同的接受、協同、共生、提高的“知行”邏輯路線,使新型圖書館的文化主體地位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得到加強和提升。
大模型數字化時代會使圖書館轉型為社會文化體系中的一個核心節點和關鍵主體,其功能定位將不再是知識資料的供需樞紐,而是數據、信息、知識和精神的創造輸出主體之一。未來數字化轉型的圖書館其主體功能將是知識資源的交流體驗中心和價值賦能中心。一方面,圖書館的公共文化資源性質會進一步社會化,另一方面,圖書館在智能化合作網絡中其社會服務價值體系得以確立,成為創新的一個關鍵主體。新時期的圖書館建設勢必要求對其管理要素中人、技術、規范、流程、用戶等進行重新定位。
參考文獻:
[1] Collier,M.J.,Thomas,M.Cultural identity:An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J].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988:99-120.
[2] 錢穆.國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3]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M].臺北:三民書局,1992.
[5] 曹慧,張妙清.認同整合:自我和諧之路[J].心理科學進展,2010(12):1839-1847.
[6] 董莉,等.心理學視野中的文化認同[J].教育文化論壇,2014(6):134.
[7] 黃永林,李媛媛.文化強國戰略背景下的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J].理論月刊,2022(3):68-78.
[8] 江暢.核心價值觀的合理性與道義性社會認同[J].中國社會科學,2018(4):4-23.
[9] 項久雨.新發展理念與文化自信[J].中國社會科學,2018(6):4-25.
[10] Gabora,L.,Probing the mind behind the(literal and figurative) lightbulb[J],Psychology of Aesthetics,Creativity,and the Arts,2015(9):20-24.
[11] 范洋洋.社區共同體培育中的認同機制:基于“和諧-滿意-認同”模型下的跨文化比較[J].人口與社會,2022(6):66-78.
[12] [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M].劉懷玉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
[13] E.Soja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Blackwell,1996.
[14] 肖希明,完顏鄧鄧.治理理論與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社會參與[J].圖書館論壇,2016(7):18-23.
[15] Peukert C.,The next Wave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J].Jou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19(2):189-210.
[16] 賀怡,傅才武.數字文化空間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創新方向與改革路徑[J].國家圖書館學刊,2021(2):105-110.
[17] Mayo A,et al.Surprise amp; Delight:The Library as Cultural Space[R].UMB Digital Archive,2017.
[18] 蔣一平.公共文化空間價值視域下圖書館職業人員空間素養研究:內涵、現狀與提升路徑[J].國家圖書館學刊,2023(5):32-43.
[19] 邢磊.數字賦能圖書館閱讀推廣服務轉型升級策略研究[J].圖書館學研究,2023(9):77-83.
[20] 洪芳林,龔蛟騰.圖書館全面參與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研究[J].圖書館建設,2023(7):2-11.
[21] 索傳軍,牌艷欣.面向圖書館數字化轉型的數據架構內涵、方法與策略[J].情報理論與實踐,2024(3):27-35.
王紅梅 女,1972年生。碩士,館員。研究方向:數據管理與知識服務。
(收稿日期:2024-01-22;責編:徐向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