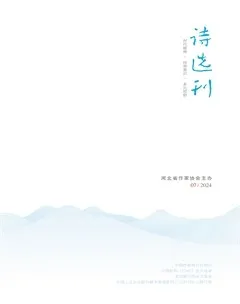閃閃發(fā)光、直入人心的明珠
2024-07-25 00:00:00王久辛
詩選刊 2024年7期
詩人普希金說:詩歌是文學皇冠上的明珠。公劉先生說;詩歌是精神的稀有元素。為什么說是明珠?又為什么說是精神的稀有元素?我的理解是,詩的語言是一劍封喉式的直抵人心的藝術。就是說,詩是以直擊人心為藝術目的的藝術。如果你的詩與人心無關,或繞開了人心,或只有所謂的語言而無他指,只有能指,那么你的這個“詩”,就要被打上引號,歸入非詩的一類。這就涉及了一個嚴肅而且莊重神圣的問題——什么是人心?人心在哪里?
在我看來,這么多年了,仿佛大家都在回避一個久違的詩歌標準:共鳴。我認為詩歌的他指,就是人心的共鳴。沒有共鳴的詩歌,我以為就是沒有能指的詩歌,至少不是好詩歌,因它沒有情感的對應物。我知道有很多很高級的表達只能獲得很少很少一部分人的共鳴,這里所謂的妙不可言,也是屬于很少很少一部分人的。從探索的意義上說,為獲得更大的共鳴而尋我先進的表達方式,我以為是屬于學術試驗——屬于成功之前的千萬次的失敗、失敗再失敗的苦苦求索。這令人敬佩,而當探索的成果一旦被智慧聰明的詩人掌握再運用于創(chuàng)作實踐并獲得成功,即獲得了巨大的共鳴,試驗的價值和意義就顯現(xiàn)了出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追求共鳴與暫時忽略共鳴的試驗,對于真正的詩人來說,都是一樣的。詩歌創(chuàng)作一直都是寂寞的事業(yè),而寫出流芳百世的經典之作,才是詩人永恒的追求。而事實上,古今中外的成功經典,都是汲得了稀有精神而直擊人心的詩人創(chuàng)作出來的。毫無疑問,大海不是明珠,貝殼不是明珠,雖然它們都為明珠的成長貢獻了力量,但是它們永遠不是明珠。明珠永遠就是明珠本身,或者干脆說罷,明珠本身就是稀有的精神鑄就的閃閃發(fā)光、直入人心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