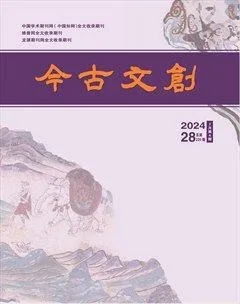神話原型視域下《等待戈多》的精神隱喻
【摘要】《等待戈多》里有著眾多意義懸置的信息碎片,筆者經過對《等待戈多》文本的反復細讀,聯系諾斯洛普·弗萊的神話原型批評理論分析其六位主要人物的圣經原型,并進一步通過原型分析《等待戈多》對當下人類精神世界整體圖景的隱喻式書寫。在《等待戈多》更深層的隱喻圖景中,戈戈/耶穌隱喻著人類的自由精神,狄狄/先知隱喻著人類的理性智慧,幸運兒/人類隱喻著人類的物質存在,波卓/假上帝隱喻著人類創造的精神偶像,戈多/真上帝隱喻了人類實現超越性的可能性,孩子/天使則是溝通超驗與現世的紐帶和聯系,戈多的不在場是對超越性精神的解構,暗示著期望得救的不可能,而以開放又循環的戲劇結尾表明未來的不確定性,宿命感的悲觀與未確定的希望交織,將根植于人本能深處的依賴沖動與超越性的自由欲望間的強烈張力詮釋得淋漓盡致。
【關鍵詞】《等待戈多》;貝克特;諾斯洛普·弗萊;圣經原型
【中圖分類號】1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8-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03
一、原型、神話與《圣經》
作為神話原型理論的集大成者,弗萊的“原型”的概念不同于創始人卡爾·榮格所認為的“集體無意識”,而是摒除人類學的影響,試圖把原型完全置于文學的視野下。弗萊的“原型”是一種固定的文學程式,它包括同類主題、結構和意象的所有要素。而所有文學的脈絡的起點一定就是“神話”。神話是無可取代的,是構成一切思維的框架和語境,神話是無法被完全驅逐的。
從文學一體的宏觀視野來看,神話就是文學最初和最根本的原型。但要注意的是,弗萊的神話原型是形式性的,包括它的語言模式、意象結構、敘事結構等。在神話中,弗萊最為推崇《圣經》,認為《圣經》在文學的視野中就是西方文學的最本原的神話原型。對于弗萊而言,正如《圣經》無法脫離整個西方文明而單獨存在一樣,其理論最主要的兩個核心概念—— “神話”與“原型”,都無法獨立存在于《圣經》以外。在弗萊的著作中,《圣經》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他認為,《圣經》是一個浩瀚的神話集,對文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包含著語言結構、意象結構、敘事結構的所有原型,為后來的文學創作提供無限的創造力和想象力。
《等待戈多》屬于文學模式循環的反諷一環,反諷意味著超感官根基的缺失,認識和感受形成了斷裂,個體與自我、他人和世界都形成了難以彌合的隔離感。反諷文學采用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指東說西”,它往往利用兩個看似不相干的意象疊加的方式,使兩者之間的聯系產生懸掛,進而形成一個流動的隱喻結構。借此外層的隱喻框架得以跨越理性思維及傳統說教語言所無法涉及的層面,并與深刻的內在精神進行對話。借由人與神之間的矛盾對抗,反思現代人內心所存在之神靈缺失以及物質需求突增的精神狀態,以及隱藏在理性生存假面下,人類實則一直生活在神話中的生存本質。
二、《等待戈多》人物的圣經原型
(一)弗拉第米爾和愛斯特拉貢:先知與彌賽亞
弗拉第米爾(狄狄)和愛斯特拉貢(戈戈)是《等待戈多》的中心人物,整部劇本中充斥著兩人大量的看似無意義的行為和對話,邏輯混亂,前言不搭后語,大量意識流的線索隨意穿插在文本中。在已有的神話原型批評分析中,兩人是人類的代表,然而筆者認為,弗拉第米爾以其審視的思想和忠誠的姿態,隱喻身份是圣經中的先知/信仰者,而愛斯特拉貢以其既低下又高貴的雙重地位和獨有的悲憫態度,隱喻身份是圣經中的耶穌/精神拯救者。
戈戈和狄狄的舞臺身份是兩個衣衫襤褸的流浪漢。在世俗王權中,權威者不可能既是國王又是乞丐;但在宗教領域,許多宗教的宗師人物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流浪漢,不管出于自愿還是被迫,譬如佛教的釋迦牟尼、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孔子,也包括圣經中記載的猶太教的彌賽亞或是基督教的基督。弗萊認為:“一方面,大多數宗教的根本目的在于重新塑造社會群體,使它們建立在一些個體影響上,如:耶穌、佛、老子、穆罕默德,或者至多一個小群體。這些傳道者以自身來表明他們代表著一個群體,而不是群體代表他們。”流浪漢的身份正是為著人可以從社會中脫離而出,真正彰顯個人的存在。
戈戈在入眠時常常重復做一種相似的夢境,但每當他企圖向狄狄述說時,卻每每遭到極度恐懼的拒絕。按照以往學者分析,二人的象征身份是人類,這顯示了人類主體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溝通壁壘,由此推斷,人類間往往拒絕真正、有意義交流的態度。這誠然是一個合理的解讀,但若進一步思索,普通的夢有什么“受不了”的呢?戈戈每每夢到便驚醒正表明戈戈的夢是不同尋常的,終于,在最后一次做夢驚醒時,戈戈控制不住地呼喊出了這個噩夢——墜落。對現實的所感所思化為一個具體而強烈的符號在夢中出現,這一令狄狄恐懼至不敢傾聽的夢境終于得以傳達給讀者,戈戈的墜落意味著耶穌的墜落。在圣經中“記載”耶穌曾從天堂墜入人間,又墜入地獄,完成拯救后升回天堂,從而完成了圓形的閉合運動。但當前此墜落,實質上體現了信仰的淪喪,象征信仰失去其神圣性而沉淪入淤泥。狄狄的恐懼正表達了對心靈信仰的不堪跌落之懼。
在一次爭吵中,戈戈說:“要么就干脆把我給殺了,像別人一樣。”
狄狄:“哪一個別人?(略頓)哪一個別人?”
戈戈:“像千千萬萬別的人那樣。”[5]101
被“千千萬萬別的人”殺死的戈戈正隱喻著耶穌之死。耶穌是被猶太祭司處死的,但在弗萊看來,耶穌是被所有人包括基督教信徒們一同殺死的,基督教是建立在一個被當作瀆神者和社會危險分子而處死的先知(耶穌)之上的。他對抗社會,預見未來,并經受痛苦,被社會殺死。他的行動與結局表明,人必須靠自我奮斗擺脫歷史而不只是從歷史中醒來,而到目前為止的任何社會都無法接納一個完整的個體。
(二)波卓和幸運兒:上帝和人類
波卓不止一次地被戈戈指認為戈多,但每次都被狄狄反駁,語氣確鑿肯定,從而也給讀者傳達了同一信念:波卓不是戈多、波卓不是上帝。但排除狄狄武斷的否認,種種蛛絲馬跡都在暗示著波卓和幸運兒的真實身份:上帝和人類。
波卓和幸運兒的主仆關系怪異而離奇,波卓無情地奴役著幸運兒,卻又極度依賴和害怕幸運兒。幸運兒看似事事服從波卓卻不再服務慰藉波卓的心靈,因為幸運兒的不作為,波卓只能請求戈戈請求他坐下。波卓是個被寵壞了的暴君,就像上帝一樣。世事變遷,幸運兒則從主動的供養變為被動的服從,就像人類一樣。
幸運兒之姓名與境遇截然相反,名為幸運卻受著奴役,但他卻渾然不覺,反而樂在其中。簡單一個設置已是辛辣的諷刺,人類雖然追求自由和平等,自以為受到上天眷顧,但對自己和別人受到的剝削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沉溺在幸福的幻象海洋,不愿掙脫。
幸運兒因年歲極高而顯得衰老,有著長長的白發。相比波卓、戈戈、狄狄,他是如此衰老,這正象征著人類存在時間之久遠,遠超他所崇拜或信仰的偶像和領袖。但如今,人類的生命力也從春天走向了冬天,曾經生命可以自由地起舞,“以前,他跳過法蘭多拉舞、埃及舞、法國搖晃舞,快步舞、凡丹戈舞,甚至跳過水手舞。”[5]64現在卻變得衰弱蒼老,喪失活力,僵硬麻木。
幸運兒應波卓要求,辦了兩件事情。第一,跳舞。“幸運兒跳舞。他停下來。”他的舞蹈簡單到只有一個動作,一個“詞語”。對于幸運兒舞蹈的闡釋命名,共有四種視角:戈戈、狄狄、幸運兒自己和讀者。戈戈的猜想是:“《點燈人之死》”。“點燈人”從廣義的含義來看,其奉獻性和獨一性都與耶穌有相似之處。“點燈人之死”更像是一種犧牲。犧牲本質上屬于替罪儀式,在原始部落便已存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耶穌被基督教所賦予的就是“替罪羊”的價值,因此他的猜想屬于合理地以己推人,這是其隱喻身份的另一例證。狄狄的猜想是“《老年人之癌》”,狄狄下意識地認為他是因為衰老、動作遲緩,才無法起舞。它表達了一種對人類生存現狀的認知和領悟,人類沒落的根本原因不在外在的束縛,而在生命力的衰竭,感性力量的喪失,在“不再起舞”。他們兩人都猜錯了,幸運兒舞蹈的正確答案是“《網之舞》”。“他以為自己陷入了羅網。”[5]49幸運兒以為自己“陷入羅網”,隱喻的是文明的羅網。許多反思現代性問題的思想家們都像幸運兒一樣,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文明的制度中,渴望掙脫文明的束縛而重返自由。
第二,思想。幸運兒的長篇演說沒有標點,詞匯使用混亂,毫無邏輯。有學者認為這象征了現代人因接受了爆炸式的信息而導致了思想的破碎和思考能力的萎縮。筆者則試圖從另一角度出發,不著重“破碎”,而著重“統一”所呈現的信息。這段文本的書寫以上帝開始,以上帝結束。盡管其邏輯結構存在混亂,但從整體的敘述角度來看,它實質上具有一篇布道文的表現特征,諸如“耶和華在那高高的山上”。然而,預期傳統的贊美上帝之愛的頌歌相比,這段演講卻是一段充滿著殘酷無情預言的呼喊。我們在混亂的文本中抓住關鍵詞,會發現“但時間將會揭示”一共出現了4次,“不知什么原因”出現了10次,“衰弱萎縮”出現了4次,并且出現了許多物品名。如同翻譯預言的亂碼,經過分析重組,依筆者分析,此一句子所概括之含義為:時間流逝的過程中,人類在物質領域所追求的進步均無法承受時間的考驗,最終所有人事均將進入入衰敗及減毀的狀態。人類既無法了解此一現象的成因,更無力改變這殘酷的命運。這一最終歸宿使人聯想到《圣經》的末日以及時間的終結。
第二幕再上場時,波卓已失明,幸運兒已失語。波卓的失明隱喻了主仆關系的顛倒。最開始波卓掌控著絕對的權力,但他失明后,不僅難以準確鞭打懲罰幸運兒,而且難以決策行進的方向道路,實權轉移到了幸運兒手中。幸運兒的失語隱喻了行動和真正的思考將要取代浮于表面的言語。行動與言說在常識認知中是二元對立的,一方的增長必然導致另一方的消減。最開始,幸運兒不能跳舞,卻能長篇大論地演講。而現在,他不再能說話,但或許正預示著其思考能力的回歸和對自己生命的重新掌控。
(三)戈多和孩子:上帝與天使
戈多的圣經原型是上帝這一觀點已被學界進行了充分闡釋,并得到了普遍接受。需要補充的是,戈多在劇本中處于不在場狀態,其上帝形象在文本中的明顯線索,如胡子是白色的,兩個孩子為他放羊(牧羊人)等,都是由孩子傳遞的。孩子充當了戈多的傳聲筒,而圣經中的天使意象往往象征了語言交流,天使是為上帝傳賜圣經的使者,我們可以基本確定孩子的圣經原型就是天使。
三、《等待戈多》的精神隱喻圖景
神話闡釋的真正價值在現象學維度方得以展現,《等待戈多》是基于圣經原型的現代人類精神現狀的縮影。貝克特將人類這一難以言說的復雜對象進行拆解,剝離出不同的元素,并將其化為具體的分身角色,上演了這一出隱喻性極強的戲劇,在《等待戈多》更深層的隱喻圖景中,戈戈/耶穌隱喻著人類的自由精神,狄狄/先知隱喻著人類的理性智慧,幸運兒/人類隱喻著人類的物質存在,波卓/假上帝隱喻著人類創造的精神偶像,戈多/真上帝隱喻了人類實現超越性的可能性,孩子/天使則是溝通超驗與現世的紐帶和聯系。
戈戈和狄狄是一對個性迥異的朋友,戈戈喜歡自說自話、行事隨心所欲且性情陰晴不定,狄狄則相對顯得更加沉穩理智、喜歡思考講道理,二人分別是人類的追求釋放自由與追求克制理性的兩種精神追求的擬人化形象。二人徘徊在荒野之中,四面寂靜,空無一人,他們是被驅趕來的,被拋棄來的,他們也曾有過好日子,也曾有過被尊崇的時候,但現在世界變了,是人類自己拋棄了人類的自由精神和理性智慧。
幸運兒是人類的物質文明與現實存在的擬人化形象,幸運兒曾經也是威風凜凜、機巧可愛的,擔得起他的名字,但他現在卻虛弱衰老、僵硬麻木、破破爛爛像個乞丐,這正是對經歷了一戰、二戰的人類物質存在的形象書寫。幸運兒的演講初看只覺恐怖,而另一方面,意象引發的火花構成了一種不同于流俗時間的本真時間,雙雙塌陷于現在的過去與未來已經終結,現在構成了一種統攝性的同時性觀念,存在著時間的原型,過去未來統統消減,當下也就實現了永恒。
波卓和戈多的圣經原型都是上帝,但二者不可等同而語。波卓不是真正的“上帝”,只是被人創造的一個“偶像上帝”,代表著人類文明創造出的各種偶像。《圣經》譴責偶像崇拜,其譴責的正是它所使用的意象在外部世界的反映。摩西誡命曾言:“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出埃及記》20:4-5)創造并侍奉諸如波卓這樣的虛假偶像不過是人聊以自慰的謊言,是人對責任的懼怕與躲避,它們憑借著人類的崇奉和供養豐滿健碩,奴役著自愿被奴役的人們。
劇中從未現身卻存在感最強的戈多才是真正的“上帝”,或者說是人類實現超越性的可能性。《舊約》明確表明:上帝永不現身,凡見過他的人必遭受死亡。而《新約》中耶穌則表示上帝是他自己能量的看不見的源泉。上帝顯現是一個偽命題,“等待戈多”也是個偽命題,因為“上帝”非實非虛,戈多也沒有實體形象,而只有“名”。問題的重點從不是見到上帝或是戈多,而是要“打通人的個性和象征著人的個性無限延伸的神的個性之間的界限”,要使人的可能性由此得到無限的延展。幸運兒憑借崇拜想要獲取無限與超越的精神力量是癡人說夢,而只能把自己鎖死在波卓這種宗教偶像的手里。戈戈和狄狄一再等待戈多,但他永遠不會來,也不可能來,因為戈多并非獨立存在,而只是代表一種可能性。唯有戈戈狄狄重與幸運兒聯手相助,人類開始重拾理性精神,承擔起應負的責任,不再試圖有任何依靠或推脫,勇敢地面對自由,那么真正的解救才將到來。
弗萊將《圣經》中的“原罪”看成是“人類對自由的懼怕,對自由所帶來的原則和責任的懼怕”。贖罪、解救則相對的,隱喻著人類的自由、理性精神的真正實現,人對生命自身的真正負責。在戲劇的最后,波卓依然失明,戈多卻仍被等待,何時人類能不再等待戈多,使幸運兒和戈戈、狄狄相認合一呢?狄狄最終戴上了幸運兒的帽子,也許這是個好的開始。
參考文獻:
[1](加)諾斯洛普·弗萊.批評的解剖[M].袁憲軍,吳偉仁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2]Northrop Frye,Fables of Identity:Studies in Poetic Mythology[M].New York,Hareout Brace and World,1963.
[3](加)諾斯洛普·弗萊.偉大的代碼:圣經與文學[M].郝振益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4](英)詹姆斯·諾爾森.塞繆爾·貝克特:盛名之累[M].王雅華,劉麗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5](英)薩繆爾·貝克特.貝克特全集16:等待戈多[M].余中先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6.
[6]饒靜.中心與迷宮:諾斯洛普·弗萊的神話闡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法)梅洛-龐蒂.可見的與不可見的[M].姜宇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