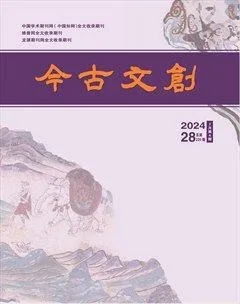淺談顧頡剛的“古史層累說”
【摘要】顧頡剛是中國近現代杰出的史學家,在歷史學領域有著豐富的研究成果。顧頡剛的“古史層累說”思想主要受到西方進化論思想的影響、胡適的影響、前人辨偽的影響而逐漸形成,該觀點對歷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了解和評價顧頡剛“古史層累說”思想的來源不僅有助于了解20世紀的史學思想,對今天史學工作者研究古史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顧頡剛;古史層累說;思想來源
【中圖分類號】K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8-007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23
“古史層累說”是顧頡剛古史研究中最重要且影響力最大的一部分。顧頡剛最早對古史的“層累說”提出見解是在他1921年寫給王伯祥的信中,表示其在搜集整理前人辨偽的成果后將做三種書,即偽史源、偽史例、偽史對鞫。“所謂源者,其始不過一人倡之……所謂對鞫者,大家說假話,不能無抵牾,我們要把他們抵牾的話集錄下來,比較看著,教他們不能作遁辭。這三種書自是終身之業,現在只是收集材料。”[1]他認為采取這樣的方式可以在中國歷史界引發一場重大革命。顧頡剛的“層累說”也確實在中國古史研究領域掀起一股浪潮。錢玄同表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一觀點精當絕倫[2],胡適更是稱贊“古史層累說”將中國史學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可以看出,“古史層累說”在20世紀的古史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開啟了古史研究的新時代。
一、古史層累說”的學術背景
鴉片戰爭后林則徐作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開始向西方學習,隨后一批早期的有識之士翻譯并介紹西方的文化知識,哲學、數學、天文學、生物學等各個領域的思想文化被傳播至中國各地,這不僅拓寬了學者視野,也指導了當時的學術研究。陳獨秀于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倡導民主與科學,隨后新文化運動以《新青年》雜志為陣地逐漸向全國傳播。在這樣打破傳統的自由的學術氛圍之下,顧頡剛突破舊思想的枷鎖,不拘一格的治學態度受到極大的鼓舞。
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進化論和個性解放觀點對顧頡剛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在相對自由的學術環境中,顧頡剛逐漸敢于表達其疑古的思想。在充分吸收西方學術思想,尤其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歐洲的歷史學方法,并繼承發展中國史學上的辨偽成果和方法,提出了“古史層累說”這一理論學說。
二、“古史層累說”思想來源
顧頡剛在《古史辨》的自序中表示崔述疑偽工作、胡適的科學方法、民間戲曲之觀賞、康有為與章太炎的影響是其從事疑古工作的幾個重要支柱。由此可見影響顧頡剛“古史層累說”形成的因素大致有:近代西方思潮的影響;胡適的潛移默化;對姚際恒、崔述和鄭樵辨偽的繼承發展。
(一)西方進化論思想的影響
1906年顧頡剛離開傳統私塾教育,進入高等小學學習,開始接觸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五四運動”前夕,顧頡剛就已經受歷史進化論的影響,并對西方進化論有了一定的認識,在讀胡適《周秦諸子進化論》后在日記中寫道:“我方知我年來研究儒先言命的東西,就是中國的進化論。”[3]是年1月17日他又寫下“姑順俗言之,舊者將謝而未謝,新者方來而未來,其中不得不有共同之一域,相與融化,以為除舊開新之地;此共同之域,即世俗,所謂調和。不有此共同之域,世界決無由運行,人類決無有進化”[4]。隨后顧頡剛為闡發其對進化論之理解,分析進化論與社會思想變遷之關系作《中國近來學術思想界的變遷觀》,認為人類的進化應該是有意識的自主進化,無意識的進化只能被稱為“劣等人類的進化”。顧頡剛還將歷史進化論運用至治學之上,認為前代學者所缺乏的便是對治學的發展,這為其后來提出“古史層累說”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
(二)胡適的影響
顧頡剛曾稱:“胡適是我的引路人。”胡適最初對顧頡剛的影響是在北京大學的哲學史上,作為一名剛從美國留學回國的哲學史教師,在給學生上課時竟直接舍棄三皇五帝、夏朝、商朝,從周宣王開始講起,引得學生瞠目結舌。而顧頡剛卻對胡適先生這樣的行為表示理解,并稱贊胡先生:他具備睿智的眼光、勇氣和果斷的決斷,是一位有能力的歷史學家。他的言論無不符合我的理性思考,并且表達了我想說卻難以言表的觀點[5],顧頡剛早期的疑古思想在胡適的影響下逐漸放大。此外顧頡剛的進化論思想也受胡適的直接影響,出國留學歸來的胡適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常發表文章介紹西方各種思潮,其中達爾文及其進化論思想對顧頡剛的影響最深。顧頡剛將歷史進化論運用至治學之上,為提出“古史層累說”準備著理論基礎。
胡適與顧頡剛熟悉后,曾囑咐顧頡剛為《偽書考》標點,顧頡剛在整理該書的同時收獲良多,并堅定了其辨偽的決心。隨后顧頡剛在整理《詩》《書》《論語》時對上古三皇五帝產生了諸多疑問,為此顧頡剛查閱諸多史料,并做出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在不斷地整理材料進行辨偽工作的同時完善其提出的假設,并進一步將之凝練為“古史層累說”。
(三)對前人的繼承
顧頡剛早年對清代的姚際恒非常關注,在其《古今偽書考》中將漢魏、六朝時期的諸多書籍判定為后人偽造的,這樣的觀點吸引了顧頡剛的注意,此后顧頡剛專門搜集姚際恒的著作研讀。之后顧頡剛為《古今偽書考》點讀,在標點注釋的過程中收獲頗豐,這讓其認識到辨偽工作在史學領域的重要作用,并立志維護歷史的真實性。在了解姚際恒及其作品的過程中顧頡剛也逐漸認識到姚際恒的不足,“姚君對于經傳非全持懷疑的態度,故《堯典》《中庸》并皆信為實錄。他所辨的偽,只是著作人的偽,不是著作內容的偽——徵事的確實與否”[6]。
其次崔述的治學思想也影響著顧頡剛。1923年顧頡剛在闡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時便引用崔述的觀點,“其識愈下則其稱引愈遠,其世愈后則其傳聞愈繁”,且“世愈近而史追述益遠”“大抵古人多貴精,后人多尚博;世愈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7]。可見顧頡剛對于古史更加系統且理論化的觀點是與崔述的觀點十分相似的,因此學界一度認為顧頡剛的辨偽思想是全盤接收崔述的思想而形成的,但觀顧頡剛在辨偽工作上的成就可見其是比崔述更進一步的辨偽學者,工作更加徹底,是對崔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而并非止步不前。
另一個引導顧頡剛走上懷疑古史的人是宋代的鄭樵,顧頡剛在對《詩經》的研究中很大程度受到鄭樵《詩妄辨》的啟發,此后顧頡剛辨偽的精神不斷被激發。顧頡剛評價鄭樵的疑古精神和辨偽工作的態度是其生涯中最為寶貴的,同時這樣的精神也是當時學術界所缺乏的,可見鄭樵在其心中的地位。
姚際恒、崔述和鄭樵的辨偽工作及其成果,為顧頡剛的疑古辨偽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顧頡剛在繼承前人辨偽工作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時正確對待前人辨偽的不徹底性,把疑古辨偽工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三、“古史層累說”的主要內容
顧頡剛的“古史層累說”認為古史是不斷的層累形成的。在其與錢玄同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了“古史層累說”的主要內容:“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8],并以三皇五帝為例講述,周朝人認為歷史上的中心人物是禹,到了孔子的時候又增加了堯、舜,秦代增加了三皇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上的中心人物會被“制造”的越來越多,同時人物故事也會愈來愈豐富。其最初的意思是指周秦以前的歷史,大多是經過后人編改形成的。進一步發展為我們研究歷史的過程中,不能僅關注史料所敘述的內容,對于史料所屬時代更應放在首位被思考。根據史料所屬年代,距離所述時間發生的年代越近則史料的可信度越高,反之則可信度越低。
顧頡剛以對中國傳統的三皇五帝提出質疑,打破了我們對傳統歷史的認識。顧頡剛在與錢玄同《論古史書》中簡要地論述了堯、舜、禹由來。春秋時期,根據《詩經》的內容所推斷,東周初年只有禹,由論語推斷東周末年有堯、舜,故禹在堯、舜之前。隨后史料記載秦靈公祭黃帝,后又出現許行推行神農氏,易繁辭推行庖犧氏,到李斯的天皇、地皇、泰皇,漢苗交流后出現盤古開天辟地的傳說。在其與劉掞藜和胡堇人的書信中《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中提出自己的觀點:禹有天神嫌疑,因當時神和人的界限并沒有那么清晰,又與周族的祖先并稱,因此禹越來越接近人,脫離神話。禹與夏朝也無關系,禹為動物,出于九鼎,是南方神話中的形象。堯舜禹也沒有關系,禹是西周中期出現的,堯、舜是春秋后期的,三者本沒有關系。只是禪讓制讓其聯系起來,而禪讓制度是戰國學者對當時政治形勢無可奈何而設想出來的。后稷是周民族供奉的耕稼之神,不一定是創世耕稼的古王,也不一定是周民族的始祖。否定了周文王為商紂王的臣子,這是春秋后期乃至戰國初期的引導。顧頡剛認為這都是春秋戰國的學者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所說的“謊話”,這些都揭示了我們傳統的公認的古史事實是由傳說層累締造的。
除此之外,顧頡剛認為研究古史還應該區分出信史和非信史。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提出了四條標準,即其一,打破民族一源論。中國傳統歷史強調一元的觀念而非種族觀念,而這種觀念導致了許多民族的始祖傳說逐漸融合為一。但顧頡剛認為我們對于古史,“應當遵守民族的分分合合,尋找他們系統的異同情況”[9]。其二,打破地域統一論。中國統一始于秦朝,希望統一始于戰國,縣制始于楚國,晉國繼而,秦并六國才一統。因此敘述歷史上的一統應當從戰國敘述而非三皇五帝,如果一統從三皇五帝說起就亂了步驟。故我們對于古史的研究,要將時代和該時代的地域環境對應,不能用不同時代的地域環境研究該時代的事件。其三,正確認識古史中“神人”的形象。古人對于神是沒有概念的,因此往往用人類的特征描述神。自春秋以后,文獻記載中的神人紛紛“人化”,這影響混亂后人的認識,所以對于古史要分辨哪些是真實的宗教史,那些事附會的、虛假的政治史[9]。其四打破古代黃金世界的觀念。神的“人化”,讓所謂的“王”代表這世間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所治皆為盛世,于是古代世界成了黃金世界,但翻看古書,商、周時民眾終年勞作,四處征戰,流離失所,所以學者要懂得黃金世界只是戰國后被營造出來的供君王學習的假象。
四、“古史層累說”的評價
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念是在一種全新的理論,對傳統的古史系統提出的質疑,在“五四運動”時期新的社會形勢下得到了鼓勵。最終顧頡剛在胡適、錢玄同的支持和引導下,對舊的古史系統發起了進攻,“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由此誕生。該觀點中所蘊含的:強調歷史是進化發展的;不懼權威,始終保持懷疑的治學精神;不分貴賤等等,這些史料思想在中國史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郭沫若對于“古史層累說”有“‘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確實是一個卓見之論”的高度評價。傅斯年更是將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一學說在史學中的地位比喻為牛頓在力學上的地位。
“古史層累說”影響了中國學者的“史學觀念”。余英時認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之所以能對史學界產生巨大的影響,主要就是因為“它第一次有系統的體現了現代史學的觀念”[10]。中國人有著“歷史退化觀”,認為越古老的東西越好。“古史層累說”打破了這個觀念,它將舊的歷史放置在懷疑的境地,不再一味地遵照傳統,要對歷史保持一種懷疑的態度。正如顧頡剛在自序中所說的:以前的人做學問,目光短淺,道路狹窄,只是信守前人的觀念。現在的學者知道要把學問建立在事實上。歷史是進化的,不是退化的,這一觀點被眾多研究古史的學者所接受。在顧頡剛的大旗之下,中國史學界出現了一個以“疑古”為旗幟,以考辨古史為志向的“古史辨派”。在“古史辨派”的陣營里匯聚了一大批史學泰斗,如胡適、錢玄同、童書業、錢穆等人。“古史層累說”使古史的研究從“信古”走向“疑古”,為古史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古史層累說”的提出,讓學者不僅僅只是照搬古人,更加注重審查資料的真實與否,保證歷史的客觀真實性。
但學界也有一些尖銳的評價,如劉扶黎、胡堇人。劉扶黎表示對于顧頡剛的疑古精神大為贊同,但其中疑古的例證和推想并不能使人信服。胡堇人也認為僅有堯舜之前的古史相對復雜,可能存在偽造成分,但堯舜以后的歷史還是“比較稍近事實的”。錢穆先生雖然受到了顧頡剛的“古史層累說”的影響,成為“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但在其出版的《國史大綱》中認為顧頡剛的“疑古論”過于極端。
總之,顧頡剛的“古史層累說”所彰顯的進化史觀、疑古思想、辨偽思想,對中國的古史研究所做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今天的史學工作者對顧頡剛的“古史層累說”的認識,更要保持一種客觀公正的態度。對“古史層累說”所提出的正確的理論方法當然要繼承,對于一些“矯枉過正”的東西也要修改補充,批判地繼承。
參考文獻:
[1]顧頡剛.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國歷史意見書[A]//顧頡剛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10:180.
[2]顧頡剛.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國歷史意見書[A]//顧頡剛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10:187.
[3]顧頡剛.顧頡剛日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0:73.
[4]顧頡剛.顧頡剛日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0:61.
[5]顧頡剛.顧頡剛全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一)[M].北京:中華書局,2010:31.
[6]顧頡剛.古史辨(答姚際恒著述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
[7]崔述.考信錄提要(卷上)[A]//崔東壁遺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3.
[8]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A]//顧頡剛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10:181.
[9]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A]//顧頡剛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10:203.
[10]顧潮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顧頡剛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11]黃海烈.試論顧頡剛“層累說”對中國古史學的影響[J].歷史學研究,2010,(4).
[12]韋勇強.顧頡剛“古史層累說”的形成及意義[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4).
[13]馬竹君.顧頡剛“層累說”的再審視——以大禹傳說研究為中心[J].民俗研究,2018,(3).
[14]王紅霞.《古史辨》對中國史學近代化的影響[J].濟寧學院學報,2014,(5).
[15]胡繩.顧頡剛古史辨學說的歷史價值——紀念顧頡剛先生誕辰一百周年[J].學習與探索,1994,(3).
[16]黃海烈.顧頡剛“古史層累說”初探[D].吉林大學,2007.
[17]李振宏.顧頡剛疑古史學的現代價值[J].齊魯學刊,2020,(2).
[18]白壽彝.談談近代中國的史學[J].史學史研究,1983,
(3).
[19]黃正術.重新審視顧頡剛的古史“層累說”[D].蘇州大學,2004.
[20]趙寶勝.近現代學術轉型與古史辨運動[D].廣西師范大學,2015.
[21]葛興苗.顧頡剛“古史層累說”探析[D].河北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