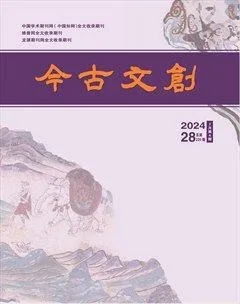郭象《莊子注》與王夫之《莊子解》相同詞句注釋的比較研究
【摘要】郭象的《莊子注》與王夫之的《莊子解》在解莊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有獨(dú)特的研究價(jià)值。《莊子注》和《莊子解》不僅是《莊子》思想的闡釋之作,也是寶貴的訓(xùn)詁材料,有待更進(jìn)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主要從字詞注釋的角度出發(fā),針對《莊子注》與《莊子解》中對《莊子》文本的同一詞句的相同注釋或相異注釋,嘗試比較研究,并結(jié)合《莊子》文本進(jìn)行探討與分析,揭示王、郭二人各自注解的合理之處。
【關(guān)鍵詞】《莊子》;《莊子注》;《莊子解》;注釋;對比
【中圖分類號】B223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28-007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8.024
基金項(xiàng)目:2023年國家級大學(xué)生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訓(xùn)練項(xiàng)目《王夫之〈莊子解〉與郭象〈莊子注〉訓(xùn)詁對比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湖南省大學(xué)生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訓(xùn)練計(jì)劃項(xiàng)目資助(項(xiàng)目編號:S202310555106)。
《莊子》,又稱《南華經(jīng)》或《南華真經(jīng)》,恢詭譎怪,風(fēng)云開闔,由戰(zhàn)國時(shí)期道家學(xué)派代表人物莊子及其后學(xué)寫就,分為內(nèi)、外、雜篇三個部分,共計(jì)三十三篇,其內(nèi)容涉及人生、社會、哲學(xué)等多個方面,具有杰出的思想價(jià)值與藝術(shù)成就。郭象,西晉時(shí)期玄學(xué)家,彼時(shí)政局混亂,老莊之風(fēng)盛行,出現(xiàn)了許多注莊者,而郭象的《莊子注》一書,清辭遒旨,以寄言出意的方式闡發(fā)義理,后又有唐代成玄英為之作疏。王夫之,明清之際頗負(fù)盛名的哲學(xué)家、詩人,與黃宗羲、顧炎武、唐甄三人并稱明末清初四大啟蒙思想家,《莊子解》為其晚年解莊之作,體系成熟,“以莊解莊”,思想廣博,捭闔自如。郭、王二人對《莊子》的注解內(nèi)容既有相似之點(diǎn),亦有不同之處。本文對《莊子注》與《莊子解》中同一詞句的異同注解進(jìn)行發(fā)掘,嘗試做出分析與探討,或有利于對《莊子》文意更深一步的解讀與領(lǐng)悟。
一、對同一詞句的相同注釋
《逍遙游》:“之二蟲,又何知!”
《莊子注》:“二蟲,謂鵬蜩也。”
《莊子解》:“郭象曰:‘二蟲謂鵬蜩也。’”
按:“之二蟲,又何知”,當(dāng)下較為通行的理解是:蜩與學(xué)鳩又哪里會知曉呢,其中“二蟲”即指“蜩與學(xué)鳩”。而在《莊子注》中,郭象卻將“之二蟲”釋為“二蟲,謂鵬蜩也”,王夫之亦遵從郭象的注解,直引郭象之言。成玄英疏:“且大鵬摶風(fēng)九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fù)遠(yuǎn)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yuǎn)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jī)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于高卑,豈有情于優(yōu)劣!逍遙之致,其在茲乎!”可見,對于“之二蟲”究竟指代哪兩種對象,從郭象“二蟲,謂鵬蜩也”的注、唐代成玄英的疏,再到王夫之對郭注的直接引用;從彼時(shí)的“二蟲,謂鵬蜩也”到今天的“蜩與學(xué)鳩”,似乎已生出較為明顯的差異。依郭象之說,“之二蟲,又何知”或可做此番理解:“何知”即“無知”,指鵬與蜩雖然飛行的距離遠(yuǎn)近不同,但都遵從著其自身的自然本性,二者都處在一種無知的無意識狀態(tài)。而無論是鵬還是學(xué)鳩,又都可以指稱為“蟲”。然而,相比于“蜩與學(xué)鳩”之說,郭象“鵬蜩也”的注解或失之偏頗。《逍遙游》一篇,講的是人應(yīng)該超越外在功名利祿的桎梏,從而達(dá)到內(nèi)在精神逍遙無礙的自在之境。文中首先展現(xiàn)了一個浩蕩廣博的奇特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對于乘著大風(fēng)展翅飛行九萬里,背負(fù)青天而無所窒礙,準(zhǔn)備飛向南海的鵬,蜩與學(xué)鳩卻發(fā)出譏笑:“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shí)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而對于適莽蒼者、適百里者和適千里者,他們目標(biāo)不同,路程不同,所需準(zhǔn)備的糧食的分量自然也不相同。搶榆枋而止的小蟬與小鳩不明白大鵬為何要乃今而后圖南,不懂得腳程不同,所需準(zhǔn)備的餐食的分量也不相同這樣的道理,往近處飛的不能理解向遠(yuǎn)處飛的,即小知不及大知也。故從蜩與學(xué)鳩的何知可引發(fā)下文的“小知”“大知”,再引出“小年”“大年”,從而展開“此小大之辯也”的論述,語意連貫,邏輯自然。對于郭象所注的二蟲謂鵬蜩也,清代著名的經(jīng)學(xué)大師的俞樾先生認(rèn)為“此恐失之”,二蟲所指應(yīng)為蜩與學(xué)鳩。依俞樾之見,后文說“奚以知其然也”,朝生而暮死的小蟲哪里能懂得何為一月,只能存活一個季節(jié)的小蟬哪里能明白何為一年,說的都是小知不及大知的“不知”,故云“之二蟲,又何知”,“其謂蜩、鳩二蟲明矣”。可見“二蟲”作蜩與學(xué)鳩解甚具其理。
二、對同一詞句的不同注釋
(一)《逍遙游》:“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
《莊子注》:“冥靈大椿,并木名也。”
《莊子解》:“冥靈,冥海靈龜也。”
按:對于“冥靈”一詞,王夫之認(rèn)為其指的是“冥海靈龜”,郭象則將其注釋為“木名”。《說文解字》中說:“冥,幽也。從日從六,冖聲。日數(shù)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莫經(jīng)切。”《廣雅》:“冥,暗也。”“冥”之本義為幽暗《漢書·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中的“其廟獨(dú)冥。”“冥”字在此處便是指幽暗之意。再看“靈”字,《玉篇》:“神靈也。”《大雅·靈臺傳》中說:“神之精明者稱靈。”“冥靈”,本來自于神話傳說,而非實(shí)際所有,并非存在于現(xiàn)實(shí)世界。唐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卷二六·莊子音義上》:“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將“冥靈”作為一種樹木來記述。三國阮籍《詠懷詩》中也有“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之語,“冥靈”作為木名的接受情況或較為廣泛。郭象將“冥靈”與“大椿”兩者歸于一類,皆作長生之木來進(jìn)行闡述。而在《逍遙游》中,除“冥靈”外,亦有“北冥有魚”“是鳥也,海運(yùn)則將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等語,皆以“冥”指稱海。《正韻》指出,“通作溟。”故“北冥”即是北海,“南冥”即指南海。南宋末年時(shí)期的羅勉道的莊學(xué)著作《南華真經(jīng)循本》中有不少名物訓(xùn)詁,其中就有提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可見,“冥靈”者,所指代的可能就是冥海靈龜。故雖兩注各有其合理性,但從對原文語境的理解下出發(fā),王夫之將“冥靈”作“冥海靈龜”注解或更有其理。
(二)《達(dá)生》:“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莊子注》:“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
《莊子解》:“齊、臍通,水之旋渦如臍也。汨,水滾出處也。”
按:《說文解字》:“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凡亝之屬皆從亝。徂兮切。”《說文解字注》:“從二者,象地有高下也。引伸為凡齊等之義。古叚為臍字。亦叚為臍字,徂兮切。十五部。凡齊之屬皆從齊。”“齊”通“臍”,有中央之意,如《列子·黃帝》:“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齊”通“臍”,又指肚臍,如《左傳·莊公六年》:“若不早圖,后君噬齊,其及圖之乎!”《莊子解》對《達(dá)生》中“與齊俱入”之“齊”的注解是“齊、臍通,水之旋渦如臍也”,此為王敔的增注。其意指漩渦的中心處狀似肚臍,比喻可謂生動。而《莊子注》中說:“磨翁而旋入者,齊也。”是說石磨的中心,即連接上下扇的地方叫作“臍”,漩渦中水流回旋,正如石磨一般,故將漩渦的中心處稱作“臍”。唐成玄英也疏曰:“湍沸旋入,如磴心之轉(zhuǎn)者,齊也;回復(fù)騰漫而反出者,汨也。既與水相宜,事符天命,故出入齊汨,曾不介懷。郭注云磨翁而入者,關(guān)東人吹磴為磨,磨翁而入,是磴釭轉(zhuǎn)也。”回到《達(dá)生》,此篇的主旨為重視人的精神作用,以臻于生命暢達(dá)之境。在《達(dá)生》的第九個寓言中,記敘了孔子及其弟子在呂梁游玩時(shí)所遇之事。孔子與弟子們觀賞瀑布,瀑布高懸,水勢浩大,激流洶涌,連黿鼉魚鱉這樣的水生生物都不敢在這附近游水,但卻看到一名男子游泳其中,以為他是因不堪遭受磨難苦厄的折磨而尋短見。于是孔子趕緊命弟子順著水流去救下那人。而那男子卻等過了好幾百步才從水面浮出,披著頭發(fā),唱著歌,一邊游至岸下。孔子驚異于那游水者的非凡的水性與本領(lǐng),詢問其蹈水是否有道,即游泳的竅門與方法,而游水者卻回答說“吾無道”,之所以能在水中練就如此本領(lǐng),只因其起初源于故常,長大后依從習(xí)性,再順從自然之理達(dá)到有所成之境。對于三個階段,可見唐成玄英疏,先是其“初始生于陵陸,遂與陵為故舊也”;再是“長大游于水中,習(xí)而成性也”;最后“既習(xí)水成性,心無懼憚,恣情放任”,于是達(dá)到“遂同自然天命也”之化境。而“與齊俱入,與汨偕出”之“齊”,便是指漩渦中心,游水者從漩渦中心處下潛至水底,又隨著涌出的漩渦一起上游到水面。無論是《莊子解》中的“齊、臍通,水之旋渦如臍也”,還是《莊子注》里的“磨翁而旋入者,齊也”,都指的是漩渦的中心處,故王、郭兩注均合理。
(三)《外物》:“其不殷,非天之罪。”《莊子注》:“殷,當(dāng)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后失當(dāng),失當(dāng)而后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莊子解》:“殷,盛也。”
按:《說文解字》:“殷,作樂之盛稱殷。從?從殳。《易》曰:‘殷薦之上帝。’”《說文解字注》中說:“作樂之盛偁殷。此殷之本義也。如易豫象傳是。引伸之為凡盛之偁。又引伸之為大也。又引伸之為眾也。又引伸之為正也、中也。”可見王夫之在《莊子解》中“殷,盛也”之注釋與“殷”字的本義一致。《說文解字》:“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從皿成聲。氏征切。”“盛”的本義是指古時(shí)候放置在用于祭祀的器物中的谷物,如《周禮·地官·閭師》中的“不耕者祭無盛”之“盛”。而此處的“盛”或作興盛之意解,同《論語·泰伯》中言,“唐虞之際,于斯為盛”中的“盛”。結(jié)合文意,可以看到在《外物》中有這樣的論述:“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文中將眼睛、耳朵、鼻子、口舌、心靈、智慧的靈敏狀態(tài)分別稱作“明”“聰”“膻”“甘”“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眾害生。”凡是道都不愿被壅滯,一旦壅滯便會導(dǎo)致梗塞,梗塞如果不能停止便會生出乖戾,乖戾的猖獗則會招致禍害。“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有知覺的事物依靠的是氣息,倘若氣息不盛,那并非是天性所導(dǎo)致的,故絕不可歸咎于自然。“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自然之理,貫穿于世間種種事物,日日夜夜也不曾停息,但人們卻堵塞自己的竅孔。正是因?yàn)槿藗儧]有順應(yīng)自然,影響了氣息的生發(fā),從而導(dǎo)致氣息不夠強(qiáng)盛,故王夫之對此處“殷”的注解符合文意。而唐成玄英疏:“殷,當(dāng)也。或縱恣六根,馳逐前境;或竅穴哽塞,以害生崖;通蹍二徒,皆不當(dāng)理。斯并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辜。”郭象將“殷”解釋為“當(dāng)也”,亦有其理。
(四)《則陽》:“圣人達(dá)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莊子注》:“所謂玄通。”
《莊子解》:“《循本》曰:綢繆,事理轇轕處。唯圣人為能達(dá)之。”
按,在《則陽》篇中,此處文段之旨為言說圣人之心態(tài)。對于“綢繆”一詞,《說文解字》有言:“綢,繆也。從纟周聲。直由切。”《說文解字注》:“繆也。謂枲之十絜、一曰綢繆二義皆與繆同也。”《廣雅》中說:“綢,纏也。”“綢”為形聲字,本是纏繞之意。《說文解字》中有“繆,枲之十絜也。一曰綢繆。從纟翏聲。武彪切。”《說文解字注》:“繆,一曰綢繆也。唐風(fēng):綢繆束薪。傳曰:綢繆猶纏綿也。鴟鸮鄭箋同,皆謂束縛重疊。”《詩經(jīng)·豳風(fēng)·鴟鸮》有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傳曰:“綢繆,言纏綿也。”王夫之引用了《循本》中“綢繆,事理轇轕處”的說法。“轇轕”為縱橫交錯之意,則王夫之對此處“綢繆”的解釋即為事理復(fù)雜糾葛,這樣的糾纏事理令人難得自在;而“達(dá)綢繆”,便是指圣人對世間復(fù)雜事理的認(rèn)識處于一種通達(dá)狀態(tài)。郭象的注解是“所謂玄通”。《老子》有言:“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河上公注:“玄,天也。言其志節(jié)玄妙,精與天通也。”可見,郭象對“達(dá)綢繆”之意的解釋或?yàn)椋号c天道相通達(dá)。唐成玄英疏云:“綢繆,結(jié)縛也。”他解釋道:“夫達(dá)道圣人,超然縣解,體知物境空幻,豈為塵網(wǎng)所羈!閱休雖未極乎道,故但托而說之也。”圣人貫通天道,將普遍之萬物合為一體,但并不知悉其中的所以然,只是出自他的本性啊。可見郭象與王夫之二人各自的注解均合乎文意。
(五)《天道》:“而口闞然。”
《莊子注》:“虓豁之貌。”
《莊子解》:“氣盈,常若欲言。”
按:對于“闞”字,《說文解字》中說,“闞,望也。”《說文解字注》:“望也。望者,出亡在外,望其還也。望有倚門、倚閭者。故從門。”《集韻》:“獸怒聲。”“闞”指虎嘯之聲。在《莊子注》中,郭象對“闞然”的注解是“虓豁之貌”。而“虓”在《說文解字》中的注解為“虎鳴也。一曰師子。從虎九聲。許交切。”《說文解字注》也說:“虎鳴也。大雅:闞如虓虎。毛曰:虓虎,虎之自怒虓然。按自怒猶盛怒也。口部曰:唬,虎聲也。虓與唬雙聲同義。從虎九聲。”《詩經(jīng)·大雅·常武》中云:“進(jìn)厥虎臣,闞如虓虎。”毛傳:“虎之自怒虓然。”《天道》一篇,主要闡述的是自然之義理。篇中,士成綺見到了老子,卻出言諷刺:“吾聞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辭遠(yuǎn)道而來愿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說自己聽聞老子是圣人,于是不辭艱辛,遠(yuǎn)道而來,腳上生了厚厚的繭,希望能得見老子。見面之后,卻說“今吾觀子,非圣人也”。“鼠壤有余蔬而棄妹之者,不仁也,生熟不盡于前,而積斂無崖。”但老子卻漠然無應(yīng),并未作答。第二天,士成綺又來詢問老子,說自己昨日諷刺了他,今日又心有所悟,這是為什么呢?老子說士成綺是“虓豁之貌”,即形容士成綺言語之專橫粗暴。王夫之的注解“氣盈,常若欲言”,則是說士成綺嘴巴虛張,好像將要說話一樣,亦顯其性格之特征,同時(shí)也契合后文老子對士成綺“似系馬而止也”的生動形容。可見,郭象與王夫之的注解雖有不同的意義側(cè)重點(diǎn),然皆符合文意。
綜上,通過比對王夫之的《莊子解》與郭象的《莊子注》,針對兩書中部分相同詞句的不同注釋或同一注釋,分析其間異同,或可幫助讀者進(jìn)一步厘清《莊子》文意,理解其中歷久不衰的深刻蘊(yùn)含。此外,在王夫之的《莊子解》與郭象的《莊子注》兩書的注解中,仍存在著一定的研究空間,有待更深入的挖掘與探討。
參考文獻(xiàn):
[1]郭芹納.訓(xùn)詁學(xu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郭象注,成玄英疏.莊子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
2011.
[3]路慶蘭.王夫之《莊子解》文獻(xiàn)研究[D].魯東大學(xué),
2018.
[4]彭再新,彭粵珊.王夫之《莊子解》用字注釋研究[J].河北科技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21,20(04).
[5]彭再新,周霞.王夫之《莊子解》語法觀研究[J].河北科技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20,19(04).
[6]王夫之撰,王孝魚點(diǎn)校.莊子解[M].北京:中華書局,
1964.
[7]許慎.說文解字[Z].北京:中華書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