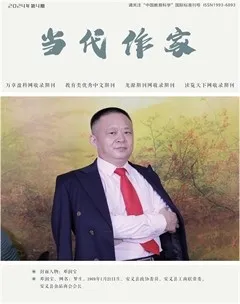三舅的小軍壺
小時候我經常去南村的三舅家玩,因為相隔幾里地,一高興連跑帶顛地一撒歡就到了。
每次去都看到三舅家的西墻上,掛著一把軍綠色的小壺,樣子很獨特,上面布滿大坑小包的,顯得很老舊。我就央求三舅摘給我玩玩,可三舅就是不答應。其實三舅很疼我,要什么都舍得,可就這把小壺就是不給我玩,我莫名其妙,三舅便告訴我,長大了他給我講講這把壺的來歷。
于是,我盼著長大,等著聽三舅給我講故事。不知不覺地我已上了小學五年級,當我再次去三舅家,三舅主動招呼我和表兄弟表姐妹,說要給我們講故事,大家一擁而上,團團圍坐在炕上。此時三舅摘下小壺,拿在手中翻來覆去地摸著,用低沉的聲音,給我們講起這把小壺的來歷。
“這事還得從1948年解放戰爭說起,在戰斗中時刻都有戰士流血犧牲,為了支援前線,開魯縣共組織了四期戰勤擔架隊。第一期是1948年元月,出擔架隊100副,戰勤民工400名,每副擔架編制3至4人。那時我才19歲,年輕力壯,也報名參加了擔架隊,分配到第一期,由縣政府戰勤科郭云峰同志任大隊長,鄭蔭亭任副大隊長。于元月3日全縣擔架隊集合在縣政府院內準備出發。出發前由縣長唐宏光同志作戰斗動員講話。講話的內容大致是:開魯縣擔架隊是支援東北解放戰爭的擔架隊,打倒蔣介石,保衛祖國,保衛家鄉,保衛勝利果實的光榮行動。擔架隊員個個磨拳擦掌,喊著口號:堅決完成任務。
唐縣長做完動員講話,由郭云峰率領隊伍,打著“開魯縣擔架大隊”的紅旗,由縣政府院內出發,一支浩浩蕩蕩的戰勤擔架隊走出東門,三舅也隨著隊伍,奔赴戰場。
擔架隊3日由開魯縣出發,夜宿道德營子和宋家店,4日進駐通遼,5日由通遼乘火車奔向鄭家屯,當日下午由鄭家屯,直奔即將解放的康平、法庫、彰武一“大崴子兵站”。這個地方風沙不斷,平原內澇,沙漠荒野,氣溫寒冷,交通不便。
當我們駐扎妥善,在晩飯后就接到緊急通知:有140名傷員,今夜必須轉移到鄭家屯,可只有100副擔架,怎么辦?郭云峰立即召開大會宣布,無論如何也要完成任務,擔架隊員舉手表決心,不怕流血,不怕犧牲。隊伍出發了,此時大雪連綿,寒風刺骨,轉移傷員非常困難。地下有匪徒騷擾,天上有飛機轟炸,解放軍奮力抵抗,擔架隊齊心協力,轉送傷員,時而有受傷的,時而有犧牲的,場面非常慘烈。突然,又是一陣轟炸,一顆手榴彈落在一名解放軍戰士近前,隨著一聲巨響,戰士倒下了,血肉模糊得沒了右腿,大家連忙把他抬上擔架,擔架隊員飛速前進轉移,血水順著擔架直流。這個解放軍才十八歲,叫王中,參軍一年,立過戰功,這次又主動請戰,參加戰斗。王中滿臉黑乎乎的,嘴唇干裂得扒著皮,三舅問王中喝水吧,他點點頭,可一問大家,幾個人誰都沒水,此時王中用左手指指7144251aa5f60f717dc91974eccc370586692df72d9c2de6bcd1c7ff9bd80735右臂,三舅一看,原來壓在右肩下面,是把小水壺,三舅趕忙摘下,搖晃幾下,還真有點水,趕忙給王中飲水,就這樣每過一會三舅就飲幾口,生怕小戰士犧牲,艱難的行走一段路,小戰士突然喊:“別走了,把我放下,去轉移別的傷員吧,我不行了”大家齊聲鼓勵王中:“小王,堅持住,小王,堅持住…”王中此時有氣無力真的不行了,他用盡全身的力氣指指三舅,三舅把耳朵貼在小王嘴邊,只聽小王說:“大哥,我不能和你們一塊戰斗了,這把軍壺留給你做個念想,等解放了你可以用它裝水去家鄉的田野耕田種地。”話音剛落頭一歪沒了氣息,大家脫帽致哀,都流出傷心的淚水。
在這冰天雪地里,我們幾個人選了一棵大樹下,用手費了很大勁扒個長方體小坑,掩埋了王中,用雪聚起一個高高的墳墓。從此,我背著這把軍壺,奔波在東北解放戰爭的戰場上,抬擔架,搶救傷員,給傷員飲水,形影不離”。
1948年5月,擔架隊全部完成了任務,三舅帶著這把軍壺回到了家鄉:開魯縣建華鄉福盛號村,才有了三舅講軍壺的故事,我才知道這把軍壺的來歷,怪不得三舅對這把軍用小壺這么珍惜。
三舅的名字叫王少武。為懷念戰友,三舅的第一個兒子起名叫王中。
根據《解放戰爭時期的開魯擔架隊》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