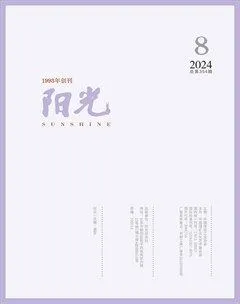父親這座礦山
我的父親一米七五的個頭,中等身材,眼神深邃。他寬闊、堅實的身板如同我們身后的一座大山,給予我們無盡的安慰與依靠。他做事情干脆利索,從不拖泥帶水。
一天晚上,父親神情凝重地對我說:“燕,爸想給你說個事?”
當時把我嚇壞了。在我的記憶里,他是一個不茍言笑的人,用商量的口氣和我說話幾乎沒有。跟兒女嬉戲的時候也少,除非喝了酒之后,在酒精的驅使下,他會說幾句玩笑話。我們家的好多親戚都怕他,我也不例外。
我吃驚地小聲問道:“爸,您說什么事啊?”
“爸爸想去新疆干煤礦,你幾個叔叔最近來咱家就是商量這個事情,說我有經驗、懂技術、會管理,想讓我入伙一塊干……”說著說著,父親的聲音就低沉了,陷入了沉思。
“爸,怎么了?發生了什么事情嗎?”
“你媽不想讓我去新疆,說離家太遠。我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就是不同意。你現在已經是大孩子了,幫忙勸勸你媽,爸爸去新疆是為了多掙些錢,供你們姐弟三人讀書,讓咱家能過上好日子。”他說完,我們相互凝視著沉默了一會,父親就忙他的去了。我懵懵懂懂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該怎么辦。
一晃兩天過去了,我一直沒有想好該怎么去勸說母親。這天剛吃完晚飯,天麻麻黑。父親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乘涼,一根煙接著一根煙地抽,他的臉上露出無奈的表情。蚊子時不時地在眼前“嗡嗡”地轉圈圈,小飛蛾也在空中翩翩起舞,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個不停。我從小就是別人口中乖巧懂事的孩子,性格綿綿的,話不多。而母親并不是書里描寫的“溫柔慈祥”的母親。她是個急性子,脾氣不太好。也許是父親一直在礦上上班,她長年在家里既要照顧我們姐弟三人,還要干農活,太辛苦了。所以,她對我們這些孩子們少了耐心和溫柔。
我鼓足了勇氣,小聲說:“媽,我爸說想去新疆干煤礦,您為什么不同意呢?”
“你爸讓你來給我說的……”母親表情里充滿了失望,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此刻,我想她內心是五味雜陳的,是糾結困惑的,她在默默地、無力地掙扎著。新疆那么遠,父親這一去,可能一年才能回一次家。以后家里的大事小情可都要靠她一個人來撐著了,而且她沒有信心能將膝下三個孩子都帶好!
看見母親這個狀態,我不敢吭聲,也不知道該如何勸慰母親。最終,母親還是拗不過父親,同意了父親去新疆。
父親早些年一直在當地的煤礦上班,從一個工人干到了礦長,不管是技術方面,還是管理方面都沒問題。另外,他的手上攢了一點積蓄可以支持他入伙干煤礦。
父親去新疆干煤礦的事情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他早先就聽一個叫董英兵的人說新疆的煤礦很好經營,不但煤炭品質好,而且采掘工藝簡單,在那里挖煤就是挖金子啊!因此,他們都動心了。
董英兵是父親以前礦上的職工,跟隨父親多年。他一個親戚在新疆的伊寧縣工作,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很了解。因為親戚的緣故,他來來回回去伊寧縣考察煤礦近半年多,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就回陜西聚集一幫子弟兄去新疆準備大干一場。他找到父親的時候,正是父親賦閑在家時。他原來干的那家煤礦資源已經枯竭,政府要求關閉枯竭礦井。父親在家等待著政府重新安置工作。董英兵跟他說了想法以及他前期考察的情況后,父親心動了。
2000年的春天,當群山脫下素裝,即將換上鮮艷的綠衣,風中還透著些許寒意,十幾位陜西的礦山漢子,離開老婆孩子,坐了兩天的綠皮火車,風塵仆仆地來到了美麗的新疆,看見了傳說中的天山。雪峰高聳入云,白雪皚皚,宛如一顆顆寶石鑲嵌在藍天之中,讓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與壯麗。
他們在天山腳下的一個小餐館里吃了點飯,小憩了一會兒,又上了大巴車,經過一天的舟車勞頓,終于來到了那個遠在千里之外讓他們魂牽夢縈的礦井。可當看到眼前這一幕時,他們傻眼了。只知道那是一個二手礦井,好幾年沒人經營了。他們沒有想到竟然如此破爛不堪,地面上最基本的生活設施都沒有,廢墟一片。
他們深入井下查看后發現井下的設備也是雜亂無章地擺放著,一個個沒有生命氣息的鐵疙瘩杵在那里像站崗一樣地等候著他們。巷道里到處是流沙,還有幾處冒頂,堵住了前進的路。他們幾經入井后總結出要想重新投入生產,必須進行全面整修,更換全套設備。怎么辦?既來之則安之,他們沒有氣餒,而是擼起袖子加油干。就這樣檢修了一年時間,各方面的投入越來越大,入股啟動資金已經所剩無幾了,職工工資也無法正常發放。不過讓他們欣慰和開心的事情是通過一年的整修,總算是見著煤了。他們興奮地邀請相關部門來驗收,驗收的結果是通風系統不過關,相關部門要求再建一個立井,在保證通風良好的前提下,才可以投入生產。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了董英兵。
董英兵學的是采煤專業,從煤校中專畢業之后,就在煤礦上搞技術。現在是他們團隊的總工。他喜歡鉆研,技術水平不錯,總是有獨到的見解和創新的想法,讓人感受到他的魅力和自信。中國太大了,南來北往地質構造差異很大,煤炭的種類也不一樣。新疆的煤炭品質好。據說,出遠門的時候往爐子里邊扔幾個小煤球(家中還有其他人),過幾天回家后,用風輕輕一吹,爐火還會呼呼地燃起來。說起此處,大家可能會想起西游記里的火焰山吧!小時候我以為那就是神話,世界上怎么會有這樣的地方呢?聽父親講述之后,我才知道原來真有這樣的地方啊!它就在新疆吐魯番盆地的北緣,被稱為“赤石山”,常年不滅,生生不息。
雖然新疆煤炭品質好,但是地質比較松軟,煤層上邊是流沙,就像水一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源源不斷地往下流。因此,頂板很難固定,壓得人喘不過氣。按照相關部門的要求再建一個立井,對父親他們來說是個技術難題。董英兵帶著大家試了很多種方法,后來是用磚將周圍全部壘起來,錨桿一個挨著一個固定,一直到井底308米的位置,打到了煤層上,才終于止住了流沙。“礦井就可以出煤了!”礦工們歡呼著、跳躍著,甚至在井下用唱歌、跳舞來慶祝這來之不易的階段性勝利。
礦井正常出煤后兩三個月的時間,突然來了一群人,個個面目猙獰,氣勢洶洶。不善的來者說著維吾爾族語,爸爸他們根本聽不懂。因此,他們召集全礦的干部職工尋找翻譯。有一個叫巴特的老工人,大高個子、身材魁梧健壯,濃黑的眉毛像兩條粗黑的蜈蚣一樣趴在臉上,說起話來,兩條“蜈蚣”上下跳躍著、表情非常豐富。他懂維吾爾族語,同時又懂漢語。經過巴特翻譯后父親他們才明白:帶頭的那個人是之前這個礦井的包工頭。他經營了幾年礦井,沒有看到效益,就舍棄了礦井。如今看見父親他們把礦井經營得盈利了,就帶了些人來鬧事要錢。他們隔三岔五就來,頻繁地鬧事致使礦井無法正常經營,沒辦法只好通過報警來調節著他們之間的關系。最終還是給了那個包工頭一些錢,才把這“無中生有”的事情化解了。
從那以后,巴特就成了他們的翻譯官。經常游走于包工頭和礦井兩邊,化解了一些小矛盾。巴特待人很熱情,他和父親關系相處得挺好,每到過維吾爾族節日的時候,他就邀請父親去他們家做客,“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父親他們初來礦井的時候,地面上沒有房子,他們都住在地窩子里。所謂的地窩子就是在地面以下挖約一米深的坑,形狀四方,面積約幾個平方,四周用土坯或磚瓦壘起約半米的矮墻,頂上放幾根椽子,再搭上樹枝編成的筏子,用草葉、泥土蓋頂,鑿一個土炕睡在上邊,人進去連腰都直不起來。陜西的礦山漢子們充分發揮了煤礦工人“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奉獻”的“三特”精神。經過一年的努力,他們就蓋了八十多間磚房,職工們就從地窩子搬進了新房,生活質量一下子改善了許多:他們終于可以去食堂買飯吃了,也可以自己在宿舍里做點家鄉口味的飯菜。慢慢地,吃住舒服了,心里自然也就感覺沒有那么苦了。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新疆當地的人,牛羊肉是他們每餐的必需食物。有些買不起大塊牛羊肉的人,會買點小顆粒肉干,吃飯的時候,撒一點到碗里,就算是把今天的肉吃了,明天才有力氣干活。而我們陜西人從小吃豬肉已經習慣了,但到了新疆以后很奇怪,也不想吃豬肉了,每天也是必吃牛羊肉才行。
新疆很多地方從十月份就開始下雪,幾乎每天晚上都會下,早上起來天又晴了,整個冬天基本都是這樣。雪下了不怎么融化,越積越厚。那里沒有春天的過渡,等到來年也不知道是哪天,氣溫驟然升高,直接進入了夏天。一夜之間雪全部融化了,藏在雪下邊偷偷生長的草兒露出了可愛的笑臉,綠油油的大地一望無垠,在微風的吹拂下搖曳著柔美的身姿。土地寬廣而肥沃,牛羊在上邊自由地奔跑,健康茁壯地成長,渾身充滿著生命的活力。新疆是個好地方,可是它再好,陜西的漢子們還是想回家。
這一年的礦井改造,將陜西的這群精兵強將干得筋疲力盡。用他們的話來說,一年到頭實在是太苦了!但一想到回家過年他們就來了精神,心情愉悅。
陜西到了天寒地凍的臘月,村子里家家戶戶都把爐子燒得暖烘烘的。學校放寒假了,我和弟弟們在家里待著,時而寫寒假作業,時而看看電視,時而幫母親干點小活。母親每天早上都很早起床,點燃爐子,等臥室有了溫度,我們才開始起床穿衣。這時,母親已經在爐子上把土豆、玉米糝飯煮進了鍋里,爐子旁邊的烤箱里放著手工饅頭,烤得亮黃亮黃的,外焦里軟,掰開后,一股濃濃的麥香味,抹一點油潑辣子,夾上自家腌制的咸菜,吃到嘴里嘎嘣脆,再炒個土豆絲,吃著紅薯玉米糝飯,簡直就是絕配!在我們這里的農村,這樣的早飯一吃就是整個冬天,天天如此,我們也不曾覺得膩。
一天,母親從外邊走進屋,高興地說:“你們爸爸已經買到回家過年的火車票了,大概在臘月二十五就能到家了。”我們仨在床上蹦著、跳著,歡呼著。一年沒見父親了,真是很想他了!早都盼望著這一天早點到來。
臨近年關,母親帶著我們在家里打掃衛生,置辦年貨,每天的事情安排得滿滿當當。小弟弟每天都要問一遍今天幾號了?母親都會不厭其煩地回答著。
日子說快也快,到了父親回家的日子了。吃完早飯,我們玩一會兒就去門口看一下有沒有父親的身影,一直等到了中午,也沒有等到父親。我們著急了,嚷嚷著去了離村子二里地外的馬路邊等父親。
我們從中午開始就一直在馬路邊等著。母親在家里干著活也不清靜,中間她也跑了幾趟,到馬路邊看看我們等到了父親沒。她每次來都焦急地望著馬路上絡繹不絕的車輛,心不在焉地勸我們回家等,說外邊太冷。可我們誰都不愿意回去。一直等到天快黑了,父親還沒有回來。我們一個個凍得嘴唇發紫,直打哆嗦,手腳沒有了知覺。母親看著心疼,在她再三地勸說下,正準備打道回府了。站在身后的小弟弟突然舉起小手喊道:“快看呀,爸爸回來啦!”
模模糊糊的遠方緩緩駛來一輛中巴車,在路邊停了下來,車上走下來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我們迫不及待地跑到車跟前,三個人同時撲進父親寬大的懷抱,激動地擁抱著父親。父親大笑著把我們每個人的頭都撫摸了一遍,然后對著母親苦澀地說:“車站回家過年的人太多了,排了幾個小時隊,好不容易才坐上車,今天差一點都回不來啦!”
售票員著急地喊:“孩子們,先別抱爸爸了,回家再慢慢抱唄。趕緊卸東西吧,車上這么多人都著急回家過年呢!”于是我們連忙從車上卸下來一大袋子葡萄干,十幾個哈密瓜、巴旦木及無花果等各種干果幾箱,一大塊新疆的羊肉,兩個大行李箱子等,不一會兒馬路邊就卸了一大堆東西。父親帶了這么多東西,還經過幾次轉車,他是怎么“過五關斬六將”次次把東西從車上搬上搬下的?我的眼睛濕潤了,無法想象那是怎樣的艱辛……
父親回來了!一年不見,再見時我覺得他陌生了很多,好像也蒼老了好幾歲。他面部消瘦,臉龐的輪廓線條清晰可見,眼眶凸起,黑眸深邃幽暗,不再那么明亮了。他的臉上顯著地留下了歲月的痕跡,他還常常若有所思地望著遠方發呆。我們不知道他這一年到底吃了多少苦,但從母親那里知道,這一年他沒有掙到錢。親戚鄰居聽說父親回來了,都先后來家里看望他,他便把從新疆帶回來的特產給大家一一分了些,讓他們都嘗嘗。
春節過得真快,父親回家沒有什么感覺一個月就過去了。他返回新疆的時間到了,我們和母親還是在之前的馬路邊送父親上了車,然后目送著汽車消失在遠方……
陜西的這幫礦山漢子們回老家美美地過了一個春節后,好像全然清空了上一年的辛苦。一路上個個洋洋得意,哼著小曲,相互分享著從家里帶來的美食,雄赳赳,氣昂昂,心中充滿了力量。礦井出煤了,他們看見了希望,相信只要好好干,多出煤就能多掙錢了。
進入礦區之后,他們沒有給自己留喘氣的時間,便馬不停蹄地安排著各項工作,研究著經營策略。待所有事情都安排妥當后,父親第一個帶班下井,快走到工作面的時候,卻發現前邊巷道冒頂了,幸好沒有人員傷亡。接著董英兵就帶著人又進入了整修階段,一個多月以后,總算是把冒頂的巷道打通了。但是這邊剛打通,那邊又開始冒頂了,事故頻頻發生。十米厚的煤層,能開采的最多兩三米,而且大部分都是沫煤。沫煤銷售不出去,最開始免費送給電廠,后來10元一噸賣給電廠,盡管這樣,銷售還是困難重重。
因此在新疆的那幾年,父親他們一直在與流沙、頂板、煤價做斗爭。一年一年下來,慢慢地將陜西這幫礦山漢子們磨得沒有了斗志。原來,外面的世界并不完全是他們想象的那樣精彩。掙錢是真不易啊!六年后,他們決定離開新疆,重返家鄉。
父親離開新疆的那一年,我大學快畢業了,弟弟們都在求學階段。如今我們姐弟仨都已成家。大弟弟事業干得不錯,已扎根西安。我和小弟弟接過父親這位礦山漢子手中的接力棒,光榮地成為了“煤二代”。雖然在我們人生的關鍵時期父親遠在新疆,但是他那種像礦山一樣堅韌不拔、勇于探索的斗志一直激勵著我們不斷前進。
宋 燕:陜西省銅川市人,畢業于延安大學中文系。中國煤礦作家協會理事,現供職于陜西陜煤銅川礦業有限公司,有作品曾發表于《陽光》等刊物及各網絡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