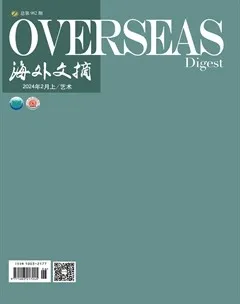窗的視野與心的映照:易安詞“窗”意象解讀


宋代李清照,自號易安居士,以詞聞名后世,其詞風清新婉約、憂憤深沉,得到了許多研究者的關注。自20世紀90年代始,通過對易安詞中審美意象進行微觀研究來探究詞人的人生境態與情感意識的研究逐漸受到關注。直到現在,其依然是熱門研究內容。在現存易安詞中,有11首包含“窗”的意象,詞人通過“窗”這一物質存在,宣泄不同人生階段的內心情感,將其作為心靈的“出口”,向讀者展現了她閨怨中的愛恨苦愁及對家國民族的深切慨嘆。基于此,本文對易安詞進行“窗”意象解讀。
1 易安詞研究
李清照(1084-1155)的詩詞為宋代婉約之風的代表,尤其重視對情景的白描,極擅通過某一具體物象來傳達細膩的情感,其詞具有非常豐富的蘊味。自20世紀90年代始,對易安詞的審美意象的微觀研究逐漸得到學界關注,學者們通過對具體意象審美價值的剖析來審視詞人的內心世界。
目前,多數學者認為李清照現存詩詞67首。在唐圭璋先生(1901-1990)編著的《全宋詞》中輯錄易安詞47首,學者徐培均《李清照集箋注》一書輯錄易安詞53首,兩相結合,依其題旨大致可分為四大類:閨情詞、風景詞、身世詞及晚境詞[1]。此前對于易安詞的審美意象的研究多集中于對“花”“酒”“飛鳥”以及其他類似“黃昏”“夕陽”“細雨”等意象的解讀[2]。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是學者楊艷梅,她將易安詞中的審美意象劃分為四類:雄渾壯闊的意象、悲觀蒼涼的意象、清新靚麗的意象和衰颯凄苦的意象[3]。經筆者梳理,現存易安詞中,有11首包含“窗”意象,本文通過對不同分期李清照望窗之景及臨窗之情的意蘊解讀,來還原詞人不同人生境態下的生命情感意識的變化。
2 易安詞“窗”意象演變
李清照現存詞量并不算多,其中提及“窗”意象的詞作有11首,大約占其總量的六分之一。 前人研究李清照的詞多尊“南渡前后二期說”,建炎南渡作為宋金政治對峙的歷史選擇結果,固然會對文化書寫環境產生一定影響,但對于久處深閨的李清照而言,封建社會對女性的束縛顯然對其影響更大。“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三綱五常成為影響李清照一生行為的核心觀念。因此,以宋室南渡為節點對易安詞進行前后分期未免太過籠統。細觀李清照的一生,相較于政治時局,與趙明誠共治金石之學好像更能給她安全感,以致趙明誠身故后,易安詞風及意蘊發生了顯著改變。而李清照在《清平樂·年年雪里》亦有對個人創作心態進行階段暗示,與學界現今“三期說”正相契合(即少女前期、婚后中期、孀居晚期)。基于此,本文采取“三期說”,論證三個不同時期易安詞“窗”意象的各自側重,由此窺探其心境及意識變化的特征。
如表1所示,宋王灼在《碧雞漫志》中評價李清照道:“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堅辛,姿態百出。”李清照所作的11首望“窗”的詞作似乎正合此言,沒有刻意地去描摹窗戶周遭的環境,卻給人一種臨窗幽婦的女性形象印象。
第一個時期,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到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李清照有3首詞提及“窗”,《浣溪沙》中“小院閑窗春色深,重簾未卷影沉沉”。小院春色正濃,主人閨房那陰沉沉的有護欄的窗戶卻緊閉著,窗簾也沒有打開,看似白描實際卻飽含少女懷春的愁緒,而那一道緊鎖的窗戶好似封建女性窮其一生不能跨越的屏障,窗戶此刻就是詞人那內心森嚴的壁壘高墻的外化。同樣,《玉樓春》的“道人憔悴春窗底”和《滿庭霜》的“小閣藏春,閑窗鎖晝”,也都是傷春之作。從李清照早期的望“窗”詞作來看,“所望之窗”所表達的其實正是少女對外面世界的向往和對時間飛逝的感傷。
第二個時期,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至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也是宋室南渡的轉折,有5首寫“窗”的詞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聲聲慢》與《鷓鴣天》。《聲聲慢》里是“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這樣一個“守窗人”有著和《念奴嬌》里“玉闌干慵倚”及《點絳唇》中“望斷歸來路”同樣的“等人之語”,所盼之人就是“走遠的武陵人”,即丈夫趙明誠,由“晚來風急”到“到黃昏”,李清照一直都是那個“守窗的幽婦”,一首首詞述說了在窗戶旁邊急盼歸人的時間之長以及她孤寂的心境。而《鷓鴣天》里的“寒日蕭蕭上瑣窗,梧桐應恨夜來霜”,瑣窗指的是刻有連環圖案的窗,深秋的陽光照在窗戶上,卻沒有給人以溫暖的感覺,“應恨”恨的是寒夜的濃霜嗎?在低沉的基調下,詞人恨的是身世之悲。正如朱彧《萍洲可談》卷中所評“天獨厚其才而嗇其遇”,“窗”在此處仿若詞人那緊閉的心門,任李清照有一顆七竅玲瓏心,面對丈夫的生病,她也不免黯然銷魂。
第三個時期,宋高宗建炎四年(1103)至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1155),此時段趙明誠身故、李清照孀居。這個時期的《攤破浣溪沙》和《轉調滿庭芳》都是以與窗紗的距離來表達內心面對現實苦痛的迷惘,突出破碎感。心境上的孤寂比前兩個時期多了幾分淡然,這時期的“窗”更像是連接內心與外部環境的鑰匙,有心打開卻再無力應對,這種痛苦上的逐漸朦朧化也是李清照晚年的真實寫照,似乎顯出了她的麻木。《添字丑奴兒》中“窗前誰種芭蕉樹,陰滿中庭”寫南渡嫠婦在臨時住所中看到了窗前的芭蕉。在炎熱的天氣內,芭蕉讓人有幾分舒爽,這種芭蕉的清涼卻在晚上對詞人造成了困擾。“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霖霪。”這和杜牧的詩《雨》以及溫庭筠的詞《更漏子》有異曲同工之處。這一切的所見之景是詞人以“窗戶”為參照,分別從“窗外”到“窗內”的視感結果,“窗”成為了詞人的眼睛,所有的感觸在“窗”的狹小范圍內得到了變化。
3 李清照“窗”意象美學內涵
易安詞當中對于“窗”意象的使用有較為明顯的特點,李清照用她極其擅長的白描給我們描繪了一個臨窗婦人孤怨哀婉的一生。從前述三個時期的對比中可以看出,與趙明誠婚后,她描繪臨窗場景的詞作明顯多于另外兩個時期,且在11首臨窗詞作中幾無例外,全都是詞人透過描寫窗戶外的一番天地來達到抒發一種憂戚情緒的目的。窗戶不僅可以是點綴哀婉的詞中之景,也可以成為溝通內與外的媒介。
在易安詞中,內心對外部景物的接受如同對一幅畫的觀察,“窗”就是定格的畫框,且李清照詞作望“窗”所處空間各不相同,如表2所示。《聲聲慢》中窗戶內是守著窗兒的一個看黃昏的婦人的孤獨背影,窗戶外是細雨中的梧桐嘀嗒作響,窗內之景與窗外之景分明是兩個世界但卻完美相融。《轉調滿庭芳》中池塘里生長的春草和庭院里的綠蔭,都是詞人透過紗窗所感受到的景致,可以說窗戶成為詞人溝通外部世界的媒介。當然還有更為特殊的例子,即李清照的兩首《臨江仙》。詞人對窗戶內外都有所關注,但是相較于窗外之景,窗戶內的描述更多是通過詞人的感受向我們呈現出來的。一邊說著庭院春色已深,一邊感慨深閨愁情,完全是依靠窗戶內的愁人情緒的起伏來展示周圍環境。由此我們還可以從“窗”的物理空間的不同角度切入來分析詞人心理狀態,11首詞中只有2首是詞人以窗外的視角來觀察個人生活的,窗內向外的透視更像是詞人內心的自省,那么窗內望向窗外之景就是心靈意識的表達。其中《臨江仙·并序》中窗戶外是一片云霧繚繞,但是窗戶卻是“常扃”的,詞人緊緊關閉高樓之窗,擁有俯瞰外物的條件卻選擇自閉于房門,何嘗不是詞人難言悲苦、無人訴說的心情的寫照呢。
詞人通過“窗”實現了所觀之景與審美心靈的勾連,詞人與窗戶的物理距離使文字具有了畫面的空間感,以窗戶內外的變化引導讀者的視線。一是由內及外。《菩薩蠻》中“背窗雪落爐煙直”讓人看到了窗外的飛雪以及窗內的溫暖爐煙,兩相映襯給人以動態的審美感受。在空間的切換中,窗戶成為兩個空間的阻隔,詞人憑窗而望,詞作站在觀察者的視角,以景物的轉移來實現詞人情緒的轉移,即情緒上的沉郁向淡然的過程。二是由外及內。《添字丑奴兒》中“窗前誰種芭蕉樹,陰滿中庭”,陰雨連綿的天氣,詞人立于中庭之下,看到了窗下的雨打芭蕉,看似在自言自語地詢問,其實不是舒卷的芭蕉葉有情感,而是孤寂的詞人多了幾分愁情,在雨夜中發出了身世之嘆。窗戶拉近了空間的距離,形成了“窗”“雨”“芭蕉”共處的視聽環境。三是內外交互但又止步于窗。《聲聲慢》中的“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在此處,窗戶意象就顯得靜態很多,只是作為一個相對封閉但又開放的空間,讓人有一種隔離感。于李清照而言,少女時期的窗外是令人期待的,晚年喪夫的世界是灰暗的、不值得留戀的,絢麗屬于窗外的白天,與她無關,狹隘逼仄是她窗內的世界,才是她的歸宿,以至于她雖終日守著窗兒感慨天黑的難熬,聽到了窗外的點點細雨但卻不踏出房門,獨留自己在冷清孤寂的房間里尋尋覓覓。綜上,窗戶作為易安詞中的獨特意象,讓她通過“窗”見證了外部世界的風云波動,也通過窗外向窗內的過渡,讓她對自己的內心的意識進行了自省,為我們展現了她的不安、孤苦與憂愁,李清照對“窗”獨特審美空間的把握,使易安詞有別于其他詞人的獨一份美感。
4 結語
在李清照11首包含“窗”意象的詞作中,婚后是其望窗、臨窗的創作爆發期。本文以其創作的三個分期來把握易安詞中“窗”意象的背景及演變,可以發現李清照“臨窗”的心理意識變化是由“春愁”向“相思愁”再到“身世愁”轉變的過程。對于易安詞“窗”意象的審美內涵而言,李清照通過對“窗”的觀察達到了對外部世界的審視和自我內心的反思,狹窄的窗戶視野就是她與外部空間的交流,窗戶周遭的環境變化就是她自身心境的寫照。詞人視野通過對窗戶的由內及外和由外及內的視聽傳遞,實現了現實世界與心靈世界的勾連以及個人情緒的轉移,完美呈現了李清照不同人生階段個人境態與內心情感意識的外化。“窗”這一物質存在成為她在不同時期宣泄內心情感的“出口”,如同心門的具象化,向我們展現了她閨怨中的愛恨苦愁及對家國民族的深切慨嘆。■
引用
[1] 徐培均.李清照集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王姝.李清照詩詞中的“窗”意象研究[J].今古文創,2023 (11):53-55.
[3] 楊艷梅.論易安詞的審美意象[J].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99(6):27-30.
作者簡介:劉彧江(2000—),男,河南鶴壁人,碩士研究生,就讀于香港教育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