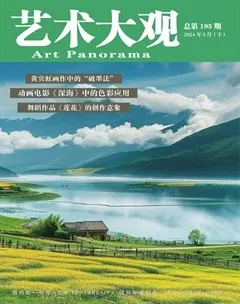貴州織金苗族蠟染紋樣與中國畫的關系

摘 要:基于織金苗族蠟染與中國畫都萌發于中華文化深厚底蘊下,本文通過探討織金苗族蠟染與中國畫的點線面、構圖及設色上的異同來揭示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文化價值。首先,從媒介和載體入手找到兩者的共同點,再進一步通過畫面構成形式和點線面的應用找到兩者的不同點;其次,探討兩者在色彩使用歷史上的不同。最后,總結出兩者是辯證統一,和而不同的關系。
關鍵詞:共性;紋樣構圖;點線面;色彩;對比
中圖分類號:J5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905(2024)15-0-03
一、織金苗族蠟染和中國畫的共同點
蠟染與中國畫,一個是民間手工藝術,一個是繪畫藝術,都在隨著中國發展的幾千年中不斷地探索新思路,這也說明兩者在審美風格和形式上都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風俗內涵,且影響深遠。
第一,從兩者媒介的互通性上來說,銅刀作為蠟染工具與國畫中運用的毛筆只是運用方法有所不同,但兩者的本質都是來自畫者展現對物象本體的描繪,主要體現在對點、線和面的應用方面。
第二,從載體的角度來說,織金苗族蠟染藝術和中國傳統繪畫藝術作品傳達載體也具有共同性。盡管在表現物象功能上有所不同,但蠟染或是中國畫,它們開始的載體大多是織物,盡管后來中國畫大部分用紙張取代,但仍有小部分以“絹”繪畫。
所以,兩者在媒介和載體方面具有共通性,其共通性也離不開中華文化發展的歷史沉淀,這也是兩者最大的共同點。
二、織金苗族蠟染與中國畫的不同點
(一)織金苗族蠟染和中國畫構成的不同
紋樣的構成形式,是有序劃分的理性秩序空間。組織形式和構成形式始終是密不可分的,可以理解為是利用組織手法來表現構成形式。織金苗族蠟染的組織形式表現為發散式和重復式,幾乎沒有近似漸變等其他形式。重復組織形式要求畫面空間平均劃分,各個塊面面積相等,是最基礎的組織形式。蠟染紋樣必須均勻重復地分布,劃分形狀可以是正方形、三角形和長方形,總體是統一規矩有秩序的表現形式。
另一種是正負形相依,通常黑為正,白為負,具體有單獨紋樣、連續紋樣、適合紋樣和組合紋樣四種構成形式[1]。
構圖在織金苗族蠟染和中國畫中都占據著重要地位。首先,中國畫中的構圖在南齊時期被謝赫稱為“經營位置。”在國畫中,位置經營強調“意在筆先,畫盡意在。”“立意”受到中國歷史中哲學思想發展的影響,決定了人們對時間和空間的認識,在《道德經·道生一篇》中,老子說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指出了天道和人道的統一,即世界萬物與人的根本都是一樣的,所以產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國文人看來,做到本我與自然合為一體,用本心去體會大自然的“意”,才能達到心物統一,體會到世界對于山川河流所處位置的微妙。這也解釋了為何部分古人在中國畫的構圖上運用了“散點透視”。這種視角的繪畫不是固定焦點,不僅強調景物之間的實際空間關系,也體現了畫家思想與自然的合二為一。
其次,在中國畫中,主賓關系是構圖中的一個重要原則。一幅完整的作品需要有主和賓。主體就是畫面中最重要的形象,而為了突出主體,還需要有陪襯,這個陪襯便是“賓”。這種關系在中國哲學中被類比為“君臣”關系。郭熙的《早春圖》就清楚地展示了這一特點。作品從上至下,山水、樓閣、樹木和人物等物象依次分布,中間的山作為主體,是“君”的位置,左右兩邊的小山如同輔佐它的臣一樣存在,具有明顯的等級層次,所有的物象都按照一定的秩序排列。
最后,中國畫位置經營中常常會運用“留白”“虛實相生”的手法。留白這一語言藝術在國畫中有著重要內涵,通過巧妙運用和經營,將畫中空白部分與其他部分聯系在一起,相互交融,創造出一種無聲勝有聲的意境。同時,還需要考慮整個空白區域的外形,分析畫面中的“正形”和“負形”的關系,真正做到知白守黑。通過留白手法,將豐富的內涵和意境通過虛實展現給觀者,黑從白現,白從黑生。白不等于無,而是除黑以外的無形之形。虛實兼備、黑白相生,留白能夠展現出豐富的層次[2]。
(二)織金苗族蠟染紋樣中的點線面與中國畫中的點線面的不同
1.織金苗族蠟染紋樣中的點線面
織金苗族蠟染以點線面為基礎元素,形成了獨特的紋樣,呈現疏密相間、依形共生、對稱均衡的構成特點。織金苗族蠟染整體具有造型美、色彩美、意蘊美的三大藝術特征。
點。織金苗族蠟染中,點可分兩種形式。第一種是“點”本身去表現不同的圖案元素,并不是我們平時理解的單純的點。蠟染中的點可以表現為三角形、正方形和圓形等元素。三角形和方形的點適用于幾何紋,圓點適用于植物和動物紋樣,但基本不單獨使用,而是與其他圖形共同構成完整紋樣。第二種是相同的點的組合,是由單一點元素的基礎構成,以組合的方法來整合形成新的點,再將新的點構成完整紋樣。這些點的元素通常根據主題紋樣進行隨機的變化和排列,這種靈動處理方式下的點可以打破印象蠟染中的刻板形象,使畫面更跳脫。
線。線是蠟染紋樣的重要造型元素。蠟染線條的粗細、長短、虛實變化都能營造一種視覺的空間感。在織金苗族蠟染中,線條表現形式可分為三種:直線、曲線和幾何線。
直線平穩靜態,簡潔明了。如果帶有方向變化,就具有速度感和方向感,垂直的直線則顯得嚴謹莊重和冷靜。長直線常被用作蠟染的邊框,使蠟染的邊界明確,既規范了畫面邊緣,又明確地劃分了畫面空間,給人嚴肅規整的感覺。在織金苗族蠟染中,長直線也象征著回家的路面,有幾條線就代表著幾條路。折線相對于直線波折感更強,更容易造成心理上的焦慮感。
曲線大多是小號蠟刀繪制的,線型較小。蠟染紋樣中無論閉合幾何曲線還是開放幾何曲線都給人優雅流暢的感受,與直線形成對比。在織金苗族蠟染線條中四分之三都是曲線。然而曲線的繪制非常復雜,要根據畫面需要來控制線的走向和長短,一氣呵成,做到繁而不亂。
面。面是最具有視覺沖擊力的元素,當面的形態最為凸顯時,其他元素就會自動弱化,點線就成為面的背景一樣的存在。但在蠟染作品中,織金苗族的蠟染并沒有采用大面積染色的方式,線條居多。以線的組合圍合封閉形成的面,形態規整,多呈現對稱樣式。直角面由秩序性直線構成,包括方形、菱形和三角形都由固定的角度構成。曲線面的特點就是柔和圓潤,蠟染中基本體現為圓形和水滴形的面[3]。
2.中國畫中的點線面
點。中國畫中的點線面是屬于三位一體的,不僅是為了造型而造型,還是藝術形象的組成結構,通過意蘊感情和筆墨形成繪畫的藝術趣味,所以不能將它們拆開來看。中國畫從宋朝就有“點”這個概念,郭熙把它定義為“以筆端而注之稱為點”。點是中國繪畫中不可缺少的因素,點相連接為線,大的點就是一個面,這與織金苗族蠟染中對于點線面的運用是一致的,但在點的運用上中國畫中更講究點的干濕濃淡,意趣不一。中國畫中的點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其不只是對實物的直接描繪,還包括各類物象的類比。他既能當作一片葉子,也可當作一朵花。清鄭績在《夢幻居畫學簡明》中道:“點苔之法,其意或作石上蘚苔,或作坡間蔓草,或作樹間薜蘿,或作山頂小樹,概其名曰點苔,不必泥為何物。故其圓點、橫點、尖點、禿點、焦點、濕點、濃點、淡點、攢聚點、跳踢點皆從山石中皴法生來,又從樹葉中點法化出”。由此能理解他的審美意義,手法的多樣化。
線。中國畫中的線與織金苗族蠟染的線不同的是,織金苗族蠟染富有更多的形式感,而中國畫的線則更注重運用時的筆法。一是線條作為中國畫造型的媒介,就如建筑內部的骨架,所有線條包括框架在內也講究優劣之分。而真正給出線條好壞的評定標準要追溯到東晉謝赫六法中的“骨法用筆”一說,后來張彥遠更進一步提出骨法用筆的精髓所在,如運筆勾線是必須意在筆先,筆盡意在。二是中國繪畫中的線條必須講究勾勒的用筆之法。勾勒不僅要有順逆之分,要求用筆有方圓和頓挫之感,還要有線條的繪畫意識,這樣才能使線條飽滿結實,有立體感。三是講線條“留重”是一種在繪畫時線條受到阻力下形成的澀感,在中國的傳統畫論中稱為“屋漏痕”。在繪畫時能夠感受到用筆的力度和肯定。
面。積線成面,面是擴大的點,中國畫“計白當黑”的觀念不僅與構圖有關,還在體面的處理占有著重要的地位。“白”是針對畫面布局中過度黑的壓迫感而言的,整個景的布置所留的空白要得體,否則就會顯得過于滿密。所謂白中藏黑,是計劃之白,是一種高度的概括,使景物的意境更深幽。但是對于留白的靈性,也離不開黑的運用。老子也強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道家的陰陽八卦圖就是這一觀念的物化。總之,中國傳統繪畫非常注意點線面三者的結合,但也要分清主次運用。中國畫中的點線塊面的組合是不可以追求面面俱到的,而是要懂得點到為止。
(三)織金苗族蠟染用色與水墨畫的用色的不同
織金苗族蠟染由靛藍與白色構成。織金苗族蠟染的色彩選擇與當地的環境、生產條件有著必然聯系。織金依山傍水群山環繞,盛產藍靛草。古代當地多戰亂,原始氏族渴望和平和安穩的社會環境。色彩心理學中,藍色被認為是具有視覺愉悅和心理撫慰作用的顏色,靛藍色也體現了傳統色彩的最初來源和目的。從另一層面來說,人們對靛藍色的選擇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染色植物是祖先勞動中的偶然發現與運用。古人在勞動中偶然被一些植物的汁液染到,于是想到將顏色用于衣裙上。另外,靛藍成為主要色也是古人的必然選擇,源于他們發現藍草具有藥用價值,適用于外出勞動中防止蚊蟲叮咬。
但對于蠟染中這一藍色的運用,它沒有深淺的變化,沒有過渡的中間色的顯現,只有單一穩定的靛藍。
在中國傳統水墨畫中,“墨色”從奴隸社會開始就得以見雛形。在奴隸社會時期,人類的文明化程度發展處于初級階段,所以對于顏色的認識比較單一,關于墨色的理解也只停留在黑白兩個顏色。在那個階段,人們通常認為黑白兩色中涵蓋了自然界的所有,原因是因為人們對當時顏色的感受還較為粗線條。隨著文明的進步,在水墨畫中墨色更為細化,不再滿足于黑白兩色,灰色也開始用于中國水墨畫中。黑白灰對于畫面運用不僅是機械的使用,還開始帶動人的情緒。黑色帶有神秘肅靜之感,產生恢宏壯闊的視覺沖擊力;白色給人純潔、敞亮之感,小面積留白被當作畫面的氣口,也讓畫面延伸感和擴張力有所凸顯;灰色介于黑白之間,給人平和、寧靜之感,明度跨度一般不會很夸張且沒有分界線。盡管灰色缺少黑白的跳躍和直接,卻是畫面層次豐富的關鍵。灰色程度根據畫面需求變化,通過調節墨的水量多少,控制濃淡深淺變化過渡,灰色在黑白之間起到調節、銜接、統一和豐富畫面的作用。
上述水墨畫中的黑白灰的運用造就了中國水墨畫中深厚的精神內涵和中國化特征。然而,僅僅通過這種方式去還原物的造型并不是中國藝術的最終歸途。中國水墨畫中體現的墨色繪畫理念也是如此,墨色觀是不同于其他繪畫形式下的審美意識,它是以水墨變化的寫意性進行參禪造化。
這兩者的色彩來源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文化底蘊上也難分伯仲,但在色彩的審美意識上,蠟染始終如一地追求他們所期望的穩定質樸,一切都是平鋪直敘、娓娓道來之感,有著一份獨屬于它的執著。國畫則以玄而未玄傳達其用色意境,追求意境的同時,又希望將意境有所寄托,通過細分顏色來盡其本意。無論是靛藍,還是玄色,都是以自己最單純的本質承載著歷史氣息的中華文化的審美意識。這就是它們共同的獨到的魅力。
三、結束語
織金苗族蠟染歷史悠久,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是織金苗族人民精神情感的表達,也是織金苗族所特有的藝術形式,為人們帶來美的享受。本文從苗族蠟染紋樣的角度入手,通過對織金苗族蠟染紋樣的構成結構和內在點線面的分析,同時將織金苗族蠟染紋樣中的紋樣與中國傳統畫中的多個元素進行對比,討論它們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蘊。這樣既可以在蠟染中尋找中國畫中的水墨韻律之感,又能在中國畫的創作中融入織金苗族蠟染紋樣中那種直接明快的沖擊力。這兩者并非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相互映襯的關系。它們有著許多共通之處,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發現。
參考文獻:
[1]王曉雪.貴州織金苗族蠟染紋樣研究[D].中南林業科技大學,2020.
[2]陶亞杰.民間蠟染藝術在中國畫技法上的延伸[J].上海工藝美術,2003(04):57-58.
[3]楊柳.有法還是無法:謝赫“六法”內涵與體系辨析[J].民族藝術研究,2023,36(03):5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