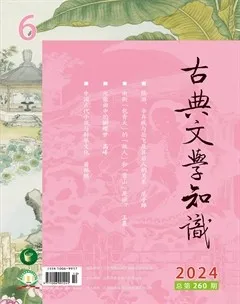改朝換代之歷史宿命

“窯洞對”
1945年7月1日到5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黃炎培與王云五、傅斯年、章伯鈞等一行七人,訪問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黃炎培在《延安五日記》提到,他與毛澤東主席在延安窯洞里對中國歷史興亡周期率有所探討,毛主席認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主席還常以“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中國歷史,教育全黨引為鑒戒。如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所撰《甲申三百年祭》(甲申年,1644年)在重慶《新華日報》連載。這篇近兩萬字的文章,主要講述了明朝滅亡、李自成興起與失敗的經過以及原因,并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贊譽。
天意或宿命
然則黃炎培與毛主席所稱的“周期率”,郭沫若所祭的大明朱由檢之亡、大順李自成之敗,落實到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典型的例證就是似乎已成“宿命”的改朝換代吧!如僅就表層顯見的現象而言,先是創業大帝、守成之主,然后是養于后宮的庸主、間或出現的中興之主,再是(抑或勝利者“建構”或“書寫”的)孱弱、昏聵以至殘暴、荒淫的末主;先是國勢強盛或與民休息,然后是政治腐敗、天災人禍、民不聊生,接著民變、兵變。而上有孱弱、昏聵、殘暴、荒淫之君,下有沸水甚至烈火般的變亂、起義,于是或內部禪讓或外力征服,從而完成改朝換代。這樣的改朝換代,無論周期長短,大體如出一轍,無論統一分裂,總在反復上演。而在此循環不已的過程中,筆者還注意到一些“神秘”或“無解”的現象。如:起自秦朝的11個統一王朝中,三個短命王朝即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新朝(9年—23年)、武曌的周朝(690年—705年),都是15年。又三個長壽王朝,唐朝從618年到907年,減去中間武曌改唐為周的15年,還有276年;大明從1368年到1644年,也是276年;大清國號起自1636年,止于1912年,仍是276年。為什么會如此呢?筆者不知道。而面對諸如此類的許多不知道,習慣尋求答案的人們往往也就一推了之:那是天意或宿命—注定的命運所決定的。
以天意或宿命解釋王朝的興替,姑以王莽代漢為例。眾所周知,王莽的新朝把漢朝腰斬成了兩半,就是前漢與后漢,或說是西漢與東漢。劉邦創建的西漢210年(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劉秀創建的東漢196年(25年—220年),中間則是歷時15年的新朝。那么為何會在長長的兩漢中間夾著個短短的新朝呢?有種長期流傳民間的說法是:這得追溯到秦朝末年。大概公元前211年時,黑夜沉沉的豐西大澤中,小吏劉邦(當時還稱“劉季”)與跟隨他逃亡的本來要去驪山修秦始皇帝陵的十幾個刑徒,正行進在蜿蜒曲折的小徑上,突見一條碩長的蟒蛇盤踞徑中。劉邦拔劍就要斬蛇,蛇昂起頭說:你斬頭,我鬧你頭,你斬尾,我鬧你尾。沒想到劉邦毅然將蛇攔腰斬斷。后來的王莽就是這條蟒蛇的轉生,“莽”者“蟒”也。因為這條蟒蛇被劉邦腰斬了,漢朝等于虧欠了蟒蛇的“蛇情”,于是漢朝送了蟒蛇投胎化作的王莽15年,算是償還了前世的因果恩怨,而且這種償還,還是超越“人情”的“蛇情”,漢朝的形象也隨之更加高大。又因王莽的倒行逆施,劉秀在云臺觀白蟒臺再斬王莽,這就是京劇傳統劇目《云臺觀》中所唱的:“白蟒臺是孤傳詔建,今日送孤命歸天”(王莽),“生擒王莽云臺觀,仇報仇來冤抱冤”(劉秀)。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見于不少演義小說、傳統戲劇里的說法,并不完全是虛構,而是有著真實的影子。如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描寫當朝高皇帝劉邦之“斬蛇”情形道: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愿從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愿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后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 人乃以嫗為不誠,欲告之,嫗因忽不見。后人至,高祖覺。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東漢班固《漢書·高帝紀》的記載略同。這是說劉邦為赤帝之子,白蛇為白帝之子,劉邦斬蛇,寓意劉漢將滅嬴秦。但是到了后來,也許面對著210年的漢(西漢)、15年的新朝、又196年的漢(東漢)這個奇怪的改朝換代局面以及甚是詭異的年數,人們為了給自家的、正統的、喜歡的漢朝掙些臉面,為了替并未出過特別混蛋皇帝的漢朝找些借口,就做起了王莽之“莽”的文章,這樣,王莽代漢遂被納入宿命輪回、因果循環的鏈條之中。又與王莽代漢相差仿佛,公元220年曹丕篡東漢、封漢帝劉協為山陽公,公元266年司馬炎篡曹魏、封魏帝曹奐為陳留王,《三國演義》遂引后人的詩句道:“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晉國規模如魏王,陳留蹤跡似山陽”。
民族形勢與政治制度
當然,宿命輪回、天運循環不能詮釋歷史,恰恰相反,唯有歷史才能詮釋宿命、天運。從表象看,雖然一部中國王朝史,改朝換代的確堪稱頻繁,其相關的史實,就社會認知而言,也因其復雜而頗顯混亂。但也要我們跳脫瑣碎的細節,進行宏觀的觀照,則歸納起來,改朝換代也就外力征服、內部禪讓兩種形式而已,且可劃分為前、中、后三個階段:從公元9年王莽代漢建新到公元960年趙匡胤篡周立宋,這近千年的中段,王朝遞嬗多是通過內部禪讓的形式完成的,而其前約兩千年的前段即夏、商、周、秦、漢,其后近千年的后段即宋、大元、大明、大清,朝代的更迭大體為外力征服所致。
那么,我們又如何理解中國歷史上這一明顯的政治現象呢?其中的關鍵,應該在于民族形勢與政治制度。以言外力征服為主的前段與后段,王朝外的力量之所以能夠取代該王朝,是因為這種力量已經足夠強大,而這大多聯系著新興的民族勢力。如夏、商、周三代,夏起于西部,然后為起于東部的商人取代,周人又起于西部,取代了東部的商,這是黃河流域東、西民族之間的相互征伐;金先滅了北宋,大元再滅了南宋,大明接著滅了大元,大清最后又滅了大明,這是邊地民族與中原漢族之間的相互征伐;至于雖不算是改朝換代、但反映了王朝的國勢由強盛轉向衰弱的先“西”后“東”、先“北”后“南”的習稱,如“西周”再“東周”、“西漢”再“東漢”、“西晉”再“東晉”、“北宋”再“南宋”,也是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強力壓迫乃至其他民族入主中原所致。至于以內部禪讓為主的中段,如西漢禪讓給新,東漢禪讓給魏,魏禪讓給西晉,東晉、宋、齊、梁、陳的接連禪讓,西魏禪北周、東魏禪北齊,北周禪隋、隋禪唐、唐禪五代之后梁,十國之楊吳禪南唐,以至五代之后周禪宋,簡而言之,都是王朝內部的力量取代了該王朝,也就是君臣發生了換位,本來的君成了臣,本來的臣成了君。可以想象,君臣換位是以君弱臣強為前提條件的,而這種條件的出現,又往往與政治制度的設計有關,也就是制度的缺陷造成了權臣的產生。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賴肖爾(Edwin O.Reischauer)在《中國:傳統與變革》(陳仲丹等譯)一書中,曾分析過這個問題,他們指出:
因為宋代完善了文官制度,中國政府相當穩定。趙匡胤960年的篡位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后一次,在以前,皇帝不斷被他的大將、皇后和其他有權的大臣奪去皇位,960年以后,這種情況不再出現。王朝繼續被外來征服或民眾革命所滅亡,皇室的一些成員將皇位搶來搶去,但不再有臣下成功地篡奪皇權的事例。
這段話可謂形象地說明了外力征服、內部禪讓兩種改朝換代的形式及其原因所在。
令人深思的是,如上費正清、賴肖爾的說法,“宋代完善了文官制度,中國政府相當穩定”,而當時宰相趙普的話,則可視為費、賴之論的注腳:“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唯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司馬光《涑水紀聞》)于是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趙匡胤為了別人不再重演他演過的歷史,正是從權、財、軍三方面加強中央集權制度的,并且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然而另外的麻煩又出現了:冗官、冗兵、冗費,使得趙宋朝廷陷入了“積貧積弱”的難堪境地,威脅皇權的文臣、武將是沒有了,抗擊邊患、鎮壓民變的強臣、悍將也沒有了,皇位不再被“家人”侵奪了,卻受到了“外人”的覬覦。事實正是如此,北宋徽、欽二宗為女真金朝所擄,南宋恭宗舉國降元、帝昺投海而死。也許,這就是歷史的悖論吧:在內廷與外朝、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君弱臣強、干弱枝強,難免出現權臣、內部禪讓、君臣換位;君強臣弱、干強枝弱,也會有外來征服、民眾造反,從而王朝易主。而在這樣無法求得平衡或重近利、輕遠弊的制度運行中,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的治亂興衰、改朝換代,真的成了無法改變的歷史宿命;而一部中國王朝史,也便由外力征服—內部禪讓—外力征服三大板塊結構而成。
◆ 胡阿祥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六朝博物館館長、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