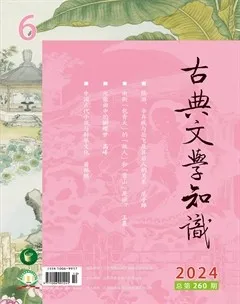南衙“包青天”的“敵人”和“靠山”是誰?
《三俠五義》小說里的包青天形象在民間流傳甚廣,以至于后世認為包拯仕宦的主要身份即“開封府尹”,實際上他擔任京師長官的時間只有一年半左右。但在這任期不長的“首都市長”職務上,包拯確實因為一些剛正不阿的表現而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當時百姓口耳相傳著“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民諺。
所謂“龐太師”與包拯為敵當然是小說家的戲言,翻開《宋史·包拯本傳》,可以看到其在“權知開封府”任上,曾有這樣一段重要經歷:
中官勢族筑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惠民河(蔡河)在汴河之南,是東京漕運的主要河流之一。“中官勢族”園宅侵占河道導致了惠民河的堵塞,這一方面會影響漕運,另一方面如果碰到洪澇災害,那么兩岸百姓自然是苦不堪言。
中官謂內侍宦官一流,勢族指官宦豪右一類。從本傳的簡要記述來看,當包拯要拆毀兩岸“違章建筑”之際,頗有人拿出所謂的地契,試圖阻撓。但僅就本傳而言,我們還不能知曉這個膽敢阻撓包拯的人屬于中官還是勢族。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六《包孝肅公拯》中就有了明確的說法:
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歲久湮塞,遂盡毀去。宦者偽增地契步數,悉奏劾之,權貴為之斂跡。
可見拿出“偽增步數、冒添土地”的地契者,指的是中官內侍。
按包拯門人張田所編《孝肅包公奏議集》,至南宋時附入的《國史本傳》(明朝以來刊本均作“國史本傳”,然或是《仁宗實錄》中的臣僚附傳,而非《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中的臣僚本傳,為方便故,下文稱為《包公奏議集》附傳):
京師大水,乃言勢家多置園第于惠民河上,歲久湮塞,遂盡毀去。中貴人有侵跨河壖為亭榭者,自言地契若此,驗之,乃偽增步數,劾奏之。
“中貴人”一詞可見這并非尋常的內侍宦官,而很可能是一位貂珰,否則也很難有經濟能力在東京城置辦臨河的豪宅,畢竟開封的房價在當時是極貴的。《包公奏議集》附傳應當也是如今傳世的幾個包拯傳記所依據的原始史料之一,或者說至少在時間上比《名臣碑傳琬琰集》收錄的曾鞏所撰包公傳、元朝所修《宋史》包公本傳要早。
當時侵占惠民河兩岸的中官勢族當然不是一二家,但在此番拆除違建的過程里,首當其沖與包拯產生沖突的這位“中貴人”究竟可能是誰呢?
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的是,這件事發生在什么時候。好在“京師大水”四個字提供了一些線索。
據《開封府志(康熙)》卷三十九《祥異》:
嘉祐二年夏六月開封大水,壞安上門及大社、大稷壇。
包拯擔任“權知開封府”的時間是從嘉祐元年十二月到嘉祐三年六月為止,因此可以獲知,拆毀中官勢族園宅亭榭一事,當在嘉祐二年的六月。
按《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八十五,五月辛巳條目下:
內侍副都知、昭宣使、果州團練使武繼隆遷宣政使,尋罷之。此據百官表,不詳何事。韓絳行狀、神道碑及本傳并云內侍武繼隆遷官,絳封還詞頭,因數其過惡,遂出為鄆州鈐轄,當即此事。不知實錄何故不書。
據此,武繼隆升遷為宣政使是在五月上旬,但不久遭到了罷免。具體罷免的時間并沒有說。
所謂的“宣政使”是內侍班官,屬于內侍遷轉高階與加官,極難獲得,須特旨除授,為正六品。太宗朝權閹王繼恩因軍功方能遷宣政使,可見其貴崇難得。即說,武繼隆以內侍班官正六品昭宣使、遙郡果州團練使,擔任內侍省右班副都知。因內侍省左右班都知不常除授,因此內侍省領省官即左班都知和右班都知,而武繼隆為內侍省副貳長官。只是宋代內侍另有入內內侍省,權責一般更在內侍省之上,但稱呼武繼隆為“中貴人”“大珰”那是沒有問題的。
按照李燾在《長編》中的說法,武繼隆被罷宣政使的原因不詳,并且奇怪的是,《仁宗實錄》里沒有記載韓絳封還武繼隆升遷宣政使圣旨詞頭和論列其罪愆,并導致武繼隆貶官鄆州鈐轄出外的事情。
《仁宗實錄》為何沒有記載此事呢?好在李燾特意提及,說“韓絳行狀、神道碑及本傳”中都記錄了下來。
據李清臣所撰《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即韓絳神道碑):
(韓絳)轉禮部員外郎,罷諫職,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修起居注,試知制誥。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詞頭,陳其罪,出繼隆為鄆州鈐轄。
在這里,武繼隆遷官不成而反遭貶黜的線索是相對明確的。韓絳作為“知制誥”負責撰寫外制詞,武繼隆遷官宣政使一事,當然要有由這樣的兩制大臣根據圣旨詞頭來寫,而兩制是有權封還除拜旨意的。不僅如此,韓絳后來還彈劾武繼隆,只是神道碑中一樣沒有記錄所彈劾的具體罪名。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疑問是,在《長編》中明確記載武繼隆為內侍省副都知,為什么《神道碑》里作“押班”呢?押班也是內侍的高級官職,但顯然要比副都知低。究竟是時代更早的《神道碑》記載有誤,還是李燾的《長編》寫錯了呢?
今按出土的《包拯墓志銘》:
中人有構亭榭盜跨惠民河壖表識者,會(中缺)詔書廢墀便河壖廬舍,完復舊坊,中人自言地契如此。公命(中缺)丈余,得河濡表識,即毀撤,中人皆服,遂坐(中缺)官。
墓志銘中能見到許多細節,即當對方拿出地契后,包拯明察秋毫,令開封府兵丁差役等前往挖掘了一丈多深,找出了真正的河岸界碑標志所在,那么地契“偽增步數”的事實也就十分明白了。
更重要的是,這一段記錄提到了“遂坐(中缺)官”。從上下文及當時史實來推測,應當是表達了“中人”遭罷官、奪官、免官之類的意思。
然而據《長編》來看,武繼隆“遷宣政使”不成,即“罷官”或在五月—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其遷官事廢止哪怕在六月或以后亦無不可,關鍵是其“罷官”乃由于韓絳之封還詞頭,與包拯自是兩件事。而此處若為“免官”一語,便能解決《長編》作“副都知”而神道碑作“押班”的疑問。
換言之,嘉祐二年五月間,有旨武繼隆遷官宣政使,而知制誥韓絳封還詞頭,其遷官終究不成,此其“罷官”;六月間包拯奏劾武繼隆侵占惠民河岸事,乃從內侍省“副都知”免官為“押班”;加上(更有可能是同時或之前)韓絳論列武繼隆之罪,這些因素的疊加下,最終這位大珰以“鄆州鈐轄”離京補外。至于《神道碑》中“押班武繼隆遷官”,恐怕只是李清臣以武繼隆后來左遷時的職務為稱,并非以押班而遷宣政使。
但僅僅是時間線上的較為吻合還不足以讓我們的推斷具有說服力,因為就上述的史料來說,還不能解釋《長編》中“不知實錄何故不書”的疑問。
幸好司馬光留下了一本《涑水記聞》。
在《涑水記聞》卷五“嘉祐違豫”條目下詳細地記載了一樁驚心動魄的陰謀,原文較長,今節錄后逐一分析: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既卷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復卷簾,趣行禮而罷。
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邪?”彥博知上有疾,猝愕無以對。然尚能終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
這是整件事的背景,在嘉祐元年正旦大朝會上,仁宗皇帝忽然“風眩”發作。這大約是一種中風(腦卒中),天子趙禎整個人甚至無法保持坐姿,而是不由自主地向一側傾斜,導致通天冠都搖搖欲墜了,左右儀鸞司諸人趕緊放下了簾幕……到紫宸殿招待遼國使臣的國宴時,皇帝竟也胡言亂語,沒能安坐如儀至終席,便被扶回了宮中。
初七日,事情在向更驚人的情況發展:
庚申,兩府詣內東門小殿門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宰相曰:“相公且為天子肆赦消災。”……曹后以是亦不敢輒近上左右。……上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文彥博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宿于殿之西廡。史志聰等曰:“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何論故事也?”
皇帝喊出了曹皇后和內侍張茂則謀逆的“胡話”來,并且趙官家的病情發展到了完全不能處理政務的情況。于是次日初八,宰相文彥博為了能讓兩府宰執留宿宮禁之中,甚至想出了在大慶殿設立道場,為天子祈福的辦法,而宰臣們則臨時睡在大慶殿西面的廡殿內。這是沒有舊章可依的“出格”舉動,但文彥博堅持為之,除了天子的病情,是否還有他憂心的事情呢?
壬戌,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眾心。癸亥,賜在京諸軍特支錢。兩府求詣寢殿見上,史志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問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子,赦天下。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
初九日,仁宗稍稍有所好轉,一度在崇政殿內短暫地“接見”了重臣們,想來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御前會議,天子是否恢復了語言能力也未明說。因此第二天,宰臣們要求進皇帝的寢宮福寧殿視察圣躬,內侍都知史志聰等頗欲阻攔,以為不可。在文彥博的政治盟友,另一位宰相富弼的斥責下,史志聰等大珰才不敢違抗輔臣。文彥博等必欲見到皇帝,只是為了察看天子的病情嗎?
正月十一日,東京城內竟有禁軍兵卒聲稱殿前司僅次于都指揮使副的第三號人物,即殿前司都虞候準備發動兵變作亂!誰不知道太祖趙匡胤是以殿前司都點檢的身份得了天下的呢?為了平息這種謠言,穩定人心,首相文彥博果斷請次相劉沆一同簽書,直接將誣告謀反的兵卒斬首……
天子的“譫語”、內侍宮人們的遮遮掩掩、殿前司都虞候謀反的傳言……在這些波譎云詭之外,甚至滾落下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這一切的背后,是否另有隱情讓局面如此緊張呢?
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接著記述:
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候兩府聚處,于大慶殿庭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顧未有以制也。后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眾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武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我們終于等到了武繼隆的出場,甚至還看到了幕后真正操控之人的名字,原來武繼隆竟和一位前宰相勾結在一起,背后是賈昌朝在玩弄陰謀詭計!此人是范仲淹、韓琦、文彥博、富弼等人的政敵,他利用天子圣躬不豫的機會,雖然其身在北京大名府,卻仍然遙控一切,通過大珰武繼隆來脅迫、唆使兩名司天官員(不詳是司天監抑或翰林天文院),命二人公然聲稱皇帝病重和宰相富弼令人在京師北面開河有關。更可怕的是,這二人還上奏請曹皇后“同聽政”!
這實則就是在策劃一場不流血的政變。如果通過制造開河有傷地脈而造成天子不豫的輿論浪潮,“坐實”宰相富弼的決策失誤,那么作為首相的文彥博自然也難辭其咎,在巨大壓力下,二人將不得不辭相。曹皇后垂簾聽政之后,通過武繼隆之流的進言,賈昌朝就很可能再入相,大約在他們想來,如此則內外大權就能操持在其手中!
但文彥博終于將這一切消弭于近乎無形。
他以“族誅”使司天官員懾服屈從,不敢稍有違背,又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不令中外驚疑;隨后立即命此二人再勘定開河方位究竟與京師有否利害,從輿論層面進行化解;當武繼隆察覺關節,想要阻攔時,洞悉一切的文彥博輕易便制服了他。
這樣我們就能知道,武繼隆竟是一場巨大陰謀的參與者。其背后牽涉到賈昌朝與文彥博、富弼的權力斗爭,甚至天子與皇后都被放到了棋盤上。賈昌朝的權術、狡詐、奸邪,至于如此。
諷刺的是,到了此年十一月,賈昌朝反而以樞密使的身份被重新召回京師。這便讓仁宗皇帝看起來仿佛一個完全被蒙在鼓里的糊涂天子。
今按《長編》與《神道碑》均不言韓絳所數陳武繼隆之惡、罪為何,李燾又云《仁宗實錄》不書武繼隆貶謫出國門事,恐怕正是因為諱言仁宗被如此小人與賈昌朝所蒙蔽之事。
從時間線索來看,仁宗皇帝很可能直到韓絳論列武繼隆罪惡之際,才知曉了去年初的一連串“風波”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而為了天子的顏面,似乎并不該以武繼隆參與宮廷陰謀的罪名懲辦他,那樣等于向朝野坦承皇帝受到了愚弄。“恰巧”這時候(或前不久)包拯奏劾武繼隆等中官勢族侵占河岸土地,那么用這一罪名來把武繼隆貶出國門,倒是保住了趙官家的體面。
因此我們看到,皇帝甚至沒有同時處理賈昌朝,這位樞密使被罷免執政要等到次年,也就是嘉祐三年的六月。有趣的是,在賈昌朝罷樞密使的同一天,文彥博也遭到了罷相出外的處理。仁宗似乎把氣也撒到了文彥博頭上,或許在他看來,首相在御前對此事三緘其口,已屬欺君,頗是可恨。此后到仁宗登遐的五年內,文彥博再也沒能回朝,更遑論重登宰輔。
而巧合的是,在六月間,包拯由“權知開封府”遷官“御史中丞”,這是塵埃落定后的“獎賞”嗎?
那么為何在嘉祐二年時,包拯的奏劾會如此“恰巧”呢?
原來包拯并非天子孤臣、無黨無派,他在朝中也確有“靠山”。
考察包拯進士登科之年,乃天圣五年王堯臣榜。他的同年有誰呢?正是文彥博和韓琦。包拯升遷的快車道,也與文彥博、韓琦為宰執大臣的時期高度吻合。
假如上述的推測無誤,那么包拯對武繼隆的彈劾,恐怕更是要劍指樞密使賈昌朝。畢竟在包拯看來,攻擊賈昌朝,便是保護文彥博和韓琦了。
富弼用李仲昌策開河,單就此事來說,開河確乎是失敗的,甚至“而患滋甚”,到了“費國虐民”的程度,當時絕不是只有賈昌朝論及開河,彈劾武繼隆的韓絳就曾彈劾過李仲昌。然而此事上文彥博卻為富弼遮掩彌縫,李仲昌被棄車保帥遠謫嶺表。包拯并沒有就這一件事,對文彥博的做法有過任何的“聲音”。
另外,文彥博與包拯兩家交情極深,二人的父親便是同僚友人,包拯去世后,文彥博更將女兒嫁給其子包授為妻。
根據這些推測,我們甚至看到了一個參與“權力游戲”的“包青天”。
◆ 王 晨 上海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大宋文臣的品格》《締造的“中興”:南宋紹興三十二年的政局與人物》《陸游的詩詞人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