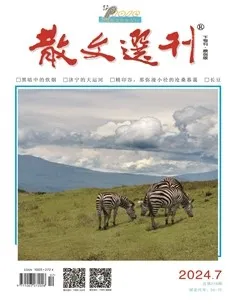母親的解放腳
母親今年86 歲,長了一雙“解放腳”。所謂“解放腳”,是指剛裹腳不久,還沒成型時就不再纏足,但四個腳趾頭已經畸形。
由于母親腳的特殊,小時候見母親修腳指甲特別費勁費時,而且由于工具不趁手,母親的腳趾頭經常溢出鮮血,卻是疼痛難忍也要強忍著修剪。隨著年齡的增長偶爾也會給母親剪腳趾甲,卻不得訣竅。
忽然有一天,發現小區內開設了洗腳店,價格比較親民,第一時間辦卡,帶著母親去洗腳。開始母親是抵觸的,大概是因為在老年人看來腳還是具有私密性的,二來還是怕我花錢。隨著帶去的次數多了,也知道花費不多,母親愛上了洗腳,大概一兩個月就主動要求帶她去洗腳、修腳。
母親逐漸與洗腳店的老板熟悉起來,每次去都有拉不完的呱。母親說“舊社會”女孩子七八歲甚至五六歲就開始裹腳,剛開始纏腳時因為要把除大拇指外的其他四趾盡量朝腳心拗扭,疼得撕心裂肺,火燒火燎,整夜無法入睡,時常會在夜里疼醒,那時也沒有止疼藥,只能生生忍受……母親感嘆說:“幸好全國都解放了,就不用再纏足,躲過一大劫。”
母親常常說自己趕上了好時候,能吃飽喝足,讀書上學,畢業后,還被選中在學校當民辦老師,在校期間,大膽樸實能干的母親被推選為團支部書記。母親在開黨員會時,懷抱一歲多的大姐步行從鄉下到縣城開會,邁著“解放腳”,母親是如何一步步、一步步忍著鉆心的疼痛走過近60 里路?后來隨著孩子增多,又有政策號召干部工人下放到農村,母親便積極響應號召,回村當起了全職農婦,下地不遺余力干農活兒掙工分。后來,勤勞公正的母親又被推選為大食堂的“司務長”,干了一個村子人吃飯的“良心”活兒。
閑暇與母親聊天,她回憶說真正的小腳除大腳趾頭外,其余四個掰斷的腳趾頭蜷曲著由腳心底下向內側臥倒,平時還要用裹腳布使勁兒勒著,再穿窄窄的小鞋,怕腳再長大。大姨就是小腳,活到101 歲,到100 歲時還是自己獨居,自己收拾家務,兒女家的條件再好,也不愿意去住。后來不小心摔了一跤,再也沒起來,臥床后不久就去世了。大姨父50 多歲就去世了,大姨一個人含辛茹苦供孩子們成家立業,兒女后來都有了出息,也孝順,可是大姨離不開那個小山村,她的小院。
母親50 多歲就離開了她熱愛的土地,伴隨著她一個又一個外孫、外孫女的誕生,甚至是侄孫的誕生,隨時改變住址。說是享兒孫繞膝之樂,實際是看完兒女看子孫的踐行者,因此不得休息,加之年輕時太過勞累,最終膝關節壞死,不得不動手術。
那是黑暗的一天,漫長的一天。
我們五姐妹齊刷刷聚到醫院,手術簽字時,姐妹五個就忍不住淚水婆娑,強忍住不讓淚水流出來,笑著為老人家加油。母親卻出奇的平靜,絲毫沒有手術前的緊張與害怕。后來她告訴我們:已經這樣疼了,還能疼到哪里?再說有我們五個“小刷帚頭”(母親一直認為我們五姐妹就是她的“小刷帚頭”,比“小棉襖”還要貼心的比喻),她也會平安地出來。
母親被推進手術室,我們又像父親做手術時那樣開始了漫長的等待。
我們姐妹五個終是控制不住,哭出了聲。父親做手術時,我們雖是傷心難過,卻認為父親是堅強的軍人,經歷過槍林彈雨的洗禮,是一座可以戰勝一切的高山。可是母親,我們受苦受難的親娘,我們已失去了父親,再也不能沒有了娘!
娘在兩個小時后被推了出來,醫生做了勝利的手勢,然后把一包東西遞到二姐手中:“你們看一下。”我們接過東西,來不及看,圍在母親身邊。母親是局麻,還很清醒,對我們說:“沒事,很好。”隨后,昏睡了整整一天。
安頓好母親,二姐把我叫到一邊,哆嗦著把醫生交給她的包打開,竟然是娘換下的膝關節上的骨頭!我難以控制,淚水頓時決了堤,肆意流淌……
母親至此行走更加不便,殘疾了的“解放腳”,雙關節植入的假體。
但是,母親用她的胸懷告訴我們,無論雙腳怎樣都要走正道,要有尊嚴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