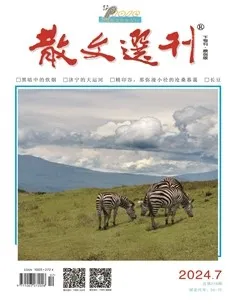饅頭
臘月,村里的磨面機房熱鬧非凡,村里最擅長發酵的邱大伯,一早就將蒸籠擔子挑到了我家的灶房。
母親洗了灶間,擦了灶臺,開始做飯炒菜,溫黃酒,外公和邱大伯坐在堂屋的桌旁,花生米就黃酒,喝得臉酣心熱。及至午后,邱大伯就甩掉了棉襖,掄起了膀子,和起了面粉,他在一口大缸里施展著身手,一上一下,一左一右,或雙手并按,或左右開弓,或包籠圍圈,或四散鋪開,那架勢,那姿態看得人眼花繚亂,一會兒,汗水從額間淌下,大伯索性脫掉了馬夾,只剩了一件汗衫,他咕咚飲下一杯開水,抬手抹掉兩滴汗水,將毛巾扔給呆若木雞的我,又迅速投入了一個人的戰斗之中,不知經歷了幾個小時的揉捏攪按,那口茶色的大缸終于恢復了平靜,棉被覆蓋了缸口,缸兒挪至了灶間。汽燈點亮了堂屋,大伯端起了酒盞,而我也在場外轉起了冰輪。突然,村頭的林二叔推門進來,于是又一輪酒香四溢,聲震如雷,終于,他們抹干了酒漬,清洗了桌面,掀起了棉被,打開了酵缸,邱大伯閃亮登場,唱起了主角,而一向爭強好勝的外公他們只能打下手,父親母親自覺技不如人,心甘情愿跑起了龍套。
大伯將那么一大團面酵從缸中提出,在案板上又是一輪上下齊動,左右輪番,不知大戰了多少回合,面團敗下陣來,一任大伯隨意蹂躪,大伯操起了大刀,一刀下去,分成了幾段,一段一段的面團搓起了長長的圓條,大伯左手抓起長條,右手輕輕一扭,一小團一小團的面疙瘩就撒落在案上,外公二叔和父母就開始在這面疙瘩上大做文章,他們搓起了面團,包起了菜餡兒,捏起了唇邊,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搶過一個面團胡亂揉搓,父親輕斥一聲,而我不以為然。母親分配了任務,讓我沾著胭脂點紅點,蘿卜絲的點一點,咸菜的點兩點,紅糖的不必點。可是點胭脂是最后的步驟,這中間的時光如何消受?外公拉起了我來到了灶膛,紅紅的火焰照耀著我的臉蛋兒,大鍋里熱水在沸騰,灶膛里樹枝在燃燒,一個個饅頭裝上了蒸籠,一片片蒸籠疊在了鍋灶,我上上下下,小腦袋探個不停,我要添柴,外公不讓,我要加水,大伯不允,我要裝籠,父親阻攔,無奈的我搬起竹凳來到檐下,踮起腳尖,伸直手臂,掰下一根冰凌,尖尖的長長的冰凌啊,咬上一口,仿若是盛夏的冰棍,雖然無味,卻也美妙。鄰家孩子和我玩兒起了折冰的游戲,看誰掰的冰凌長,我一激動,搶著攀折,差點兒滑倒,鼻子凍得通紅,小手腫脹,乖乖地由外公牽回了灶膛,溫暖的柴火映射著我,我的身影在墻上舞蹈,小手熱了,小腳暖了,瞌睡也來了,頭一歪便倒在了灶間的稻草堆中。
不知到了什么時辰,隱隱聽到了屋外的贊嘆聲。“這饅頭可真豐滿啊,味道真香啊!”“饅頭!”驀然睜開蒙眬的惺眼,一骨碌爬起,正看到大伯揭起蒸蓋,一股面香迎面撲來,嗅嗅鼻子,舔舔嘴巴,小跑著跟著大伯來到場邊,一個個饅頭頃刻間映入眼簾中,它們規規矩矩排著方陣,紋絲不亂,白白胖胖的精靈啊,靦腆地坐在那里,不聲不響,卻散發著誘人的香味,我急急地捧起一只,忙忙地咬上一口,呀,太燙,兩只手輪流打轉,卻舍不得丟下,這饅頭可真美味啊!
直到小肚子撐得圓圓鼓鼓,我們才開始了清點工作:圓的是饅頭,長的是酵條,方的是饃饃,哎喲,我數不過來啦!
責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