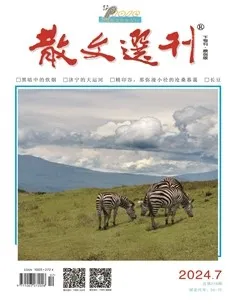我的姥爺姥娘
我的姥爺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種了一輩子地,是種地的老把式,勤勞、樸實、老實、節儉,所有贊揚農民的詞用在他身上都不過分。他像路邊的小草,像莊稼地里的一棵矮小的禾苗,但是,他卻是一名老黨員。
在我印象中,有兩次比較深刻:一次是我五六歲的時候,在他家吃完晚飯睡了,姥娘把我從床上喊起來,讓姥爺把我送回家,我不想走路,姥爺就背著我走。我們家和姥爺家是一個村子的,從村南到村北大概三四里路的樣子,我竟然趴在姥爺的背上睡著了。那時,姥爺的背已經有些駝了,但是卻很堅實溫暖。后來,姥爺的背駝得更厲害了,我走到他面前,他只能仰著臉看我,然后微笑著喊著我的小名,把我讓到堂屋里。現在回想,姥爺一生很少生病,即使有個頭疼腦熱的小病也會很快好的。
另一次是我都結婚生子了,回老家,姥爺知道了,佝僂著身子,步履蹣跚地來了,手里還拎著一條大鯉魚。還未等我上前去扶,姥爺不小心一腳踩在了淌水溝里,一下子滑倒了,我們嚇壞了,我和母親忙去把他扶起來,找了椅子讓他坐下。只見膝蓋處滲出了殷紅的鮮血,母親忙端來清水給姥爺擦了擦,又涂抹了碘伏,用紗布給包裹上了。我問姥爺疼不疼,姥爺仍舊微笑著說:“不疼。”幸好沒傷著骨頭,因為姥爺那時已經有八十多歲了。姥爺不善言談,坐了一會兒就要走,我和母親挽留,但是姥爺說:“年齡大了,能走動來閨女家看看就知足了,人老了不能在閨女家住。”姥爺就拄著拐杖晃悠悠地走了,看著姥爺遠去的背影,我的鼻尖感到一陣子酸楚。
后來,姥爺活了八十六歲就去世了。
我的姥娘個頭兒不高,是很精干的那種,先前當過八路軍,也算是老革命。姥娘也是受了一輩子罪,沒享過幾天福,晚年得了各種病,不到七十就飛升瑤池了。
由于姥爺家門戶大,舅多姨也多,母親一忙就把我送到姥娘家里,反正會有人照看的。姥娘平時做的飯都是粗茶淡飯,但是只要我去,姥娘肯定會做好吃的給我吃。上小學時,我放了學不回自個兒的家,一溜小跑就去了姥娘家,姥娘便圍上圍裙去小草屋(廚房)里生火做飯。有時我餓急了想先吃點兒東西,姥娘就會拿出一張她自己烙的煎餅再卷上白砂糖讓我先吃,姥娘怕糖漏了,就用白線把煎餅的一頭綁住,我就從另一頭開始吃。那個味道,現在想想都很甜、很香。
在孫子輩里面,姥娘還是比較疼愛我的。我隔三岔五地問姥娘要點兒零花錢,買個雪糕,買個零食,買個西瓜啥的。姥娘每次都會給,多則一塊,少則一毛。那時候,買根老冰棍才五分錢。姥娘弄點兒好吃的也會拄著拐杖送到閨女家,比如自家樹上結的大棗、栗子、柿子啥的,姥娘會挎著小提籃,里面裝得滿滿的,送過來。
去年給姥爺上三年墳的時候,在他們的老房子的墻上看到掛著的發霉的老照片,姥娘年輕時長得也很俊俏的,五官清秀,目光炯炯,不讓須眉;姥爺平頭正臉,目光平和,樸實無華。他們很平常,與中國大多數的老百姓一樣,悄無聲息地來,悄無聲息地去。他們熱愛那片土地,最終還是那片土地收留了他們。
責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