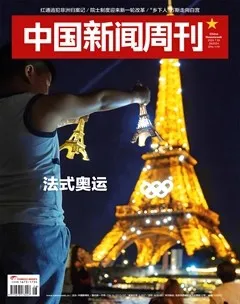為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創造契機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全文發布,其中提到“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總體上看中國在縮小城鄉差別方面是有較大進展的,城鄉收入差距已從2018年的2.69倍縮小到2023年的2.39倍,但差距仍是顯著的,其中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更為明顯。
我國有10億人被社會養老保險覆蓋,分為城市職工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在實際領取保險金的人群中有56.6%的人領取的是后者,但領取的金額僅占實際發放金額的5.9%,這個差距遠大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已完成立法保障和法定進城渠道的暢通,“進得來”的問題已基本解決,但居住證的含金量與戶籍仍有較大差距,教育、醫療和保障性住房的“歧視性”政策仍普遍存在,“留得住”和“融得進”的問題還遠沒有解決。
這種城鎮化的不徹底性,降低了社會的流動性;目前的資源配置方式也是不均衡的,城市在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土地交易收益等方面仍占盡優勢。這一切都是要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進程中通過深化改革解決的問題。
中國城鄉社會的共同發展一直離不開雙向流動的推動。當下中央已明確發文鼓勵退休干部、教師、醫生能夠下鄉或返鄉發揮“余熱”。在新型城鎮化的下半場重建城鄉雙向流動,通過從鄉到城接受前沿文化的洗禮,再從城到鄉實現文明與財富的傳播和擴散。這樣一種正向循環的建立,為鄉村發展注入可持續的動能。
在這個過程中,土地制度改革也要提供制度保障。當下從城到鄉的生產力要素流動有了明顯的方針引領,但政策落地尚待可操作的政策、法規去支撐。
首先是下鄉返鄉的人能否重新獲得農村勞動集體的身份認同。目前農村的組織形態和資源、財產以及收入的分配是以勞動集體所有制為核心運轉的,雖然基層做了不少類似“榮譽村民”的變相認同實踐,但這是不穩定激勵機制的產物,缺乏法律保障的身份認同地位仍是當下返鄉下鄉的阻力之一。另一個當然是農村最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土地問題的解決出路。
一是耕地的使用如何適應農業現代化的需要。中央已多次明確土地承包權的延續性政策,本次《決定》指出,有序推進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試點,深化承包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改革,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
耕地所有權屬于勞動集體組織,承包權落到農戶個人,經營權則可以大做文章。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推進,現代農業技術的普及也會遵循規模效應的需求,所以未來耕作制度從小戶單營到小戶兼營,再到大戶專營和新型勞動集體合作機制的形成是客觀規律使然。從保護農民利益角度看,耕地不僅僅是農村勞動集體和農民個體勞動收入的來源,也可以通過經營權流轉實現可觀的財產性收入。
二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入市問題。筆者認為,照搬傳統房地產開發模式走一次性出讓的模式是最不好的出路,值得探索的路徑是受法律保護的、相對穩定的租賃制。實踐證明,適宜在農村發展的非農產業更受市場變化影響,業態迭代頻繁,豐枯變化迅速,要弄清楚的是集體建設用地的開發建設目的不是創造更多的“二房東”,而是培育農村現代化進程中所需要的非農產業,服務農村,增加集體組織和農戶個體的持續性可支配性收入。這部分土地不能一拍了之。
三是農民的宅基地問題。隨著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不少宅基地的主人已實現了非農化就業并開始融入城市社會,所以越是發達的地區,宅基地的空置閑置現象越多。自愿放棄權益,重新利用當然是理想狀態,但在現實中這種情況鳳毛麟角。目前更多的探索是建立合法穩定租賃的渠道,既有勞動集體組織的集租,也有農民個體的散租。近年來已基本完成的宅基地確權行動也為建立更高水平、更受法律保護的政府背書的農房租賃平臺建設提供了條件,這可以給農民個體創造長期穩定的財產性收入,為進一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創造新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