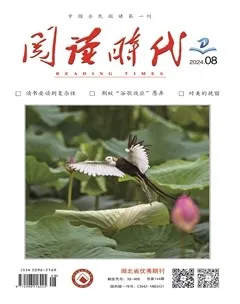五音盈耳
音樂的本意是使人快樂,誠如大儒荀子所言:“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音樂的“樂”和快樂的“樂”是一個字。“樂”的繁體字為“樂”,由三部分組成,“絲”是絲弦,“木”是桐木,合之是一張琴,中間的“白”是唱。《說文》謂:“樂,五聲八音總名。”五聲即五音:宮商角徵羽,八音指金、石、絲、竹、土、革、匏、木八類樂器,也就是說用八類樂器奏出五個音階的高低變化即音樂。
宮商角徵羽,相當于現代簡譜的1、2、3、5、6。與現在流行的七個音階比,少了4和7,堪為傳統音樂的基準音調。何以“宮商角徵羽”為名?有人說是據天上的星宿而起,這個說法有一絲神秘神圣的色彩;也有人說是根據禽獸的鳴叫聲音高低對應擬聲起的。
《管子·地員篇》謂:“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這個解釋太接地氣、太有趣了——凡聽徵的聲音,猶如一只小豬被背走而驚叫,凄厲哀傷;凡聽羽的聲音,像是一匹馬在原野鳴叫,嘹亮雄闊;凡聽宮的聲音,仿佛一頭牛在地窖里哞哞吼叫,沉穩持重;凡聽商的聲音,好像離了群的孤羊,咩咩有聲,溫婉纏綿;凡聽角的聲音,就像一只野雞躍到樹上打鳴,疾速清亮。
我喜歡這樣的解說,音樂的起源就是仿聲擬聲,與大自然息息相關。它不僅通過動物的叫聲呈現了音階的高低,而且還蘊含著情感心理的因素。
五音為正聲,但為補音階之不足,故又在其中加了變徴和變宮,也組成了七個音階。
如《史記·刺客列傳》寫荊軻在易水邊與朋友們壯別的一幕:“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于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這里先發變徵之聲,后為羽聲,從眾人的表現來看,變徵應為悲涼哀傷的音調,符合離別的氛圍,故大家都紛紛落淚哭泣;而羽聲明確指為“慷慨”,當為高亢之音,故而眾人群情激奮,怒發沖冠。
《紅樓夢》第八十七回“感秋深撫琴悲往事坐禪寂走火入邪魔”,寫黛玉撫琴、妙玉聽琴,也寫到變徴之聲——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聽他音調,也覺得過悲了。”里頭又調了一回弦。妙玉道:“君弦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里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么?”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議論時,聽得君弦嘣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寶玉道:“怎么樣?”妙玉道:“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
黛玉撫琴與高漸離擊筑的變徴之聲,皆流溢出的是悲傷哀婉的情緒,而黛玉音調調得過高,悲傷過度,故而弦斷琴崩,暗合了人物早亡的悲劇命運。
音樂的旋律節奏,萬千變化,是人心志情感的自然生發,也反過來對人產生影響。中國傳統音樂奉行的審美原則是“中正平和”“典雅純正”。司馬遷認為“音正而行正”,賦予五音以強烈的道德色彩。而《禮記·樂記》更是將五音政治化了6c4d6b5284cd960da9418d92128358a0:“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五音調和不亂,則政通人和,若出現互相侵犯的雜音,則有亡國的危險。
《韓非子·十過》記載了一段師曠為晉平公撫琴的故事。師曠是春秋時期有名的盲人音樂大師,《陽春》《白雪》即為其所作。一天,師曠彈奏了一曲《清征》,引來十六只黑鶴延頸而鳴,舒翼而舞。晉平公大悅,說沒有比這更美妙的曲子了吧?師曠說,《清角》更好聽。晉平公說,能彈來聽聽嗎?師曠說,不可,君上德薄,還不夠格聽,聽了會招來厄運。晉平公說,自己年齡大了,也就這個愛好,希望能聽完。師曠不得已,就彈奏起來。聲音響起,只見有烏云從西北方向涌來,接著彈奏,平地刮起了大風,暴雨也隨之而至,扯壞了帷幕,案幾上的杯盤摔碎一地,廊上的瓦噼里啪啦墜落,賓客四處奔散,晉平公也嚇得趴在地上。由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晉平公也患病癱瘓了。
這個故事用夸張的傳奇筆調描述了師曠琴技的高超絕妙,同時也昭示了音樂的道德能量。音樂有正聲,也有“鄭聲”,孔子說:“鄭聲淫,佞人殆。”頹廢柔媚的靡靡之音消解人的意志,是亂世之音、亡國之音。《史記》記載,那個大名鼎鼎的商紂王貪戀酒色,“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最終身敗國亡是必然的結局。
宮商角徵羽,看到這五個字,即覺典雅純正,古色古香,耳畔仿佛響起鐘鼓之鳴、絲竹之聲,余音裊裊,不絕如縷。而宏富浩博的音樂豐富著我們的生活、滋潤著我們的心靈,絕對不可或缺。
(源自《中國社會報》,平林月薦稿)
責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