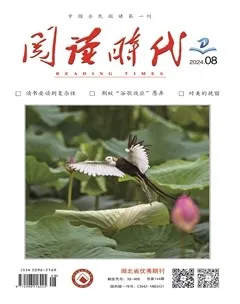圓夢書柜
2018年春天的一個日子,正在臥室梳妝臺下面和上面壁柜中找書的我,突然聽到妻子說:“你應當買一個書柜了,這太不方便了。”這句話,說出了我多年的心聲。我立馬下定了買書柜的決心。但走遍周邊家具店,我都未遇到心儀的書柜,直到妻子把網上書柜的圖樣發給我,才有了進展。當年5月2日上午,當家具店工作人員在我的臥室將一只黃色書柜組裝完畢時,我竟恍惚有“初聞涕淚滿衣裳”之感。
其實確切地說,我的書柜夢源于我上小學時。那時,我省吃儉用,用積攢的錢買了很多連環畫。這些連環畫如同磁鐵,吸引了周圍的小孩子。他們蜂擁而來,向我借閱。為了不讓他們拿走,我打起了家中“書柜”的主意。

說是“書柜”,其實是一張祖傳的簡陋舊書桌。它只有一米多高,幾十厘米寬,有三個抽屜。我把那些連環畫收藏在中間的大抽屜內。為了防止他人偷走,我還在外面裝了一把小鐵鎖。正當我為此“發明”暗自竊喜時,有一天連環畫居然不翼而飛。我大驚失色:是誰偷走了?經過“破案”,原來是比我小四歲多的大侄子。他看出了我“書柜”的秘密破綻——抽屜與旁邊的兩個小抽屜間的空隙很大。聰明的他從兩邊抽屜把手伸進去,就可夠到我的連環畫。我氣急敗壞,對著大侄子連嚇帶哄,但結果是,他仍照偷不誤。
那時不知道書柜是什么樣子,只知道要是有個能專門裝連環畫的地方,別人偷不到就好了。只可惜現在任憑我冥思苦想,總回憶不起那只“書柜”是何時被家里人收回去的。那些連環畫又是什么時間失散的?去了哪里?
1979年7月,我初中畢業,回到莫愁湖大隊15隊,從此開始了繁重的勞動。我先是萌發了當畫家的理想,后來又開始自學文學創作。其間,我挨盡了父親、繼母等的打罵,我的筆墨紙張經常被他們毀掉。那時的我,多想擁有自己的書柜啊!
第一次見到書柜,是在8隊的文友黃智輝家。看到那比我還高的大柜子開著幾扇小門,里面裝著琳瑯滿目的文學書籍,我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心花怒放。“你這裝書的家伙叫啥?”我問他。“這是書柜,你不認得嗎?”他露出輕蔑的哂笑。“這就是書柜啊!”至此,我才首次知道了書柜的形狀。
自從發現這個寶貝后,我就魂牽夢繞,經常光顧他家。我記得從他書柜中借回的書籍有蕭殷的《創作談》,泰戈爾的《新月集》《飛鳥集》等。從那時起,買書柜的種子就開始在我心中生根、發芽。
從文學的夢中清醒過來時,已是1988年。其時,我愛情的樹苗已開始鉆出地面,為了改變困境,我自學栽培平菇,遠赴沅江市郊當專業戶。離開前夕,我把《詩刊》《星星》《新華字典》《漫談詩的技巧》和樣報樣刊及手稿等,裝入一只纖維袋,送到了大哥家的豬圈頂上。后來每回來一次,我都要看看它,擔心人家拿走。我想:等我有了房屋后,我也要添置書柜,讓它們擁有自己的家園。誰知“天有不測風云”。1996年夏天,一場罕見的特大洪水將大哥家的房屋浸泡了一個多月,我的纖維袋中的“珍寶”也化為烏有。
當新世紀的曙光照暖寒冷的冬天時,我和妻女終于結束了九年的租房生活,住進了益陽市資江風貌帶畔的三室兩廳。住進去前,妻子把我在益陽市購買的漢語言文學教材等,先運到了新居。也許是因為臥室梳妝臺下面和上面的壁柜中空空如也,她把這里當成了“書柜”。誰知這一放,就將我購買書柜的夢想束之高閣了十六載。
記得每次在那些積壓在一起的書籍中找書時,我總是找得心力交瘁。彼時的我也有過買書柜的想法,但轉念一想:家中空柜子比比皆是,還是節約為好。有時,我也會突然想起那“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的對聯。上聯非常貼切,這些雜亂無章的書籍聳起,可不是一座座青山嗎?而下聯呢?相思什么?應當是書柜。我的燈在想念著書柜,我還能無動于衷嗎?
現在的每一天,我都喜歡佇立在高大的黃色書柜前,開啟六扇玻璃門,感覺就像是阿里巴巴看到了藏金銀珠寶的山洞。凝視那五層書架中一疊疊樣報、樣刊、全國征文的獲獎證書等,我覺得自己是“夕雨紅榴拆,新秋綠芋肥”的田園詩人,正在欣賞豐收的場面;又像是君臨天下的霸主,在進行“沙場秋點兵”;鎖緊書柜門,我又是最高統帥,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豪情。
我想:在明亮的光線下,在分門別類的書柜中,輕而易舉地查找到書籍,是對時間的珍惜,是對書籍的敬畏,是對眼睛的珍愛。沉浸在擁有書柜的氛圍中,縱使遇到煩惱的事情,頃刻間也會蕩然無存。我以為:家庭可以沒有鮮花,但必須要有書柜。書柜讓書的靈魂得以憩息,讓愛書人得以沐浴經典的輝煌與優雅。
責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