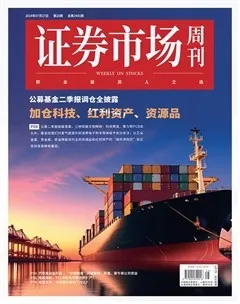洞悉貧窮的本質
美國的兩位發展經濟學家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窮》一書中,對貧窮問題進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最終,兩位學者對在世界范圍內消除貧窮總體上給出了樂觀的結論。
這本書討論的貧窮不是普通的“沒錢花”,而是“極度貧窮”,具體定義為每人每天16印度盧比(相當于36美分)以下。書中給出了一個數據,2005年全球有8.65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3%)處于這種極度貧窮的狀態中。
將近20年過去了,我并不了解同樣標準下的貧困人口數量變成了什么狀態。網上看到世界糧食計劃署披露2023年有3.33億人經歷了極端饑餓;聯合國則報告目前全球仍有約7.35億饑餓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9%)。這樣看來,我覺得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處于“極度貧窮”的人口和占比總體應該是在減少的。
捐贈是一件復雜的事情經濟學家們想要弄明白如何才能夠消除貧窮,如何才能夠切實幫助這些處于窮困境地的人們改善生活。很自然的一個想法就是援助和捐贈。援助什么?捐贈什么?是直接金錢援助還是物資援助?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復雜。我在旅行時也見過村里人家將慈善機構捐贈的圖書拿回家墊桌角。有些直接援助金錢的項目,也由于體系的腐敗,導致最終援助效果非常低下。
援助的反對者由此認為弊大于利。這些人往往是市場派的支持者,他們認為只要自由市場正常發揮作用、采用恰當的獎勵機制,人們就可以自己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援助會使得當地人們停止自己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作者顯然并不認同純粹市場派人士的觀點,反而認為適當的、認真考慮過作用機制、仔細推敲過實施細節的援助計劃是有其合理性的。
例如,關于使用蚊帳可以極大改善熱帶貧困地區人們的生活狀態,減少疾病傳播,這是科學家們公認的一些結論。基于此,慈善組織給有關地區的人們捐贈了蚊帳,但卻發現使用率并不高;這些接受捐贈的家庭后續也沒有表現出更愿意購買蚊帳的傾向。為什么改變行為如此困難呢?可能源于這樣一種深層的自我心理暗示——陷入貧窮陷阱的“我”做什么都無法改變目前的現實;在未來,并不可能有什么驚喜在等待著“我”;又何必做一些無謂的嘗試呢?
在這底色灰沉的生活中,窮人唯一能夠把握的是眼下的生活和手頭的錢財。因此,很多不合理的行為可能都能得到解釋。手頭的錢換成糧食,應該可以滿足全家人的熱量需要,但窮人卻去買了其他物品。因為這些東西給他們提供了另外一些心理滿足。這可能是死氣沉沉的生活中,為數不多的值得快樂的事情。
“家長式”幫扶是否有必要?
科學家的研究發現,童年期間的痢疾復發會永久傷害孩子的身體及認知上的發育;與患過瘧疾的兒童相比,未患過瘧疾的兒童長大后每年的收入要多50%(當然,這樣的研究需要控制許多變量)。為了控制瘧疾,慈善組織為熱帶貧困地區家庭發放了消毒劑,只需要在喝水之前放一點就好,但科學家驚奇地發現人們并不這樣做。即使志愿者進行了宣講,收效也甚微。后來,某地區的志愿者想出了一個辦法,在村子打水的水井旁安裝一個免費釋氯器,村里人在打水的時候只要轉動一下這個儀器的把手,氯元素就會釋放一些到水中起到消毒殺菌的作用,極大改善了當地人的用水安全。這個案例得到了兩位作者的高度贊揚,作者是贊同通過審慎的機制設計來實現“家長式”幫扶。
也許有人會提出,最徹底的幫扶應當是在教育上幫扶,提升窮人的認知水平,讓他們擁有掌控自己人生的能力。
教育任重而道遠書中引用的調查資料顯示孟加拉國、厄瓜多爾、印度、印尼、秘魯及烏干達的教師平均每5天就會缺席1天,其中印度和烏干達的教師缺席率是最高的。對這些地區兒童教育水平的調查結果也非常令人失望。
為了讓孩子們盡可能入學接受教育,直接給小孩父母進行補貼,這樣的行為合適嗎?反對“家長式”幫扶的人肯定認為不合適。從實踐角度,一些慈善組織為送女兒上學的家庭支付一定補貼,研究發現這確實提升了所在村莊女孩的入學概率,并且女孩的體重也有所增加。我覺得這些錢花得值得,哪怕這些女孩只多上了幾天學。
貧窮能夠被消除嗎?
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A·羅賓遜在《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中研究了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探究這些貧富差距是如何產生并發生變化的。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答案是制度,他們具體將制度從包容性(inclusive)與汲取性(extractive)、政治與經濟等不同維度進行劃分,展開比較研究。按照這兩個維度將各個國家裝進四個象限: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最后這種制度組合可能不存在。
其中,包容性經濟制度至少需要具備以下特征:保護私有財產、公正的法律制度和提供公共服務等,為社會上所有人的交易和簽約提供基礎(而不僅僅是特權階層);允許和鼓勵大多數人參與經濟活動,個人能夠自由選擇;允許新企業進入,允許人們自由選擇職業。包容性經濟制度要想確立離不開國家的力量,諸如建立法律秩序、保護私人產權和提供公共服務等。
那么包容性政治制度又具有什么特征呢?《國家為什么會失敗》提到兩個主要特征:既要有多元化的特點(廣泛聯盟或多個集團),又要有足夠的集權(避免國家能力過于羸弱,國家陷入混亂紛爭)。任何一個條件不滿足,就是汲取性政治制度。
通常來講,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經常相伴,而包容性經濟制度則是在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那么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可能帶來增長嗎?可以消除貧窮嗎?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指出在兩種情況下是有可能的——第一種是掌權者將資源直接配置到了生產率高的活動中,可能帶來增長;第二種是允許某種程度的包容性經濟制度時,也可能實現增長。但這種增長可能是不能持久的。
通過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研究,可以看到糟糕的制度非常“頑固”,很難通過正常途徑將其消除。但班納吉和迪弗洛則比較樂觀,在指出了阻滯窮人走向富裕的三大問題——意識形態、無知和慣性之后,他們提出大量的政策失敗和資源浪費的背后,是政策規劃階段懶惰的結果,只要認真規劃、切實考慮,有效政策產生的積極結果必將進一步推動深層次結構的發展和改變。他們認為積硅步可以至千里,自下而上的觀念水位變化,可以帶來更深層次的結構變化。
(作者任職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
讀書介紹:

班納吉和迪弗洛對在世界范圍內消除貧窮總體上給出了樂觀的結論。
在指出了阻滯窮人走向富裕的三大問題——意識形態、無知和慣性之后,他們提出大量的政策失敗和資源浪費的背后,是政策規劃階段懶惰的結果,只要認真規劃、切實考慮,有效政策產生的積極結果必將進一步推動深層次結構的發展和改變。他們認為積硅步可以至千里,自下而上的觀念水位變化,可以帶來更深層次的結構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