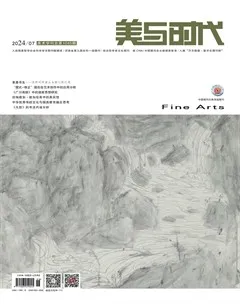“圖式-修正”理論在藝術創作中的應用分析


摘 要:圖像再現是藝術創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各門類藝術的共有特點,其中包含著藝術家與觀者雙方對于圖式的歸納、選擇與運用。藝術史家貢布里希在其著作《藝術與錯覺》中分析了圖像再現的心理學問題,論證了圖像再現中圖式與修正的運用邏輯,其對多領域知識的運用增強了論題的科學性和涵蓋范圍的廣闊性,引起了學者對于藝術與錯覺關系的探討和對“圖式-修正”理論的關注。將貢布里希在《藝術與錯覺》中提出的“圖式-修正”理論運用于藝術創作與圖像再現的分析中,以期推動藝術發展與視覺研究。
關鍵詞:“圖式-修正”理論;圖像再現;藝術心理學;藝術風格
一、“圖式-修正”理論的提出
藝術史家貢布里希于1909年3月30日出生于維也納,而后移居英國并加入英國國籍。他早年受教于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于1939—1949年供職于英國廣播公司偵聽部,而后在多家機構、院校任職。其家庭氛圍與教育、工作經歷為他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他先后出版了諸多舉世聞名的著作,如《藝術的故事》《藝術與錯覺》《秩序感》等。其對于藝術的研究成果對藝術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成為藝術史、藝術心理學和藝術哲學領域的大師級人物。
《藝術與錯覺》成書于20世紀,是一部有關制像的經典研究論著。貢布里希在書中對圖像再現的心理學及歷史進行了探究,從知覺心理學的角度回答了藝術為何會有一部歷史、何以會有風格等問題。全書共分四部分,涉及當時藝術界的諸多畫家、畫派、團體主張。如拉斯金、康斯特布爾等的觀點,20世紀初弗萊組織的后印象主義展會對年輕藝術家產生的影響,以及20世紀20年代以前出現的漩渦畫派、倫敦集團等,并著重地提及了印象派與自然主義中的再現與真實之間的關系與差異,分析了從古希臘時期到20世紀行動派繪畫中的圖像再現問題。此外,還包括漫畫、錯覺藝術等門類,檢驗了許多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觀念,改變了人們對藝術史中一些關鍵性問題的認識與理解,是研究藝術史最基本的再現問題的經典書籍[1]。其中,該書以“圖式-修正”理論最為出名,深刻影響了藝術創作與接受領域的理論研究。
“圖式-修正”理論是維也納藝術史家貢布里希在其著作《藝術與錯覺》中提出的重要藝術理論觀點。他在書中討論分析了藝術錯覺發展歷程中的本質和動力的種種假說,可大致將其分為知覺心理學、再現技法和觀看與知道三部分。知覺心理學強調人的知覺的多樣性造就了藝術的多義性與廣泛性,藝術家通過知覺感知世界,根據所見進行描繪,而又通過獨具個性的方式感知世界,結合觀眾多元的接受便會產生多義的錯覺[2];再現技法部分強調藝術史的發展取決于再現技法的發展,再現技法又與風格、社會因素相關,例如古埃及藝術和古希臘藝術中的再現技巧在之后的藝術史發展中可以看到;觀看與知道部分則試圖說明,藝術家努力擺脫自己已經形成的知識體系,企圖通過眼睛所見來描繪真實的世界,恢復“純真之眼”,同時得出了“純真之眼”并不存在的結論,并將其核心思想“圖示-修正”理論貫穿其中,運用心理學等學科進行論述。
二、藝術家與概念性圖式
“圖式”一詞源自古希臘文,原意是外觀、形象,后來轉譯為對最一般的本質特征的描繪,或略圖、輪廓、抽象圖形。對于圖式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康德的“圖式論”,他巧妙地利用圖式抽象理性與具體感性的矛盾統一特性,使其出現于先驗哲學的語境之中,使得圖式具備了造型因素之外的含義。在康德的“先驗圖式說”中,他將圖式視為知識結構,而先驗即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間的一種思維,圖式是先驗純粹想象力的產物和主動創造的成果。康德的“先驗圖式說”與貢布里希在《藝術與錯覺》中所貫穿的“圖式-修正”理論有一定的共通之處,二者均認為“圖式”由經驗積累而得。康德強調純粹性,而貢布里希著重論證“圖式-修正”理論在藝術中的普適性。
在《藝術與錯覺》中,與其說貢布里希是在論述一種“先驗圖式”的矯正,不如說是一種概念性圖式的矯正過程。這種概念性圖式是籠統模糊的,類似于偶然性的墨跡。藝術家在創作時,或多或少地會運用到知識中已有的缺少細節的概念性圖式,并對其進行反復矯正,以達到描摹的目的。這種概念性圖式在古埃及藝術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古埃及繪畫中的人物形象與現實相距甚遠,其“正面律”的運用使得畫面中的人物動態相近,對細節的描繪較少,但形象之間的種族差異較為明顯。古希臘藝術中對圖式的矯正則是一種“巨大的意外”,使藝術擺脫巫術用途而獨立存在,但即便如此,其也是先選取一個較為籠統抽象的圖式進行反復矯正,以貼近自然,這種矯正邏輯在當代藝術中仍可看到。由此可見,各個時期的藝術家在進行圖像再現時,都是根據已有圖式進行不斷矯正來達到預期畫面,而在其矯正過程中也會受到藝術家的心理、藝術手法與創作目的的影響。
三、藝術構思與表現中的“圖式-修正”
藝術功能是指藝術在人類實踐活動的變遷發展和個人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中所起到的能動作用,具體表現為藝術家在特定藝術領域的藝術創作過程中,該藝術形態給予藝術家的積極影響,或藝術家的創作行為和創作成果對藝術欣賞者起到的積極而獨特的作用。而貢布里希在《藝術與錯覺》中提及的功能與此有一定的差異,他所提到的功能并非純粹的藝術功能,而是物象的功能,包括藝術家創造形象時的目的和創作成果的功能,對應藝術創作過程中的構思與表現階段,正是這種目的影響了圖像再現的形式。比如在書中的第四節“希臘的藝術革新”中,他將古希臘藝術的創作目的與古埃及進行對比,點明古希臘藝術以輔助神話敘事為目的。古希臘藝術家在藝術構思與藝術表現的過程中進行“添枝加葉”,這種行為并不是進行虛構,而是為了加強敘事的生動性。他們以“不完整的物象”制造錯覺,打破“咒語”,從“令人信服”的藝術角度分析古埃及圖式并進行矯正。而在藝術表現階段,藝術形象會受到風格、手法的限制。
雖然藝術家在創作時有其獨特的目的,使其視覺圖像具備了不可否認的主觀性,但再現的準確性仍具備相對客觀的評判標準。各個時期的藝術家不滿足于前人對物象再現的方式或呈現效果,由此生成了不同的繪畫形式,傳統的圖示化程式不斷得到矯正,形成各具特色的藝術風格與表現手法[3]。以書中常被提及的康斯特布爾為例,作為18世紀優秀的英國風景畫家,他的風景畫摒棄了傳統油畫中的褐色調子,將春天與夏天的綠色調子引入作品之中,運用現實主義的自然觀對傳統油畫進行了改進,其速寫式技法對19世紀法國的印象派產生了重要影響。19世紀是機械和光電被發明的時代,照相技術的發展對藝術界特別是繪畫領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業內爭論紛繁。到了19世紀六七十年代,印象派產生并發展起來,該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馬奈、德加等,他們的作品在構圖與光影等方面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攝影的意味,即便是堅持對景寫生的莫奈的作品(圖1),也在視點的選擇、布局等方面受到了攝影的影響。
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對圖式進行矯正,以形成符合創作目的的圖像,但此過程并不是由矯正開始的,而是畫家先制作后匹配。在“制作-匹配”的過程中,人的心靈歸檔與投射功能起到了關鍵作用。藝術家通過歸檔與投射將所見物象轉化為藝術意象,并通過藝術手法表現出來,在此過程中獲得幸福感。正如皮格馬利翁的故事所說的那樣,藝術的力量并不在于描繪,而在于創造,藝術家先想創造獨特之物,而后才想與真實世界匹配[4],但是“在一件藝術作品創作的過程中,完全幸福的時刻是從未有過的”[5]。當作品完成之時,藝術家又會因其并非真實之物而備感絕望。因此,弗洛伊德才會感嘆“僅僅是一幅畫”,而達·芬奇也從藝術家轉變為了工程師。
四、藝術真實與創新中的“圖式-修正”
藝術作品無法轉錄自然,也無法成為真實的物象,卻能夠通過藝術手法的運用、情感的表達來實現藝術的真實。這種藝術真實的內涵包括三方面:首先,藝術的真實是假定的真實、美化的真實,藝術中的形象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或再現,人們僅在視覺或聽覺上感到它們的真實存在;其次,藝術的真實不僅是現象的真實,還是本質的真實,是現象與本質的真實的統一,通過對現象的真實反映來實現對本質的把握;最后,藝術的真實不僅是再現的真實,而且是表現的真實,在藝術真實中,再現與表現具備統一性。貢布里希在《藝術與錯覺》最后一節“從再現到表現”中,論述了個人風格與再現的評判機制之間的關系,指出雖然表現主義著作因急于擺脫程式而鮮少提到相互關系,但再現是對關系的重塑,它既是一種信息工具,也是一種表現工具,所以表現也是一種對關系的塑造。仍以康斯特布爾的繪畫觀念為例,他援引友人的觀點,指出藝術是想象世界和自然的結合體,這一點在《威文荷公園》(圖2)中清晰地體現了出來。可見,無論是再現的藝術還是表現的藝術語言,無論畫家以何種風格進行藝術創作,其過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再現與表現的因素。
藝術家對圖式的選取與矯正、對再現與表現藝術語言的運用和個人風格的延續皆體現于藝術創作的結果——藝術作品中。作品形成之時,評判系統便開始發揮作用,其中涉及對藝術獨創性與寫真程度的評判。前文提到藝術的力量在于創造而不是描述,而創造藝術的觀點是到了近代后才產生的。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其目的是創造獨一無二的作品,即追求原創性,但腦海中的圖式即“知覺”對原創性圖像產生了阻礙,因為無論選取何種圖式,都是對前人成果的矯正,這種再創造不是“原創”。由此,藝術家將目光轉向了“純真之眼”,企圖只通過觀看來創造出更貼近自然的圖像[6]。藝術家通過忘掉圖式的方式來刺激感官,想要無限地接近“純真之眼”,但正如貢布里希所說,努力忘掉和從來不知道之間有著天壤之別,描繪不可能重現之物也是依據已知圖式進行矯正。同時“純真之眼”不能被理解為“關系”,實現“純真之眼”即集中刺激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證據能夠說明事物在無偏見的眼睛中的樣子,并且人生必經過“概念化習慣”的階段。由他的觀點可知,他否定“純真之眼”的存在[7],并且認為藝術無法轉錄自然,也不可能再現真實,圖像再現的真實感需要通過藝術家與觀者心靈的合力來完成。
五、結語
藝術的歷史與風格在“圖式-修正”中產生并發展,在研究藝術史與風格的問題時,重點并非藝術家如何塑造錯覺,而是研究藝術發展的深層動因,激起對“可見的世界與藝術的語言”之間的探討。藝術語言的真正奇跡并不在于幫助藝術家創造真實的錯覺,而是藝術家通過藝術創作教給觀眾重新觀看可見世界與內心世界的方式。對此,我們應充分發揮想象力,并提升自身的模仿能力,通過不斷矯正來探求藝術的歷史與風格生成中的深層因素,以推動藝術的發展,在此方面我們還有廣闊的探索空間。
參考文獻:
[1]牟春.圖像效果的發現與發明:論貢布里希的漫畫研究[J].文藝理論研究,2018(3):78-87.
[2]王志.對繪畫再現理論之“錯覺說”的再反思:以沃爾海姆對貢布里希的解讀為中心[J].藝術設計研究,2019(3):113-116.
[3]李琦.寫真的界域[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6.
[4]余雅佩.藝術模仿中的錯覺:“模仿”所營造的矛盾魔域[J].美與時代(下),2015(5):50-52.
[5]貢布里希.藝術與錯覺:圖畫再現的心理學研究[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111.
[6]浦昕怡.藝術的“圖示”、“公式”與“算法”:對話貢布里希《藝術與錯覺》[J].大眾文藝,2018(24):95-96.
[7]劉國柱.貢布里希的藝術心理學與波普爾的科學哲學:從平行論角度解讀《藝術與錯覺》[J].新美術,2008(5):28-33.
作者簡介:
張玥盈,天津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藝術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