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山水畫與西方風(fēng)景油畫的空間意識差異


摘 要:中國山水畫與西方風(fēng)景油畫歷史悠久,繪畫題材豐富多樣,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與藝術(shù)特色。將中國畫中的山水畫與西方風(fēng)景油畫相比較,探析二者觀看與表現(xiàn)方式的差異性,并從中西方繪畫的始源形式與思想基礎(chǔ)切入展開具體分析,由此研究中西方繪畫中蘊(yùn)含的獨(dú)特的空間意識表達(dá)。
關(guān)鍵詞:山水畫;風(fēng)景油畫;空間意識
中國山水畫與西畫中的風(fēng)景油畫皆是對某一空間的描繪,畫面中的空間范圍被截取得廣大時(shí),其中空間意識的特點(diǎn)自然地被放大到可研究的地步。這使得人們不禁思考,畫中為何有空間意識?這對繪畫表現(xiàn)有什么意義?中國山水畫從圖像符號到器物紋飾再到人物畫中的背景,直到隋唐時(shí)期迎來形式上的獨(dú)立,經(jīng)歷了不斷蛻變。中國山水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在新石器時(shí)代的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的彩陶圖案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起伏的山川紋、水波漣漪紋,這些紋樣顯示了古代人民對自然山川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山水畫萌芽于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但尚未從人物畫中完全分離。到了隋唐時(shí)期,山水畫逐漸獨(dú)立,自此,其才漸漸有了有意識的空間組織,獨(dú)幅山水就這樣以山水為主角展開了對遠(yuǎn)大空間的描繪。在西方,風(fēng)景是作為宗教故事中的背景與配角出現(xiàn)在繪畫當(dāng)中的。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風(fēng)景在主題性作品中漸漸占有了更多篇幅與筆墨,至巴洛克時(shí)期,終于獨(dú)立成派。從背景、配角到主角,中西方繪畫都走過了相似的歷史進(jìn)程,但二者之間的差異也基于文化的差異性逐漸展現(xiàn)。
一、遠(yuǎn)近之序
雖然中國山水畫與西方風(fēng)景油畫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相似,但本質(zhì)上多有不同,最為直觀的就是兩種繪畫的觀看方式存在差異。下面具體分析繪畫作品的觀看方式,以兩幅具有代表性的畫作為例進(jìn)入此論題。
《秋林人醉圖》是清初“四僧”之一的石濤所作,他在題記當(dāng)中提及了這幅畫緣何而起:“昨年與蘇易門、蕭征乂過寶城,看一帶紅葉,大醉而歸,戲作此詩,未寫此圖。今年奉訪松皋先生,觀往時(shí)為公畫竹西卷子。公云:吾欲思老翁以萬點(diǎn)朱砂胭脂,亂涂大抹,秋林人醉一紙,翁以為然否?余云:三日后報(bào)命。歸來發(fā)大癡顛,戲?yàn)橹㈩}。”石濤與友人游山玩水,之后作了此畫,它既是一幅風(fēng)景畫,也是一篇游記,在對風(fēng)景的描繪中融入了敘事性的表達(dá)。再看彼得·勃魯蓋爾的《冬獵》(圖1),其描繪了尼德蘭農(nóng)民冬季出行打獵一事,同樣是一幅具有敘事性特征的風(fēng)景畫,甚至說是情景也不為過。
可以看到,兩幅畫雖然都是風(fēng)景畫,也都表現(xiàn)著人與景的關(guān)系,闡述著某件發(fā)生了的事,但其內(nèi)里卻蘊(yùn)藏兩種截然不同的空間意識。
中國山水畫對空間的表現(xiàn)方式有高遠(yuǎn)、深遠(yuǎn)、平遠(yuǎn)。以從上到下的順序來看《秋林人醉圖》,首先可見高聳威嚴(yán)的山,然后慢慢往下看,逐漸看到近處的山林、小路、游人,可以說是一個(gè)由遠(yuǎn)及近的空間審視過程。與之相比,《冬獵》的畫面布局是由近及遠(yuǎn)的順序,先看到成群結(jié)隊(duì)的獵人與交錯(cuò)的近木,而后層層倒退,逐漸看到山下的小城鎮(zhèn),再及至遠(yuǎn)處的雪山,似乎在畫布上鑿出一個(gè)向內(nèi)延伸的錐形空間。這大致體現(xiàn)了中西方繪畫觀看方式的差異。
這種迥然不同的空間意識,在梅因德爾特·霍貝瑪《林蔭道》與范寬《溪山行旅圖》(圖2)的對比中更是明了。《林蔭道》中,路邊整齊的樹木無形中形成了幾條視覺引導(dǎo)線,直白地將觀者的視線從四周引至中心,也從近處向遠(yuǎn)處延伸。《溪山行旅圖》中壯闊的遠(yuǎn)山氣勢逼人,而后觀者才會注意到山下的樹林與奇石。
自然、籠統(tǒng)地將二者以遠(yuǎn)近之序區(qū)分不盡周全。中國畫中觀者的視線隨氣韻節(jié)奏游走,并不一定由最遠(yuǎn)及至最近,西畫中也有獨(dú)特的方法控制畫面中的視覺中心點(diǎn),且常常出現(xiàn)在畫面空間的中部。因此這里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中國畫的由遠(yuǎn)及近與西畫的由近及遠(yuǎn)是針對畫面中空間的整體架構(gòu)而言,而非死板的觀看順序,這個(gè)區(qū)分脫胎于中西方繪畫架構(gòu)其畫面中空間方式的根本不同。這自然源于中西方的文化差異所導(dǎo)致的空間意識的反差,因此要想探明個(gè)中緣由,還是要從中西方的文化根源談起,一是中西方藝術(shù)形式始源脫胎之異,二是中西方文化中的世界觀、思想基礎(chǔ)之別,二者可以將其因緣揭示一二。
二、形式淵源
點(diǎn)、線、面、體之交織便為形式。不同的藝術(shù)形式先是用不同的方式將對象與觀者隔開,使其不再是對象本身自然的狀態(tài),然后將對象重新組織起來——以藝術(shù)的形式。這兩個(gè)步驟賦予藝術(shù)不同于對象本身的別樣生命力,流于表面的形式組織使得對象神形俱失,與本身的間隔變得更大,而好的形式組織令藝術(shù)載體中的形式能夠發(fā)掘?qū)ο蟾顚哟蔚谋举|(zhì)——那個(gè)關(guān)乎美的核心,能夠表達(dá)超乎自然形象本身的精神,使其發(fā)揮更勝本來的生命力。好的藝術(shù)形式組織能夠讓人從中窺得不限于一個(gè)人、一個(gè)時(shí)代與環(huán)境的獨(dú)特生命力,形式的組成方式也在于不同文化環(huán)境的人的不同感知力,空間意識就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言至于此,從藝術(shù)形式的區(qū)別就能看出不同文化、環(huán)境、時(shí)代的不同特點(diǎn),而最為始源的藝術(shù)形式就代表了一個(gè)文明的整體特點(diǎn),也能夠從中預(yù)見其一部分的發(fā)展方向,因此可從中西方最早且最重要的藝術(shù)形式入手開展研究。
中國畫的空間構(gòu)造基于書法藝術(shù),是類似于音樂的有節(jié)奏美感與線條美感的藝術(shù)。書法在于用筆,用筆得法,線條之中便蘊(yùn)藏著空間。這導(dǎo)致中國畫的重點(diǎn)不在于具體物象的描繪,而是傾向于借由抽象的筆墨來表達(dá)心境與意境,其重點(diǎn)在于創(chuàng)造意象,落眼于筆法節(jié)奏,所謂“氣韻生動”就是用筆的目標(biāo)與結(jié)果。西畫的空間構(gòu)造始于古希臘雕塑與建筑,即始于“數(shù)量的比例”,強(qiáng)調(diào)和諧美,以和諧、秩序、比例、平衡為標(biāo)準(zhǔn),以幾何為空間,結(jié)果就是西畫空間往往結(jié)實(shí),似可入、可觸。相比西畫空間的實(shí)景,中國畫則注重意境,似神可游。人步入一境往往是一步踏入而后步步深入,神游意境則無拘無束,放到繪畫上的結(jié)果便是西畫中由近及遠(yuǎn)的科學(xué)透視與中國畫中氣韻當(dāng)前,而后再有細(xì)細(xì)景致逐一出現(xiàn)。因此,中國畫的核心不在于對真實(shí)物象的刻畫,而是對意象的捕捉。雖然寫實(shí)也是中國畫不可或缺的一個(gè)重要部分(比如花鳥畫之精巧),但畫面最終還是著眼于整個(gè)畫面的節(jié)奏與畫面本身的生命力,而不是單一物體的細(xì)微刻畫。
從西畫傳統(tǒng)中對于人體解剖與透視學(xué)的研究之精微細(xì)致,古希臘人對人體具體的、相對于宇宙自然而言的微觀對象的癡迷等中就能看出端倪,神性在與人不斷接近時(shí)被消解,神秘性幾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能量無窮的人類與作為理想的美。古希臘雕塑無限縮近了人與神之間的差距,于神見人性,又于人見神性,離不開的正是對人體的細(xì)致剖析,龐貝古城的壁畫也與雕塑如出一轍,好似畫面中的雕塑。
具體到畫面中的線條,西畫之線條隱于立體的面當(dāng)中,被擠到輪廓的線條也是為體積與光影服務(wù);中國畫之線條則更為獨(dú)立,以皴擦之法自成一體,除形體外,更多的是為畫面整體意境服務(wù)。從中得出,西畫求“真”,中國畫重“意”,這就從純粹的形式討論中延伸到了畫面的意義與思想部分。
三、思想基礎(chǔ)
藝術(shù)形式無疑是受到思想意識形態(tài)左右的,當(dāng)一個(gè)人思考如何組織形式時(shí),會從自身的生活、情緒與思想中汲取靈感,而這些要素都會受到時(shí)代、環(huán)境、文化的深遠(yuǎn)影響,甚至是本人難以察覺的某些本質(zhì)上的特點(diǎn)。從思想基礎(chǔ)來說,中國畫的思想基礎(chǔ)是老莊思想,西畫的思想基礎(chǔ)在于古希臘哲學(xué)家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如此,將兩種文明歸結(jié)于具體的幾人似乎顯得狹隘了些,但不妨說他們極具代表性。“偉大的作家必是哲學(xué)家”,加繆的這句話可以用來解釋從藝術(shù)到哲學(xué)這一層躍進(jìn)的合理性。同時(shí),他還說:“表達(dá)始于思想結(jié)束之時(shí)。兩眼空空的少年充斥寺廟和博物館,藝術(shù)家把他們的哲學(xué)表現(xiàn)為舉止。”藝術(shù)家的作品中一定會有意無意地透露出個(gè)人的哲學(xué)思想,而這思想亦會受到民族與環(huán)境整體思想狀態(tài)的影響。
總體上來說,中國的古人從不追求自我的過分?jǐn)U張,從不把人看作高于一切的存在,不是絕對統(tǒng)治萬物與奴役萬物的主宰,而是在自然界中處于一個(gè)中間位置,不屈從于自然,在觀察與表現(xiàn)自然的同時(shí)帶著自己的視角,但也不妄圖征服自然,以天地為師,態(tài)度謙遜。《道德經(jīng)》中有這樣一句話:“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這句話可以十分貼切地闡釋中國畫的架構(gòu)。打個(gè)比方,有了四堵墻和一個(gè)頂,這便是“有”,它們提供了一個(gè)條件,但并無用處。在墻上開一個(gè)洞,讓它成為門、窗,這便是“無”。有了“無”的存在,“有”才能發(fā)揮它的價(jià)值,以此被利用起來。放在中國畫中,“無”也許就可以看作“留白”。當(dāng)然,這個(gè)解釋很淺顯,這句話還有無窮的韻味,還可以從很多角度來看,但在這里,我們可以把它看作中國畫的美學(xué)基礎(chǔ)。中國書法的線條不完全模仿自然對象的形,但也并不完全抽象,它依舊是有形象可依的,這也構(gòu)成了中國畫空間觀念的基礎(chǔ)。
而在西方,哲學(xué)家基于數(shù)學(xué)思考問題,盡可能地模仿自然對象,其思考內(nèi)容是如何將自然化為可掌握的某些準(zhǔn)則。盡管柏拉圖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世界模仿理念世界,藝術(shù)模仿現(xiàn)實(shí)世界,而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藝術(shù)模仿的現(xiàn)實(shí)世界具有無可懷疑的真實(shí)性,但總的來說他們都認(rèn)定藝術(shù)就是對自然的模仿。這就形成了西方繪畫的美學(xué)基礎(chǔ),在對現(xiàn)實(shí)的模仿中他們愈發(fā)嚴(yán)謹(jǐn),恨不得每一根線條都是“正確的”,即接近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真實(shí),以此構(gòu)成了西方繪畫的空間觀念的基礎(chǔ)。
由此便可見中西方思想之截然不同,中國傳統(tǒng)思想可說“不滯于物,不為物役”,西方思想則思考如何理性、全面地解剖對象。何以見得?以中西方文學(xué)中的“守財(cái)奴”形象為例,如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臺與吳敬梓筆下的嚴(yán)監(jiān)生,雖然其共通性在于揭示人性中自私的一面而帶來警示作用,但相比之下,葛朗臺的吝嗇之舉顯得具體而生動、深刻而全面,嚴(yán)監(jiān)生的生活狀態(tài)則更有脫離現(xiàn)實(shí)的荒誕感。其中體現(xiàn)出中西方人世界觀的區(qū)別,或者說對待“物”的態(tài)度的區(qū)別。
就如《易經(jīng)》中所說:“無往不復(fù),天地際也。”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并不是只有“前進(jìn)”,“返回”同樣重要,甚至“前進(jìn)”只是途徑,“返回”才是目的。《孟子》當(dāng)中有:“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在“目及無窮”后,“反身而誠”才能無愧于“萬物皆備于我”。因此,繪畫時(shí),中國古人觀察自然對象是在循環(huán)中觀察,大體上是先認(rèn)識自然對象,而后認(rèn)識或總結(jié)繪畫程式,再與自然對象相結(jié)合,以此形成作品及個(gè)人風(fēng)格。誠然,西方人也重視自我,如蘇格拉底曾說,未經(jīng)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為何還是有這么大的差距呢?西方人的宇宙觀,簡單來說是“人”與“物”、“心”與“境”的對立相視,實(shí)際上就是“主客觀的對立”。西方人將他們所看到的“具體”融入和諧整齊的形式當(dāng)中,這才是他們的理想。放到繪畫中來說,西方人大多是在“看見的對象是什么樣,它在畫布上就應(yīng)是它本來的樣子”這樣一個(gè)框架下進(jìn)行傳統(tǒng)繪畫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
由此,對于思想的討論又回到了形式上,不如說二者本就是相互糾纏、共同發(fā)展的。中西方繪畫的空間意識就是如此被不間斷地滋養(yǎng),在不同的道路上愈走愈遠(yuǎn),但通向的是人類文明對“美”的追求這一不變的終點(diǎn)。
四、結(jié)語
中西藝術(shù)皆為人類文化之瑰寶,各自體現(xiàn)出不同民族的獨(dú)特文化氛圍。中國古代“往復(fù)”之思想借由以書法為始源基礎(chǔ)的中國畫彰顯,西方的“理性”之光也以雕塑與建筑為基底綻放。不論何種藝術(shù),其都是當(dāng)下一個(gè)時(shí)代、一類文化的縮影,展現(xiàn)獨(dú)屬于這個(gè)文明、這個(gè)時(shí)代的精神面貌。
參考文獻(xiàn):
[1]宗白華.美學(xué)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朱光潛.西方美學(xué)史[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3.
[3]李澤厚.美的歷程[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
[4]徐學(xué)凡.中國傳統(tǒng)繪畫空間意識的特性[J].文藝爭鳴,2011(4):40-42.
[5]孫文娟.傳統(tǒng)中西繪畫空間意識的差異性論析[J].明日風(fēng)尚,2019(9):34.
[6]張榮浩.中西傳統(tǒng)繪畫空間意識淺談[J].大眾文藝,2011(21):56-57.
作者簡介:
劉沛松,碩士,河北美術(shù)學(xué)院造型藝術(shù)學(xué)院專任教師。研究方向:油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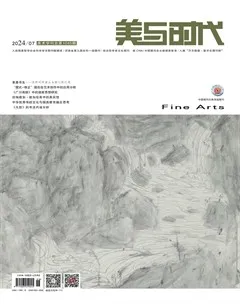 美與時(shí)代·美術(shù)學(xué)刊2024年7期
美與時(shí)代·美術(shù)學(xué)刊2024年7期
- 美與時(shí)代·美術(shù)學(xué)刊的其它文章
- 顧仕、鐘夏怡、張之彥、徐智彥作品
- 朱正基作品
- 楊菁菁作品
- 朱謙、盧慧作品
- 廖雅娟、梁瀾千、陳茵如、陸小康作品
- 尤璐瑤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