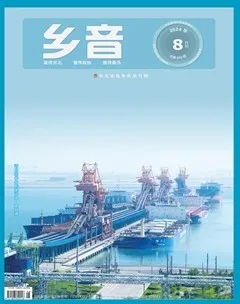文史集粹(4則)
【 巴金以幽默化解尷尬 】
現代著名作家巴金(1904-2005)的幽默是一種不同尋常的幽默,也是能夠有效化解尷尬局面的幽默。
有一次,一名記者去巴金家里采訪,請巴金談談童年的生活。
巴金的記憶力好得驚人,將兒時生活的細枝末節講得繪聲繪色。記者聽得入迷,要巴金講講當年向祖父請安時穿的什么衣服,質地和樣式如何,問得非常繁瑣。面對記者的追問,巴金一臉和煦的笑容,他對記者說:“可惜,我那時不知你要問我這些,否則我就記下了……”話畢,他自己也笑出了聲。這樣的說法在記者的意料之外,從而也終止了記者的發問,化解了對話進入僵局的尷尬。
冰心曾送給巴金一張墨寶,她在一張狹長的宣紙上寫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冰心的字寫得俊秀飄逸,她借用魯迅寫給瞿秋白的對聯,以表明她與巴金之間的純真情誼。一次,一名記者從巴金家人手中接過這張墨寶,欣賞了半天,然后詢問巴金,笑嘻嘻地說:“巴老,您能不能借給我復印一下?”記者這一唐突的要求讓周圍的人都愣住了,場面十分尷尬。沒想到,巴金不慌不忙笑嘻嘻地答道:“我能不能不借給你復印一下呢?”多么機智幽默!一時間,尷尬化解了,大家都笑了,誰都不難堪!
(摘自《新一代》武俊浩/文)
【 張衡不自欺 】
東漢科學家、文學家張衡(78—139)自小聰明好學,很早就會做文章,后來他的興趣逐漸轉向了天文地理。在讀書人一心想著做官的年代里,其身為太守的祖父張堪卻顯得與常人不同,他鼓勵張衡進行科學探索。
張衡16歲時想出門游歷,目的地是秦漢的發源地陜西。張堪聽了非常支持,決定把自己的一匹寶馬送給張衡。張衡對祖父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此次出門不要勞駕車馬,要靠自己雙腳走出來,或許這樣才能得到對自己有用的見識。”見自己的孫子有這樣的勇氣,張堪贊嘆不已,囑咐張衡一定要不虛此行。
半個多月后的一天,張衡走在去華山的路上。半道上一輛馬車停在跟前,張衡定睛一看,下車的是自己的好友陳墨。原來陳墨是去華山游玩,他邀請張衡上車同行。張衡說明了原委,表示不能破壞自己定的規矩,遂拒絕了陳墨的好意。
陳墨說:“此地只有你我,破一次例也無人知曉。”張衡回答說:“如果覺得無人知曉就此破例,就是在欺騙自己。人可以欺騙得了別人,但永遠欺騙不了自己。”聽了張衡的話,陳墨用欽佩的目光看了看張衡,然后默然地駕車離開了。
之后,張衡徒步走遍了陜西各地,考察了壯麗的山河和宏偉的秦漢遺址,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在科學研究上,張衡一直保持著親力親為的嚴謹作風,公元132年,他發明了候風地動儀,開了世界地震研究的先河。
(摘自《現代家庭報》俞繼東/文)
【 “宰”和“相”曾是兩個官職 】
宰相是中國古代君王之下的最高行政長官的通稱,但起初,“宰”和“相”是兩個不同的官職。
商周時期,“宰”是貴族的“管家”,負責監督奴隸、管理牲畜等家務事,叫“家宰”;天子的“管家”叫“太宰”,即幫忙管理朝廷。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都有了“相”的職位,“相”有“副手、輔佐”的含義,其官職是輔助國政。秦統一六國后,“宰相”作為一種官職被確定下來。
(摘自《百科知識》曉軍/文)
【 [咬文嚼字]數詞“兩”“二”的用法不同 】
讀書刊報,常見數詞“兩”“二”混用的情況,如“前邊來了二個人”“我到書店買了二本書”……這是不對的,應為“兩個人”“兩本書”。
201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釋義,“兩”和“二”用法不同。讀數目字只用“二”不用“兩”,如“一、二、三、四”;小數和分數只用“二”不用“兩”,如“零點二(0.2)”“三分之二”;序數也只用“二”不用“兩”,如“第二”“二哥”。新的度量衡單位前一般用“兩”,如“兩噸水泥”“走了兩公里”。一般情況下,量詞前用“兩”,如上例中所示,如“兩個人”“兩本書”“兩匹馬”“兩扇門”;“千”“萬”“億”前,“兩”和“二”一般都可用。
(史 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