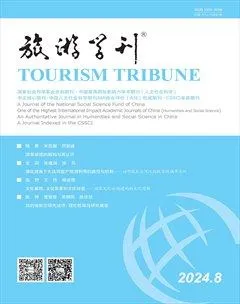“我要去巴黎旅行!”:旅游作為“意志”與倫理研究的可能
盡管倫理學的根本問題是“人應當怎樣生活”,但一般倫理學的興趣集中在道德行動及其與幸福的關系上,而對其他實踐理性興趣寥寥。胡塞爾指出了倫理與道德之間的分野,“與實踐道德理性的某些原則有關的道德只是倫理的一個部分”2,“如果我猶豫是否應該在晚上聽膚淺的滑稽劇,還是欣賞貝多芬莊嚴的《英雄交響曲》時,我可能會理性地決定后者,但這里不存在道德意義上的良心問題”3。胡塞爾意欲尋找實踐理性的一般性原則,而非有限意義上的道德感。倫理問題在其根源處與意志相關,倫理生活是由“意志引導和塑造的生活”,道德行動只是其中之一。在深入意志領域問題時,胡塞爾多次使用去巴黎旅行的論述4,澄清交織在一起的諸多概念。無論這種選擇是否帶有巧合或者說某種程度上的隨意性,毫無疑問的是,胡塞爾將“我要去巴黎旅行!”當作意志行為的典型實踐樣式。那么,我們能否從“意志”打開“旅游”,并考察旅游與倫理生活的關系?
一、“我要去巴黎旅行!”:從意志到價值
首先要確定的是旅游作為“意志”研究的內容和意義。現象學將“意志”問題看作是意識分析從理論意向性到實踐意向性的過渡,意志行為的分析是實踐哲學的邏輯發端。意志作為非客體化行為,是由價值引發的。問題在于,“我要去巴黎旅行!”具有何種價值?
在一般的旅游研究中,推-拉理論、娛樂、放松、教育,甚至一種體驗內容上的存在主義原真性,都被冠以旅游價值一說。此類“價值”在現象學視域中,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心理物理因果性,意味著“人格自我的自身遺忘”1。胡塞爾在《倫理學和價值學說(1908—1914年講稿)》中對意志、情感進行了考察,將非客體化行為提高到原初地位,認為意志行為自身可以作為目的論的意向性。因此,旅游中存在的價值并非只有經驗的時空因果性的“動機”,還具有先驗的精神因果性的“動機引發”。先驗的“我要去巴黎旅行!”的價值,并非在于我去巴黎后,會看到了、體驗到了、得到了什么益處或效果,而是在“我要去巴黎旅行!”這一意志的動機引發及其實踐行為中具有當下自我的自身超越的生命價值。
具體而言,“我要去巴黎旅行!”的意志與“我想去巴黎旅行”的愿望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意志明確要求一種實踐可能性和實踐行為,而愿望則是以“可能實現”和“不可實現”兩種狀態存在。同時,意志也并非用于滿足欲望。開啟一段旅行意志既不會消除對旅行的欲望,我在旅途過程中還有可能生成對下一次旅行的欲望。在旅行的意志中,欲望持續存在于意識的底層。意志的主要特征是有創造性地(而非已經設定的)指向未來,“在此要求一種被充實的意志過程”2,而不是愿望的實現和欲望的滿足。在此意義上,一種純粹的“旅游體驗”,如扶手椅上的旅行或者是“臥游”或者是虛擬旅游,絕不可能替代實踐意義上的旅行。意志的“創造性”解構了傳統的因果關系的行動理論。
依據傳統的行動理論,我想要去旅行是因為我確信這一行為會讓我獲得諸多豐富體驗,當我獲得了這些體驗時,我會感到滿意,如果我沒有獲得,我則會感到失望。期望差異理論即是此傳統行動理論的發展。但是,作為一種意志,旅行從不讓人失望。因為我去巴黎旅行的行動的價值,在于意志的充實和創造性的未來,而不是預期的體驗內容的充實。意志的行動理論指明,個體在行動過程中,沒有一個確定的可以被實現的目標信念,而是在實踐過程中的自我“更新”:非現成對象的創造和未來的作為本己的自我生成。這即是旅行作為意志現象的價值所在。
旅游作為意志行為的分析打開了旅游世界中新的指引關系。首先是旅游作為實踐行為的現象學分析。意志作為實踐意向性行為,它本身是缺乏獨立質料的非客體化行為,因此,只有實踐意向的相關項。以旅游來看,這個實踐意向的相關項就是“巴黎”這個“旅游目的地”。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理論,實際上是旅游目的地作為實踐意向的相關項這一性質的理論化,“旅游目的地”不是一個實體的物質,而是隨著旅游實踐產生、發展和消亡的實踐意向的相關項3。借由此種性質,更為廣泛的異鄉世界的旅游地化過程及其意義,也變得可以理解4。其次是意志行為內含的“對意志-實踐的決定”,意志決定給予了旅游實踐本身在生命意義上先驗還原的含義,它以意志“將人引向一個神圣的、賦予我們生活以意義和典范的起源之域中”5,旅游蘊含的倫理“懸隔”和“還原”在此可得到充分的闡釋。再次是旅游活動在自我引導、自我塑造和塑造世界上所具有的創造性的生命價值,更進一步的研究將揭示被構造的自我的方向(旅游目的地-陌異的世界、決定-理想的自我)。這3個方面構成了旅游實踐的現象學研究基本方向,而旅游作為意志的現象學分析,也開啟了旅游實踐研究的倫理學視域。
二、“實踐應當!”:從價值到倫理
我所意愿的即是我所應當的,我們要追問的是,旅行何須“應當”,又“應當”如何?這一問題引導旅游研究通往倫理學。
胡塞爾在一戰后對現象學倫理學的探討,倡導我們要面向倫理學最初要求,即“指示‘我’現在‘應當’如何在這個社會的和歷史的聯系中存在和生活”1。這一初衷要求倫理學回到對一般性的理性實踐原則的探尋。因此,盡管現象學倫理學主要關注的是道德意識,但胡塞爾的“改造倫理學”所面向的“受純粹理性規范支配的生活”2是指所有領域的實踐,“在普遍的以及最寬泛的意義上,我們把每一種與倫理目標理念之定言要求相符的自我規范的生活稱作倫理的生活”3。因此,對非道德行動的實踐所構成生活方式的選擇提供價值辯護和規范指導,同樣歸屬于追求好的生活的技藝學(kunstlehre)的倫理學4。在此意義上,現代旅游實踐代表著一種意愿和行動:我應該去旅游,因為它意味著一種幸福的生活,是我所意愿的“好的生活”56。
“我應當去旅行!”揭示了一個無涉道德領域的實踐應當和倫理生活。人理解著周遭世界,并發出旅行的意志,在旅行中確立自身的存在意義,理性地塑造著自己與周圍世界的關系。旅游實踐中被構造的自我,不以傳統宗教和神圣理想為目標,而是與幸福直接相關的實踐應當。旅行的倫理辯護和引導,既繞過了理智道德論者的神學化傾向,“將目光更多朝向彼岸,朝向超越的——形而上學的東西,朝向作為理念之場所的上帝”,也繞開了情感道德論者在以世俗世界為家園時掉入的相對主義陷阱7。這種倫理理想不再和宗教的拯救恢復合為一體8。
三、“旅行”:作為一種倫理生活
當代人的“生活世界”——先于其存在并作為所有實踐的基礎——較之工業革命之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去旅行的意志為特征的休閑生活無疑是最典型的代表。休閑與倫理生活的關系是有歷史和文化起源的,亞里士多德就曾指出,“閑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9,而儒家的“曾點之樂”也是以一種休閑生活狀態呈現“堯舜氣象”。而把旅游及休閑納入倫理生活中考察,是當代倫理研究發展的需要。因為在當代生活中,人格的一個本質特點便是對自我生活的實踐決斷,便是“我要去巴黎旅行!”。
旅游從反日常到日常實踐的發展中,逐漸凸顯出一種以自身為目的的意志特征。它不再以自然態度從盲目生活中尋找旅行的目的,而朝向了基于日常生活懸隔和還原的倫理生活。在此意義上,旅游實踐分有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沉思生活的基本特征。這種“意愿的倫理生活”,既是當代人自主選擇的塑造我的生命整體的方式,指向的是倫理的真,又是從當代懷疑主義、虛無主義中產生的“啞的”實踐理性的生活方式。胡塞爾對倫理學的“改造”,要求理性指引倫理生活,旨在回歸一種哲學根本興趣,即對生活的興趣以及“人成功地駕馭他的整個生活、他的全部此在”10的興趣。這種轉變、回歸或者改造,要求重新思考當代休閑與倫理生活的關系,通過闡釋這類休閑實踐的先天價值和描述其“應當”的生命樣式,為個體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提供指引。旅游研究可以在這種關系中開辟一條新的研究路徑。
致謝:感謝倪梁康老師允許我閱讀其尚未出版的《倫理學和價值學說(1908—1914年講稿)》譯稿。
(作者系該院助理研究員;收稿日期:2024-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