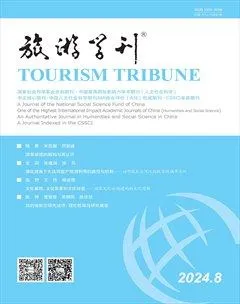旅游作為地緣政治研究的方法論
長期以來,旅游多被感知和定義為一種經濟產業、休閑活動和消費實踐。這種窄化的理解使得旅游研究多關注目的地、客源市場和游客個體,弱化了旅游在日常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中廣泛的存在及其產生的顯著影響。新興的旅游地緣政治研究已經證明,旅游和地緣政治是親密交織、相互組成和互相影響的4。筆者認為,要理解旅游與國家政治之間的關聯以及旅游的地緣政治嵌入性,需要超越上述的產業化和個體中心主義的旅游理解。將旅游視為全球最大的移動性系統和聚集體(assemblage),為拓展理解旅游的地緣政治能動性和旅游作為地緣政治研究的方法論提供了思路和可能。
旅游是一種移動性組織和系統,其將存在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地方、機構和人群組織聯系起來,增強“此地”和“彼地”之間的交互和擾動,從而使得不同地方之間的元素和日常生活彼此構成、相互塑造,并不斷共同進化5。地緣政治力量、國家控制正是通過旅游流動性及其生成的交織關系得以被引導、加強或挑戰。因此,正如Becklake和Wynne-Hughes6所宣稱的那樣,旅游一旦被發明和啟動,就具有轉變和形塑國家的能力。旅游同時也是一個由物質、實踐、話語、表征和非人類元素構成和支撐運作的異質、復雜聚集體,包含旅游機構、目的地、交通基礎設施、旅行證件、國家政策等元素7。這些聚集體元素深嵌于過去和現在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旅游的異質特征使得其嵌入和貫穿多尺度、多層級和多主體的政治過程,讓旅游既是國家戰略、經濟產業,也是人們日常實踐的一部分,并與全球化、國家轉型、地方發展、個體實踐和主體化等過程耦合。因此,旅游不僅可以成為個體對世界的認知媒介,還有成為認知當代政治經濟現象框架的潛力1。
基于對旅游的拓展理解,本文將首先闡釋旅游和地緣政治之間復雜的糾纏,再通過具體的案例說明旅游(研究)如何可以成為地緣政治研究的方法。
一、旅游與地緣政治的內生緊密性
在動蕩的全球政治和經濟安全背景下,地緣政治術語近年來被學者、政治家、媒體和公眾頻繁使用,來指代與領土邊界沖突、國際政治格局、大國擴張邏輯和霸權追求等有關的空間政治現象,但其使用含義各異。在政治地理學中,地緣政治常指(國家)行為者控制領土和全球空間的意愿、嘗試和斗爭,以及地理特征和地理知識生產對政治進程的影響23。旅游和地緣政治常被視為是互斥的,因其“看似沖突的研究話題、方法論和理論基礎”4。例如旅游研究很少關注暴力、入侵或政治干預,而這些恰恰是地緣政治研究的核心主題。此外,旅游研究受經濟話語、應用科學和實證主義范式主導,而地緣政治研究則受后結構主義、后殖民和批判理論的顯著影響5。然而,由于旅游與地緣政治都與國際交換有關,兩者在哲學基礎上是存在共性的,旅游與多尺度和多維度政治展演的交織也使得兩者有著內生聯系。
首先,旅游是當代影響最深遠的地緣政治實踐之一6。旅游(業)的存在和發展直接受國家間外交關系、領土治理、邊境秩序和人口管制等正式地緣政治決策(formal and practical geopolitics)的影響。地緣政治動蕩和國家間關系的破裂,尤其是毀滅性的地緣政治事件(如戰爭的爆發和恐怖主義襲擊)和突然的政治決策(如新冠疫情期間某些國家緊急的邊界關閉政策),會直接暫停或終止旅游活動。其次,旅游也嵌入國家關系構建中,比如許多國家出臺“旅游外交”政策7,試圖將旅游用作改善國家間關系、貿易順逆差和增強民間互動的舉措。日常地緣政治(everyday geopolitics),即日常的外交、主權、領土性、民族和國家構建等政治戰略,也總通過旅游來實踐和實現8。比如,當代民族國家結構通過公民身份自動賦予了不同群體差異化的旅游移動性,生產了全球南北之間不平等、不正義的移動性等級(mobility injustice)9。更微觀一點,國家間政治關系影響游客的目的地想象、旅游決策、體驗和行為。游客的目的地感知、情感體驗和邂逅總是被循環在國家敘事、流行文化和旅游產業中的地緣政治話語所構建。反過來,旅游又可能反作用于全球、地方和個體具身尺度的政治過程,成為“推動國家倡議和政治建設,或引發政治抵抗的關鍵機制和場所”10。
旅游是全球最大的產業,與當代諸多宏大和嚴峻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相關聯,例如移民、國家競爭、氣候變化、流行疾病、環境危機等,同時嵌入(后)殖民主義、新自由主義、安全化和軍事化等政治過程,并反過來形塑這些進程。旅游的復雜多維性讓其常與其他政治和非政治元素結合組成地緣政治聚集體(geopolitical assemblage),從而共同生產和固化當代地緣政治話語和霸權關系⑩。旅游與地緣政治之間的親密聯系,讓從旅游角度觀察和分析地緣政治博弈成為可能。本文將通過南海旅游的具體案例來展開旅游作為地緣政治方法論的觀點。
二、旅游作為南海地緣政治研究的方法論
南海的多邊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域內日益的邊界化和軍事化,以及中美在此的地緣政治博弈,讓南海問題成為全球地緣政治討論的熱點,并被認為是印太地區最危險的潛在沖突點。多個南海周邊國家為了占領島礁和控制周圍海域,海洋劃界、島礁建設、軍事管控和國際法等高政治手段被利用來搶占南海控制權。與此同時,一系列低政治的民事手段也被用于增強民事存在和領土主權,旅游就是其中之一。這種旅游通常登陸爭議的島嶼和海域,是一種領域化的技術。馬來西亞最早于1991年在其占據的彈丸礁上開展此類領域化旅游,其旅游市場面向國內外游客開放。2004年,越南通過軍艦搭乘游客在其侵占的南沙島礁開展小規模觀光旅游。近年來,其旅游活動逐漸常態化和商業化,對國內外游客開放,但禁止中國籍游客和越南籍華人參加。我國在馬來西亞和越南旅游開發前期提出了強烈抗議,為了維護主權,于2009年底批準海南開通西沙郵輪旅游,2013年正式開始運營,僅對大陸居民開放。
南海旅游是旅游地緣政治研究的一個典型案例,集中體現了日常旅游實踐如何與激烈的國家間領土爭奪和捍衛聯系。旅游的啟動、發展和演化都受到區域地緣政治局勢的驅動和影響;旅游啟動后,通過其聚集體元素廣泛嵌入南海的軍民共用建設、島嶼景觀改造、領土性和管轄權展演等多個維度政治經濟過程中,借此旅游發揮自身的地緣政治能動性。除了南海旅游研究本身獨特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外,筆者認為,南海旅游現象的研究還可以觸碰到其他敏感的高政治問題,進而拓展和深化對此區域安全、沖突、發展與合作進程的認識,讓旅游研究為國家平衡在南海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利益,推進環南海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實際依據。
首先,旅游(研究)解放了研究者南海可進入性問題。南海爭端的高敏感性和爭議領土的不可接近性,導致南海研究長期以來一直以精英主義觀點和國家中心主義視角的法律、安全和政策討論為主。這些探討固然意義重大,但其忽視了國家領土化戰略展開過程中重要的社會、經濟和地理動態,次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的領土化參與,以及民事實踐在國家領域化和邊界化過程中的角色1。盡管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南海旅游向公眾開放了部分地區,也使得研究人員得以進入南海,接觸不同的地緣政治行動者,以進一步了解和直接觀察相關的領土地緣政治動態。田野過程中,研究者既可以游客身份參與旅程收獲“局內人”的切身體驗,也可以“局外人”身份搜集信息,保持觀察距離。這種雙重身份的互動有助于研究者從多個角度聯系和反思南海地緣政治動態。
其次,旅游(研究)補充和豐富了南海地緣政治研究的數據源來源。由于歷史事件和記錄材料的缺乏,南海問題研究的信息和數據供給主要集中在當代新聞報告和外交宣言上,導致對南海地緣政治的歷史性動態刻畫不足2。南海周邊國家歷史上圍繞此區域的旅游規劃、政策和治理材料,爭議方對旅游的反應,以及游客的體驗等可以作為歷史數據的補充,增進我們對南海外交政策和雙邊關系演變的過程性理解。更廣泛來講,旅游的經濟和日常屬性賦予了其非政治、低敏感的外界印象,使其能相對容易地觸碰和窺探高地緣政治過程、敏感事件和特殊行動者,從而有潛力為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兩個領域在政治行動者實踐數據獲取困難上提供一個新的突破口。
最后,旅游(研究)可以提供多個視角去窺探南海多尺度的地緣政治復雜性。可以通過旅游與多維社會、經濟關系的糾葛和多主體的交互去觀察其他政治現象,比如南海旅游的機制和演化研究與國家尺度的的地緣政治重組過程存在直接和間接的關系,通過旅游透視島礁上的行政區劃調整、民事領域化(漁民、僧侶、旅游接待者等)實踐和海洋基礎設施建設情況等。現有研究基本提前假定了南海周邊國家民眾在南海問題上擁有很高的民族主義,具體一手的、細微的和綜合性的海洋領土意識和認同調查缺乏,這導致對地緣政治權力在微觀和親密尺度上的再生產過程和效果缺乏了解。通過在旅游情境下對游客的旅游體驗調研,從而以輕松自在的方式探討海洋領土相關的敏感問題,獲得民眾自下而上更真實和多樣的關于南海地緣政治問題的回答3。
本文探討了旅游成為多尺度地緣政治研究的方法論的依據和可行性。鑒于旅游與地緣政治之間的多重親密聯系,筆者認為,旅游的多尺度地緣政治嵌入性提供了眾多的切入口去超越國家中心主義和宏大敘事,去系統透射、觸碰和反思國家間政治關系、地緣政治話語與實踐在日常生活中的循環,高政治與低政治間的相互滲透和重構,以及去觀察多主體間的權力和地緣經濟交互和沖突。本文從進入性、數據源和分析視角3個維度列舉了旅游研究可以如何服務于南海問題研究。未來研究還可以繼續深化探究旅游在輔助認識政治世界、理解地緣政治和地緣政治動態方面的潛力,比如通過邊境旅游研究透視特殊的領土制度安排,創新區域合作和整合研究,還可以通過對主-客關系的觀察,了解普通民眾對彼此國家的地緣政治情感和地理想象。
(第一作者系該院助理研究員,第二作者系該院教授、通訊作者;收稿日期:2024-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