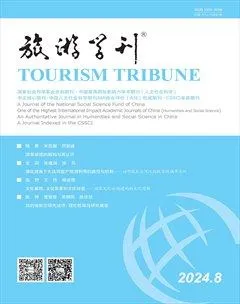“阿者科計劃”旅游減貧方法的經驗與反思
當我們開始探討旅游作為一種減貧方法時,背后隱藏一種工具理性思維,隨即引導出一個關鍵問題:旅游作為一種方法,如何能夠有效促進減貧事業?要回應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回應旅游減貧這種方法如何不同于其他減貧方法,如何在實踐策略層面提供一些案例經驗參考。基于參與云南“阿者科計劃”5年駐村建減貧項目經歷,筆者溯源了該村的旅游減貧方法施行歷程,有以下感悟。
一、旅游主客互動可以作為理解貧困和消解偏見的認識方法
旅游的高度流動性跨越了城鄉社會經濟結構的時空隔斷,游客從發達城市向欠發達鄉村流動,并走入當地社區生活世界,獲得了解貧困人口的機會5。游客在身臨其境的旅游實踐中建立自身日常世界與地方貧困世界的強烈對比,進而建構起對社會發展的新認知和省思。由此,旅游可以作為認識社會發展不充分、不均衡、不平等的認識方法。筆者在阿者科的減貧實踐發現,旅游的減貧效應不在于誘發游客對貧困人口的同情或憐憫,而在于增進理解當地貧困生活世界,并消解社會偏見,主客互動式旅游體驗活動成為關鍵的技術路徑。游客具身參與哈尼家訪、家宴、摘菜等主客互動活動,如同多棱鏡折射出一體多面,讓游客得以從當地地理交通、人口結構、文化、教育、社會觀念等多維度更全面地理解貧困人口的生存境況,更加理解了地方貧困生活世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游客充分參與體驗可以修正原有的社會偏見,即當地人貧困并非因為懶惰與不上進,而是面臨交通可達性差、土地肥力不足、家庭與社區需要人照顧、地區教育資源匱乏等各種發展限制條件。通過主客互動,游客更多表現出對當地人千百年來墾山造田努力改變生存條件的欽佩,并更加理解和尊重當地人傳統生計與生活方式選擇,改變了根據外部物欲價值文化與標準對當地人生存狀態作出的主觀價值判斷。
二、替代性旅游產品可以作為貧困人口生存環境與資源的保護方法
在盛行標準化生產的現代性與全球化浪潮中,原真性變得稀缺。貧困人口所貼近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成為原真性旅游吸引物,成為城市居民的“舒適物”1。原真性稀缺決定社區需要保留足夠多原住民,才能保護傳統生產生活方式文化。保護完整的社區產權成為保護貧困人口生存資源環境原真性的關鍵路徑,尤其是土地、房屋等產權要素。然而,現實情況往往是“資本下鄉,農民上樓”2,甚至是農民離土離村。旅游資本下鄉帶來土地、房屋等生產要素的產權非農化和文化商品化,甚至產權被完全置換。旅游減貧造就新自由主義資本擴張和增加城市居民休閑福利,真正的貧困人口卻在租賃中走向邊緣,鄉村社區成為“旅游飛地”或“紳士化”的城市居民第二居所,這有違pro-poor tourism初衷。旅游減貧項目應該追求長期發展效益目標及包括貧困人口在內的公共福利,而非短期經濟投資目標與官員政績,管理者應布局和引導通過旅游開發謀求對貧困社區長期影響和嬗變。
到底旅游減貧方法是否一定要出讓產qadgWtnhFP17P3cZ0Oj62HbLKqbo32VAZKKubLmpfw8=權,資本是否一定需要被引入?或者需要怎樣的資本進入?國際經驗表明,產權保留在社區層面對于社區掌控旅游業發展節奏與方向有著關鍵性作用,基于公共產權發展小企業更能保護貧困人口所依賴的敏感而脆弱的傳統社區文化、資源與環境3,例如薩摩亞、不丹、新西蘭毛利部落等4。“阿者科計劃”在中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情境下檢驗了保留社區產權對于保護貧困人口生存資源與環境的重要意義,為貧困人口長遠發展保留公共發展資源和緩沖空間,并探索出了基于集體社區產權保留開發大眾觀光旅游,并補充開發投資更輕微、對社區環境與文化更友好的替代性旅游開發方式。具體操作實踐上,“阿者科計劃”在發展前期引導村民建立產權出讓限制規則,即規定不允許資本進駐阿者科村,村民房屋不得對外出租。在保留社區整體產權與原真性基礎上,“阿者科計劃”帶領村民活化利用既有傳統資源與工藝,開發織染布、拜訪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等旅游體驗活動。社區居民通過多元路徑參與旅游更能加深自然和文化資源價值認知,進而促進生成對當地環境與資源保護的內生動力。關于旅游減貧與資本引入限制的關系,正如阿馬蒂亞·森認為經濟發展中的“自由”應是辯證、因果、經驗的5,“阿者科計劃”實踐表明,對資本引入的限制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作出制度安排,具體包括管理者仔細甄別貧困社區的資源屬性、細分游客市場需求、社區既有參與能力與資本、產品與設施開發資本缺口等復雜因素,根據發展需要來有條件地引入資本開發旅游。
三、旅游吸引物權制度可以作為重構分配格局的制度方法
旅游經濟增長不等于當地貧困人口實際獲得收益,旅游減貧項目需要密切關注貧困人口在旅游價值鏈中的真實地位。實踐表明,粗放的發展式旅游減貧只能惠及少數地方旅游小企業,并擴大了社區內部的收入差距,貧困人口獲得的所有旅游收益幾乎都來源于直接參與旅游的收入6,而直接的旅游參與機會是十分有限的。因此,“阿者科計劃”根據“旅游吸引物權”概念從初始分配制度維度開展工作,設計了普惠式旅游收益分配制度,保證社區內部所有參與旅游吸引物維護的農戶都能獲得旅游收入分配1。統計后發現,在阿者科的旅游吸引物權分配模式下,貧困人口能夠在門票分配中獲得多出22%的收益。此外,旅游有著市場主導的現代性特征,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并抵達邊緣地區,讓攜帶經濟與技術要素的外部經營者掌控了旅游價值生產的關鍵位置,往往只根據旅游生產過程中最直接的土地與房屋租賃、勞動力雇傭等情況對當地人進行分配。然而,旅游價值生產過程中的間接資源使用與消耗卻沒有在分配中得到應有重視,比如民宿只租賃鄉村部分房屋產權開發旅游,但卻在事實上使用了公共產權性質的鄉村整體歷史文化與環境的吸引價值,而沒有對整村居民進行利益補償。
此外,市場主導的分配制度缺乏對社區本土分配邏輯的關注。外部主體旅游收益的分配邏輯作為一種外來知識流動進入當地會經過社區經驗過濾后,結合本地傳統文化與制度規范進而生成新的分配制度知識。“阿者科計劃”在建立旅游吸引物權過程中就曾遭遇過當地傳統的村寨主義文化,為平衡旅游發展中村寨間關系,將阿者者村旅游收益10%調入行政村進行分配。
四、旅游治理可以作為貧困人口的社會增權方法
旅游不光是經濟增收工具,更是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社會增權方法。正如劉易斯發現貧困者有著自己獨特而系統的心理與文化2,“阿者科計劃”的實踐發現,關注貧困人口的文化與心理是開展社會增權實踐的基礎性工作,需要克服語言與文化差異、主體能動性、信任關系等復雜問題。例如,我們曾引導村民參與主客互動,伴隨而來的是大量游客愛心捐贈。起初,我們認為愛心捐贈應是多多益善,至少能讓無法直接參與旅游的貧困農戶也能從旅游中獲益,但逐漸發現愛心捐贈帶來了社區內部群體的心理變化,并導致主客關系矛盾,甚至強化了不平等的主體關系。例如,阿者科兒童在經常接受游客捐贈之后,開始默認所有游客都應該贈予財物,于是轉而纏著游客主動索取,一度導致多次游客投訴。旅游帶來大量愛心捐助讓貧困人口逐漸失去主動尋求生活改變的動力,并接受自己“弱者”身份,形成“自己本就應該過著這樣的貧困生活”以及“游客有錢就應該有義務來幫助我們”等復雜社會心理,陷入心理貧困的發展陷阱。在外部幫扶話語主導的旅游情境下,捐贈式減貧成為滿足游客捐贈者利他需求的工具,連接愛心捐贈資源的中介者也成功改善了企業與社區和市場間的公共關系。捐贈成為一種流行文化與商品,真正影響貧困人口長遠發展的社會心理與權益就容易被忽視3。如何調動貧困人口在旅游減貧中的發展主體性和能動性成為需要格外關注的問題。對此,“阿者科計劃”的實踐策略首先是引導村民拒絕游客個體捐贈,比如對兒童要錢行為設定100元分紅扣款懲罰規則4。然后,統一管理捐贈,搜集游客捐贈款項與物資并設立獎學金制度,鼓勵更多孩子通過教育改變貧困代際傳播。
五、旅游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方法
我們在阿者科觀察發現,旅游減貧項目顯現成效更容易引發媒體與社會關注,地方政府多個不同業務部門也會積極投入更多項目資源,集合打造“明星村”。然而,盡管旅游可以作為綜合發展工具,但并不能“包治百病”。過多、過雜的項目資源以“+旅游”之名涌入同一個鄉村,旅游成為“什么都能裝”的口袋或平臺。“阿者科計劃”的實踐表明,“大水漫灌”式項目投入反而容易導致資源浪費,甚至“創造性破壞”,比如多個項目以鞏固脫貧攻堅與人居環境整治之名對村莊進行全方位“美化”,但過度“美化”對村莊的原真性產生破壞。
項目泛濫與碎片化的另一個弊端是容易導致社區缺乏可持續性與整合發展能力,多個項目只管大手筆資源投入不評估產出,多數都走向爛尾而無人問津。從項目投入產出可持續性來看,旅游減貧不能忽視產業減貧的重要經濟功能,旅游減貧項目所倡導建立的產品框架是否具備經濟與商業可持續性?市場是否愿意持續地買單?所承建項目是否是社區急切需要的?項目經營方式是否得到社區理解和認可?項目之間是否相得益彰?是否切實增進貧困社區福祉?這些問題都應該成為旅游減貧亟須回應的問題。
總之,旅游作為減貧的重要方法,具備保護資源環境、彌合社會認知差距、重構收入分配格局、社會增權等復合功能,在后脫貧時代對解決鄉村社區所面臨的相對貧困、返貧風險以及鄉村振興等問題有著重要意義。基于“阿者科計劃”的實踐,我們認為,影響旅游減貧項目成效的關鍵在于是否有統一的管理者對減貧項目的幫扶目標、發展措施、治理策略和實踐效應進行實時調整的、精細的管理。
(作者系該院博士后;收稿日期:2024-06-09)
[責任編輯:吳巧紅;責任校對:宋志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