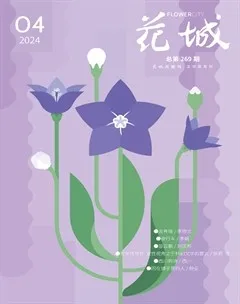安妮·埃爾諾:如何把“壞文類”寫成經典
自傳小說:一個“臭名昭著”的“壞文類”
法 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獲得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為她所擅長的文體——自傳小說正了名,雖然埃爾諾自己并不喜歡用自傳小說定義她的寫作,而且她晚期重要的作品《歲月悠悠》立意于突破自傳小說的“一己之我”。瑞典學院這樣評價她的作品——“從不同角度不斷審視因性別、語言和社會階層等差異造成的不同的生活,勇敢、冷靜而敏銳地揭露了個體記憶的起源、隔閡與集體壓抑”。
如何從女性個體記憶出發,抵達一種歷史真實和人類的真理,這是安妮·埃爾諾一生寫作的軌跡和追求,也是她的作品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自傳小說的特殊品質。說安妮·埃爾諾是因為寫自傳小說而得獎其實是對其文學成就的嚴重低估。應該說,安妮·埃爾諾是因為突破自傳小說的文體局限,再造了自傳小說而得獎。埃爾諾也認為她寫的不是個人自傳,而是“社會自傳”。
埃爾諾的第一本書《清空》出版于1974年。這是一部以她自己1963年的墮胎經歷為素材的小說。這本書也是她最接近小說的一部作品。可以想象初寫作時的埃爾諾有一種越界的緊張和欲望。她給了女主人公一個虛擬的名字,但是采用了第一人稱敘事,以埃爾諾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經驗為底本,在薄薄的面具下直截了當地描寫一個出生于法國小城雜貨店的勞動階層家庭,卻在寄宿學校上學的女孩的恥辱與撕裂,以及她發育著的身體從月經初潮、性快感到墮胎的各種經驗。初上文壇的埃爾諾沒有沿用她在大學經典文學課堂所學到的或趣味高雅或實驗大膽的語言,而是用一種直接得可怕的,并不友好的,甚至帶點粗野暴力的語言。因為她想描述她感受的真實的生活,那是一種遠非抒情的,帶有深深的社會和歷史痕跡的粗糲的生活。
埃爾諾敢這樣寫,與她寫作的年代有關。
安妮·埃爾諾開始寫作的20世紀70年代,福樓拜或巴爾扎克所代表的經典法國小說已經不再。五六十年代名噪一時的新小說實驗及其影響也已經日趨縮小。而新小說的主倡者瑪格麗特·杜拉斯、羅布·格里耶等人所提倡的物的觀察的主體意識、小說語言以及實驗精神,已然成為當代法國文學新的基因。事實上,從20世紀初柏格森和普魯斯特之后,法國社會和文學就進入了實驗年代。20世紀的法國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柏格森的影響,他關于時間、關于物質與記憶的關系的思考,以及對外在的觀察,對生命進化及自我是綿延變化的意識的實體等論述對當代法國哲學和文學的影響至深。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就被視為柏格森小說。柏格森思想還強調視覺效果。如評論家趙越勝指出,“當他論述直覺對把握實在的極端重要性,當他把記憶、形象這些藝術創造的基本要素,也當作哲學要素來闡釋時,他打開了自由的新維度”。
現代主義和先鋒派發祥地的法國在20世紀不斷地被一波又一波的哲學藝術思想實驗和運動所推動。20世紀70年代,又一個新的文類在法國生成。1977年,法國作家兼文學批評家塞爾日·杜布羅夫斯基(Serge Doubrovsky,1928—2017)用自傳小說這個詞,來描繪他自己剛完成的小說《兒子》,并用它來定義這種新文類,即以一個人的生活為主線,以第一人稱敘述的自傳性的“寫實”小說。這種自傳小說其實在以前的法語文學中有些淵源,即Roman à clef(直譯為“帶一把鑰匙的小說”),這種小說中的人物和事件隱晦地影射歷史和真人,有點像我們所說的索隱小說。
此后的二三十年里,自傳小說這個文類不僅在法國和英美盛行,在日本、印度等國家也從者甚多。如果說最開始自傳小說還只是對在非虛構的自傳和虛構的小說之間尋找某種“平衡”的作品的中性描述,那么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寫作因越來越帶有個人私密經驗,以及強烈的自我的聲音,而成為最有爭議的文類。
促使這個文類變得“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是法國作家和攝影師埃爾維·吉伯特(Hervé Guibert,1955—1991)。有新聞工作背景的吉伯特寫了許多以自己的日記為素材的小說和自傳。1990年,身患艾滋病而不久于人世的他寫下了《給沒有救我一命的朋友》,記錄生命最后一段的痛苦與面對死亡的恐懼與孤寂。因為他是第一個誠實記錄“世紀病”并直白表達個人欲望,以及他對周圍人,包括密友米歇爾·福柯的看法的人,吉伯特及其自傳寫作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這個被稱為“私小說”或“自小說”的文類,也因大量女性作家引發爭議性的作品而成為“壞文類”。當代法國女性作家筆下的自我經歷常常帶有震驚和傷痛的體驗,包括強奸、墮胎、離婚、婚外情,甚至亂倫。比如克里斯蒂娜·安戈(Christine Angot,1959— )發表于1999年的《亂倫》及《不可能的愛情》,將父母婚姻和家庭中的丑陋與病態都事無巨細地暴露出來。有些女作家還把自己與主人公等同,比如卡特琳·米雷(Catherine Millet,1948— )2002年的自傳《欲望·巴黎——卡特琳的性愛自傳》。那令人窒息的坦誠與真相在某種意義上讓很多讀者忽略了寫作這個行為和寫作者的真正用意。本來這些女作者是因為訴諸法律而沒有得到保護而寫作,巨大的恥辱感使她們四分五裂,但人們因此用“丑聞”和“不幸”來描繪女性自傳小說。毋庸置疑,90年代大量自白性作品充斥文壇,很多并無新意或原創精神,這也導致人們常常把自傳小說和家丑及暴露隱私聯系起來。
女性自傳小說還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原罪,就是所謂的自戀情結,被某些批評者嘲諷為“盯著自己的肚臍眼”的寫作。自傳小說還被指責沒有情節,沒有結構感,以嘩眾取寵的內容取代真實的情感,等等。2007年法國女作家卡米耶·洛朗斯(Camille Laurens,1957— )指控瑪麗·德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1969— )在小說《湯姆死了》中“心理抄襲”了自己的自傳《菲利普》,由此開始了一場長達兩年多的文學官司,也引發了公眾對自傳小說的真實性,寫作的誠信等倫理問題的討論。所以,充滿悖論的是,自傳小說在不斷涌現的同時,這個特別的文類也被評論家反諷地稱為“壞文類”(mauvais genre)。“壞文類”指低俗的文類,比如幻想、科幻和偵探一類的低俗小說,也指那些嘩眾取寵賣文鬻字的行為。在法語中genre這個詞除了文類還指代性別,所以這個雙關詞(壞、差、次等的文類和性別)中還暗含對女性寫作者的寫作能力的充滿性別歧視的懷疑。
發表了《清空》之后的二十年里,安妮·埃爾諾的所有寫作似乎都可以歸于這個文類。如果《清空》從形式上還可以說僅是第一人稱小說,那么以她自己的父母或母女關系為題材的《男人的位置》《一個女人》《我在黑暗中》以及一系列以她自己在生命的各個階段經歷為內容的作品,如《冰凍的女人》《簡單的激情》《恥辱》《一個女孩的記憶》,從題材或者內容上說,幾乎都是自傳性質的寫作。事實上,法國評論家瑪麗-朱塞·洛伊(Marie-Josée Roy)在評論埃爾諾小說《簡單的激情》時就用“壞文類”來描述埃爾諾的寫作,雖然她站在女性立場之上,質疑挑戰“壞文類”的定義,為寫作自傳小說而開始在法國文壇上聲名大振的安妮·埃爾諾辯護。
那么埃爾諾是怎樣擺脫自傳小說的原罪,拓寬了文學以及自傳小說寫作的可能呢?
有距離的寫作: 個人記憶中的歷史真實
那是六月的一個星期天,中午剛過,我的父親要殺我的母親……那是1952年6月15日,那是我童年時代記憶最深最清楚的日子。
《恥辱》這部回憶少年時代自我形成的自傳小說以這樣一個恥辱的記憶開頭。“后來,我曾對幾個男士說,我快十二歲那年,我的父親要殺我的母親,我幾次對人說這句話,這說明這件事已經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里了。”對中產階級的讀者和作者而言,這個恥辱的細節意義深遠。
在隨后的篇章里,作者詳盡地描述了1952年Y市的地形、人物和社會生活,同時講述“我”上教會寄宿中學時家里發生的各種事情,比如母親沒有睡裙的細節、“我”與父母旅行時的窘態,以及這個十二歲少女的種種意識——“我已經不配在私立學校了,配不上她的優秀與完美,我進入了恥辱之中”。
埃爾諾對自傳小說的警惕,或說對自我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與她特有的跨階層經歷有關。從一開始,她就不避諱自己的出身和家庭環境:在外省的小城市里長大,父母都是工人階層出身,后來經營食品雜貨店和咖啡店。但是他們送她上私立的寄宿學校,她努力刻苦,一心擺脫這個家庭和階層。以后她果然成為文學教授,并建立了自己的中產階級家庭。這段經歷讓埃爾諾對階層差別和階層意識有切膚之痛。正如她后來一再強調的,她的寫作就源于階層跨越過程帶給她的巨大撕裂,以及與之相應出現的羞恥感。《恥辱》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例子。
我要把這件事原汁原味地寫出來,讓那多年來在我腦海里揮之不去的場面重新動起來,以便驅散它在我內心深處所形成的陰影(就是這種信念驅使我寫下去)。
這個創傷記憶是促使埃爾諾思考家庭環境與自我形成的關系的催化劑,有點像催化了普魯斯特回憶的瑪德琳小點心。埃爾諾通過追究這個事件以及事件的環境充分而又生動地呈現了自我是如何開始覺醒,自我身處何樣的具體的世界,“就是這種真實將1952年的我與這個正在寫作的女人聯系了起來”。
對我來說,重要的是能夠找到自己用來思考自己以及周圍世界的詞匯……但是1995年的我是不可能重新回到1952年那個天真的小姑娘時的我了……
真正的自我記憶是不存在的。
為了找到那個真實的我,我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如今我要把我成長過程中所使用過的語言,宗教記憶以及我父親的語言價值、他們的習慣動作公之于眾,把在《時尚》和《茅屋里的聚會》所讀到的小說的內容公之于眾。
這種對某個事件的近乎窮思竭慮的追究構成了安妮·埃爾諾與她寫作的姿態,也是她作為作家與自我關系的呈現。
我不是在寫故事,因為故事本身就會闡述真理而用不著去探求它;我也并不是在寫回憶錄,只想滿足于把我記憶中的畫面原版地照搬出來。我是想把這些畫面當作材料來剖析,當一次我自己的人種學家。
就這樣,埃爾諾把文學的功能擴展成了人類學家的物種筆記。
評論者認為埃爾諾的文學突破是寫于1983年的《男人的位置》和1987年的《一個女人》。前者讓她獲得勒諾多文學獎——這個獎項被稱為法國文學最高獎龔古爾獎的補充獎,由十位文學批評家共同評出。他們看到了埃爾諾與其他自傳寫作的不同:“在短短的一百頁中,她為她的父親,以及從根本上塑造了他的整個社會環境描繪了一幅冷靜的肖像。這幅肖像發揮了她正在形成的內斂和道德動機的美學,她的風格是經過嚴格和透明的鍛造而成的。它標志著一系列自傳散文作品超越了虛構的文學世界。并且,即使還有敘事的聲音,也是中立的,并盡可能匿名。”
緊接著,埃爾諾又寫了以母親生活為主體的《一個女人》。因為“我”這個跨越了階層的中產階級寫作者的存在,對父母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情感結構,以及品位趣味的呈現,都滲透了非常清醒的階層和“區隔”的反省意識,以致有的評論稱埃爾諾是布爾迪厄式的作家。
比如在《一個女人》中,她這樣描寫父親:
父親永遠都不會打消小商人腦子的這種看法:好人和壞人。對他來說,所謂的好人就是那些到他這里來消費的人,而壞人就是那些到戰后市中心新建的商店去買東西的人……在他的內心深處,也和所有生意人的心理一樣,希望整個城市里僅有他一家商店賣東西。為此,當我們需要買一個面包時,父親也要讓我們跑很遠的路去買,就因為我們隔壁的面包店的人不到我們的店里買東西。
…………
我要以我的父親為主題,寫他的生活,寫我少年時期與他的隔膜,而這種隔膜其實是一種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隔膜,但它又是極其特殊的,不可言傳的,就像不得不分手而又情思不斷的那種愛情。
同樣,在《一個女人》中,埃爾諾刻畫了自己與母親的深厚感情和無處不在的觀念沖突,而她的人生,恰恰就是在“努力離開母親”和“深愛母親”之間掙扎的過程。
在一次訪談中埃爾諾提出正是在寫作《男人的位置》時,她理解了布爾迪厄所說的“把(寫作對象)客體化的距離”。“他幫助我產生了我稱之為從一個距離來寫作的想法。”從《男人的位置》開始,她想“以一種民族志的寫法來進行創作”。
埃爾諾這種自我的階層意識和對這種意識的一再反省,與她同時代的思想者有著諸多共振。70年代以來法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社會科學理論家就是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和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他們對知識趣味藝術習性與權力體系和社會結構之間關聯的揭示顯然也影響了同時代的埃爾諾。在布爾迪厄最重要的論著《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中,他提出品味判斷關聯到社會地位。他結合了社會理論以及來自調查研究、照片與訪談的資料,指出我們應該在客觀結構之內理解主體。布爾迪厄對主體的思索尤其是反思的概念無疑影響了埃爾諾。
埃爾諾在訪談和文章中屢次談到布爾迪厄對自己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是布爾迪厄啟發了埃爾諾方式的自傳寫作,因為在讀到布爾迪厄之前,埃爾諾已經開始孕育了后來寫作的各種想法;甚至也不全是布爾迪厄在社會調查和訪談資料中運用大量照片這種做法如何在埃爾諾的小說中留下痕跡,而是“布爾迪厄的文本對我的寫作來說是個鼓勵,就是要保留那些他稱之為社會無意識的東西”,“我得益于布爾迪厄的是將我以前認為‘超越文學’的東西作為我的寫作材料”。
她寫道:“我不認為自己是單一個體的存在,而更是一個經驗、社會、歷史、性的決定以及語言的總和,并不斷地與世界(過去和現在)對話。”
正是這種對歷史真實與自我關系的關注,以及對歷史真實的尋找,使得埃爾諾跳出了自我小說或私小說的陷阱。對個人真理的探求,發展成為對自我意識與社會結構關聯性的探討。埃爾諾的自我寫作因此避開了懷舊感傷、自戀自憐這類女性自傳寫作常常陷入的陷阱,而真正關注這些個人事件后面更壯大更客觀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因為正是這些背景構成了個人故事的形成條件,也是理解這些個人故事意義的支點。
通過寫作來解放: 個人事件的政治行為
與很多女性作家一樣,埃爾諾自傳小說寫作大多是基于與身體有關的自我成長的經歷。她的小說幾乎記錄了女性每一個階段的身體經驗:性欲望的初現、第一次性經驗、懷孕、墮胎、生兒育女、婚外戀情、HIV測試,這是一個身體和欲望的發現、發生和成熟的過程,但也常常是被創痛事件標志的過程。而與女性身體相關的創傷經驗卻不一定與生理因素相關,流血和“清空”本身并不一定有切膚之痛,它們只是生命自然循環的事實。創痛更多來自對這些生命體驗的污名化,來自社會攻擊,來自文化話語禁忌——文化話語使女性身體經驗,尤其那些不被法律和宗教承認的經驗——比如墮胎——成為禁忌,成為在流血和“清空”時也不敢大聲喊叫的秘密,甚至恥辱。千百年來,自有男歡女愛和懷孕生育,就存在人工流產和秘密墮胎。但是文化禁忌使得這部分女性經驗不可言說,也不被理解。它與道德敗壞以及墮落和懲罰相連。這讓無數女性在生理、心理以及精神幾個層面上數次被壓迫、被懲罰并失去理解自我和詮釋的可能。
在今天,與女性身體經驗相關聯的重重政治壓迫和文化禁忌依然在進行中。2022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過去五十年憲法保護墮胎權利就是這樣一種倒退。這一事件也使得以60年代秘密墮胎為題材的法國電影《正發生》獲得當代關聯性。這部斬獲第78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電影正是根據埃爾諾2000年的小說《事件》改編。
事實上,墮胎作為埃爾諾小說的重要母題一再出現。1974年她的第一本小說《清空》寫的就是二十歲時墮胎的經歷。寫作那年距1963年她在魯昂大學期間婚外懷孕墮胎事件已經十余年。最初,她用“清空”這個極富物化形象的詞語來形容那次秘密墮胎的急切以及對主流話語的挑戰。70年代墮胎在法國還沒有合理化,人們甚至不能直接使用“墮胎”這樣的字眼,而使用各種代指,比如“清空”。但“清空”這一行為本身就是對被制度和文化加持的無知的挑戰。當時埃爾諾還給她的第一人稱敘事者也是女主人公取了一個虛構的名字“丹尼斯”,一個跟作者本人的家庭出身和自我意識相近的年輕女性。她有著正常女性的種種欲望,但她同樣有對事業的抱負和成功的夢想。她不能讓懷孕阻止她奔向夢想,她不認為自己應該為自己的欲望受到懲罰。電影《正發生》中女主人公安那非凡堅定的眼神正代表了真正推動社會改變的力量,那就是她下決心為自己的身體做主,即使她要承受痛苦危險和在黑暗中被送往醫院的恥辱:“有一天我會要個孩子,但不是用我一生做代價。我會努力去解決生活的問題。”
時隔三十余年,2000年,埃爾諾又一次回到當初,寫下了《事件》。但是這一次,她用自傳小說的形式,直接認同了那個主人公“我”,那個日后成為作家的“我”。這個“我”在最近一次HIV化驗檢查后發現自己沒有問題,但相似的恥辱經驗使她意識到幾十年前那場墮胎事件于她個人,更是于她所屬的那個性別集體留下的深重創傷。但那本不必是一次創痛,是社會風俗,是人為的各種話語規定讓它成為“女性病”。所以她必須再一次回到過去。理解這段肉體創傷經驗的過去,就是對無知和禁忌的宣戰。
與早期的《清空》相比,《事件》不僅用墮胎這個題材來撕破社會禁忌,更用作家這個敘述者的聲音,揭示與這個禁忌經驗相關的歷史與政治意義。這個敘述聲音不過激,也不感傷,但具有一個寫作者的強烈意識,它直接準確地宣告寫作這種經驗的重要性:
我想再一次沉浸在我的這階段生活,理解在那里發生了什么。這種調查必須在敘述的語境中才能完成。
…………
我個人墮胎的經歷已經成為過去,并不是放棄它的理由。
…………
我要努力重溫每一個意象,直到我感受到我已經從物質意義上與它捆綁在一起。直到詞語噴薄而出,讓我能夠說,對,就是它。
這個第一人稱敘事者冷靜地看著當年那個驚慌掙扎的年輕女子,誠實而完整地寫出那個年代女性身處的外部環境以及她們的內心意識,從發現懷孕到尋找各種辦法墮胎,她一步步寫出所有的事實與細節,以及當時的精神狀態,這個可怕的經歷以及對她造成的影響。她像對待一個心理分析的案例,把折磨她個人幾十年的身體經驗與更廣闊的階層,與宗教和法律的世界連接了起來。她如此耐心地寫著,因為她在進行著一個療愈的過程。可惜《正發生》因為電影形式的限制,雖然對60年代女性秘密墮胎所經受的恐懼和壓力有準確的呈現,卻沒法展現埃爾諾原文中第一人稱敘述者的那種反思意識,而這恰恰構成了埃爾諾小說最重要的特點:女性自我的成長與領悟。
這個“現在”的制高點正是由作家這一身份所賦予的。她要把秘密的禁忌說出來,把如何造成這一切的社會法律宗教甚至家庭和教育的原因和背景都統統寫出來,通過她的個人感受,個人創傷,但并不是為她一己之故。
我一周前開始寫這個故事,不知道能否完成。我只想確認那種寫作的緊迫感依然在那里。……現在我要走完這個過程,就像當年23歲時走完墮胎那段路一樣。
…………
如果我不能做到,我就會內疚。為讓那許多女性生命緘默,為原諒一個被男性優越所統治的世界感到內疚。(《事件》)
所以《事件》也是關于個人如何回憶,如何重塑過去,如何呈現那個痛苦的事件,也就是關于寫作的文本。在這里,事件不是自動呈現,而是在“我”的追尋和凝視下,用帶著細節的記憶,以及過去的斷簡殘章,如當年的日記,被再次“發現”。這個再現的過程與當年的事件一樣重要,如果沒有這個再現,女性的經驗將永遠被放逐,無法完成它們在社會和文化中的意義。同時,這個敘述呈現了女性成為女性(becoming)的過程和能力,不僅成為一個生理女人,也成為對性別意識及其形成有了理解和認識的心智成熟的女人。所以埃爾諾書寫墮胎經驗的顛覆性是雙重的,她相信法國知識分子的社會承擔,她說寫作是一種政治行為,讓我們看到了社會不平等。通過一系列女性私密生活的自傳式作品,埃爾諾把她自己和她的性別集體從禁忌、恥辱和沉默中解放了出來。
時間的力量:從個人出發抵達集體
讀埃爾諾小說的人不難注意到她寫作的時態,那經常是一個生命旅程的現在與過去。最新的《一個女孩的記憶》就發生在1958年的夏天,在18歲的安妮、“58年的女孩”和2016年那個書寫這段年輕時光的老人之間。這是她小說中一再出現的寫作主體與小說人物的關系。她們構成的不僅僅是時空的關系,更是一種倫理的關系:書寫者在比較了當時日記中寫下的和她當時的經驗之間的鴻溝,意識到年輕的安妮,受各種壓力和自我的局限,如何壓抑和控制自己對這個經驗的理解和記憶。所以,“記憶是不可靠的”。埃爾諾并不認為過去能客觀存在,也不能完全存在于頭腦中。一個成熟的人必須充分理解時間帶給我們的心智成長,一種審視過去的距離,這不只是一個記憶的過程,更是一個發現的過程。
“如果不是挖掘發現,寫作還有什么意義?”
《紐約客》2020年一篇評論文章說,埃爾諾是一個不信任自己個人記憶的自傳作家。的確,埃爾諾寫作的核心,是意識到生活中那些最私密的時刻,其實是受周圍的社會環境所支配,因此探索個人成長,必將涉及對歷史的深入調查。
2008年的《歲月悠悠》就體現了這種對自我與歷史關系的反思。在這部后來為她贏得了很多文學獎的作品中,埃爾諾一方面記錄了自己的人生歷程,記錄了兒時的貧困生活、努力求學、墮胎、當教師、離婚、患癌乃至衰老;另一方面,埃爾諾又創造了“無人稱自傳”(impersonal autobiography)的新體裁,通過對自己成長的歷史環境的全力呈現,她所書寫的不只局限于一個人的故事,而成為一代人共同擁有的時代記憶,包含關于個人如何生活其中的法國20世紀的生活歷史。
這部時代記憶的組成部分有20世紀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包括阿爾及利亞戰爭、1968年的五月風暴、核威脅、柏林墻、阿拉伯移民和九一一恐怖襲擊;也有從作者出生的1940年到她寫作時的2006年間的法國流行文化、日常生活以及穿插其間的法國文學。而把這些記錄、事件片段、照片連接起來的就是敘述者的意識流,她的觀察,她的分析,她的感悟。
她想用一種敘事的連貫性,即從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出生直到今天的生活的連貫性,把她的這些各種各樣分開的、不協調的畫面集中起來。這就是一種獨特的,但也是融合在一代人的活動之中的生活。在開始的時候,她總是在同樣的難題上遭到挫折:怎樣同時表現歷史時間的流逝,事物、觀念、習俗的變化和這個女人的內心,使得四十五年的宏偉畫卷與對歷史之外的自我、她在二十歲時用來寫作《孤獨》等詩歌的那些中止的時刻里的自我追尋相互吻合。在“我”里有著過多的穩定性,某種狹隘的、令人窒息的東西;在“她”里有著過多的外在性,過遠的距離。她對她尚未寫出的作品的印象,它應該留下的印象,是她從十二歲時對《亂世佳人》,后來對《追憶似水年華》,最近對《生活與命運》的閱讀中保留的印象,一種陽光和陰影在一些面孔上的流逝。然而她沒有發現達到這一點的手段。她希望,偶然性提供的即使不是一種啟示,至少也是一個標志,就像浸泡在茶里的小點心對于馬塞爾·普魯斯特一樣。(《悠悠歲月》)
書寫《悠悠歲月》固然來自“她”對自我過去的懷念留戀,但更是對過去的事件和變化的自我的渴求理解,來自一種人類面對時間死亡和消失的不甘,如《悠悠歲月》那個敘述人所說的:“這個世界留給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她要用來重建一個共同的時代。從很久以前逐漸轉變到今天的時代——在個人記憶里發現集體記憶的部分的同時,回復歷史的真實意義。她要注釋自己只是為了從中看到世界,在世界在過去的日子里的記憶和想象中,掌握她所了解的一切觀念,信仰和感覺的變化,任何事物的改變……”
讀者會注意到,這本書中,敘述者已經不是第一人稱“我”,而大多是一個人(on),可以譯為“我們”。有時埃爾諾也用第三人稱“她”,好像在談論一個在時間中不斷變化的客體,是某個人,也是一切人。
年老的埃爾諾回憶說,當年她在大學生的宿舍里寫作的時候,她希望找到一種像通靈者那樣能揭示神秘事物的陌生語言,但沒有那樣一種咒語突然降臨,她也只能在她的語言,所有人的語言里寫作,這是反抗一切(外界對人)施加影響的唯一工具。要寫的作品就代表著這種反抗和斗爭。她沒有放棄這種雄心。現在步入暮年的她想捕捉從此以后看不見的面孔,以及“擺放著消失的事物的桌布的光線……一種從前的光線,挽回我們將永遠不再存在的時代里的某種東西”。
而這光線,正是寫作所體現的一種人類的精神,那種與時間流逝對峙的不甘和抗爭。
無人稱自傳的創造,既是埃爾諾對個人記憶的普世性的肯定,也表達了一種堅定的人文思想:有意識、有反省能力的自我的成長也是個人與世界融合不是和解的過程。“我不認為自己是單一個體的存在,而更是一個經驗、社會、歷史、性的決定以及語言的總和,并不斷地與世界(過去和現在)對話。”
埃爾諾2009年曾致信中國讀者,希望他們通過《悠悠歲月》“接觸一種法國人的記憶。一個法國女人的,也是和她同一代人的人所熟悉的記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今天的記憶,在各種生活方式、信仰和價值方面,比他們幾個世紀里的祖先有著更多的動蕩。一種不斷地呈現一切事件、歌曲、物品、社會的標語口號、集體的恐懼和希望的記憶。它根據對從童年到進入老年的各種不同年齡所拍攝的照片的凝視,同樣勾勒了社會的進程和一種生活的內心歷程”。
所以說埃爾諾只憑把家庭秘密和個人經歷的自傳式寫作就得獎則似是而非。事實上,正如諾獎頒獎人安德斯·奧爾松(Anders Olsson)所說:“一方面,埃爾諾寫作是繼承了普魯斯特法國文學傳統對個人經驗的根源的追尋探討,另一方面又把這個傳統引領到新的方向,那就是這一追尋的社會環境。”“她的文體非常有力量,既簡要又不妥協。”其中有法國文學背后深厚的哲學傳統和當代社會學的痕跡,又有她個人對寫作意義的認識。埃爾諾一再強調她的寫作是文學而不是自傳,也是在強調個人經驗后面的普遍真理。她希望自己使用語言就像一把手術刀,“撕開想象的面紗”。埃爾諾是在對自我的起源和局限性的認識上,在與“壞文類”所背負的與生俱來的原罪的審視與斗爭中,拓寬了文學以及自傳小說寫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