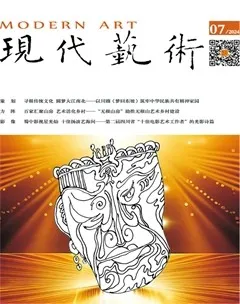梅嶺飄香二月茶
風過瀘州帶酒香,一壇老窖醉江陽。古今賢人愛在此唱酬抒懷,留下美名、佳作無數(shù)。梅嶺早茶二月采,不知其味如何。帶著好奇與向往,出發(fā)納溪。
梅嶺茶山靜佇于川南丘陵,與鳳凰湖濕地公園相伴。山是富含鐵質硅藻的巖石風化而成,褐紅的土壤得長江與永定河的滋潤。我們到時它已蘇醒,晨光熹微中青綠可鑒,薄露含香。茶樹梳著整齊的辮子,在花明柳萌下像波浪一樣從山谷向山巔起伏,又向遠處蔓延。讓人頓生“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有無間”之閑適。有這滿目翠色的呵護,我深信這里確為茶的溫柔鄉(xiāng)。
說起飲茶,宋人最為風雅。掛畫插花,焚香點茶,坐酌一壺水,看煎瑟瑟塵。初見熱播劇《夢華錄》中的“納溪梅嶺”,以為是現(xiàn)造的一個佳詞,不想這劇是從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摘取的精華,其名號早就出現(xiàn)在陸羽的《茶經(jīng)》中。精美且大氣!地球同緯度的區(qū)域中,梅嶺茶發(fā)芽最早,博得了茶中頭彩。其實更早的茶可在除夕前采摘。原來供請灶王爺上天言好事的年夜茶,便采自梅嶺。只是,“年夜茶”為何沒有拼過“二月茶”登上貢臺?因為缺少一位像黃庭堅這樣的“大網(wǎng)紅”代言。若某位大咖在除夕夜喝了梅嶺茶而眉飛色舞,贊不絕口,且揮筆題名。刻于清溪河道石壁上的,恐怕就不是“二月茶“了。
今年的“二月茶”早已飛入亭臺樓閣與檀香作伴,或是在尋常人家待客養(yǎng)神。眼前的茶山正在休養(yǎng),靜靜地積蓄著下一春的能量。可喜靜謐無語的茶樹仍有細嫩的茶尖調皮地冒著頭。我掐了一芽放進嘴里,細細咀嚼起來。友人說:茶味是嚼不出來的,還需要通過高溫破壞和鈍化鮮葉中的氧化酶活性,抑制茶多酚,分解青臭味,才能促成茶香生成。
原來“茶香”蛻自“青臭”,就像君子也有過懵懂。可見炒茶的工藝,也是成茶的功夫。
體驗大廳里布陳著今年新采的各色茶品,先到的朋友泡出了“鳳羽”的香味,我于眾多茶品中找了泡“榮龍”。轉一圈回來啜一口香茶,咬一口“甘露凝成一顆冰,露秾冰厚更芳馨。”友人笑說,這吃的是國家地理標志產(chǎn)品。我說,吃的是兩千多年前的貢品。有一說,“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中的荔枝是川南精靈,而非嶺南佳果。只因“大網(wǎng)紅”蘇大人“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讓嶺南荔枝家喻戶曉。事實上,瀘州合川荔枝已有兩千多年栽種歷史,比起廣東、廣西荔枝五六月就熟透了來說,八月成熟的川南荔枝更稀奇,更合貴妃挑剔的“品胃”。當年車馬慢,即使有寶駕晝馳夜行,到長安的距離,嶺南也是數(shù)倍于川南。所以,貴妃吃的是兩三天就能到的川南荔枝,而非八九天才能到的嶺南荔枝。只是不知貴妃當年笑吃果子時喝了梅嶺二月茶沒?
上馬境內的桃花源是納溪人周末的好去處,而深處的紅豆杉林,空氣中彌漫著一股特別的香味,這是納溪的另一個集產(chǎn)、學、研為一體的康養(yǎng)園區(qū)。三年的紅豆杉青春正盛,資料上說它的提取物可入藥,據(jù)說秋冬來此采紅豆果的人絡繹不絕,除了市內游客,還有周邊其他市州慕名而來。有些還會選擇在旁邊的小木屋住上一兩天。宿在“梔子花”或者“百合”閣樓里,會有“疑怪昨宵春夢好,原是今朝斗草贏。笑從雙臉生”的清幽。早晚去紅豆杉林跑步晨練,黃昏泡杯梅嶺茶,垂釣于黃龍湖畔,就有了擁抱層林,釣香于溪的美妙體驗。
爬上紅豆杉林的觀光亭,但見黃龍湖在指畫山河中,綠波靜靜流。因為有了這一湖水,“川南明珠”就有了泉眼和靈氣。這萬畝紅豆杉、千畝桃花源、百里濕地生態(tài)的“水鄉(xiāng)”才生出別樣的“水香”。現(xiàn)代觀光農業(yè)在這里呈現(xiàn)出真實而美好的樣子,“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得到了很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