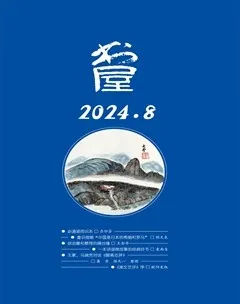《幻想底盡頭:穆旦傳》后記
說起來,或許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1994年下半年的時候,王一川教授主編的多卷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問世,小說卷收錄金庸的作品而將茅盾排除在外,自然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所在。但對于一位剛剛進入大學的中文系學生而言,“并不廣為人知”的穆旦被推上詩歌卷的首位,或許才是更值得注意的事實。
之后也有過一些閱讀和談論,但能夠記起的畫面不多。更確切的行動,應該是世紀之交的時刻,穆旦最終被選定為我碩士畢業(yè)論文的選題——其時,穆旦研究(包括文獻整理)的總體格局未定,論文主要是基于文本的細讀或所謂思想的辯詰,也做了歷史尋訪的工作,我曾去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等地查閱原始資料,得見穆旦早年詩集和若干早期詩歌的發(fā)表本,注意到了不同版本間所存在的差異。(近乎一種直覺,當時并沒有所謂版本、底本、異文等概念。)而隨后《悲觀的終結》的寫作以及采訪楊苡、杜運燮、江瑞熙(羅寄一)、鄭敏等人,大概可算是新的開始。實際上,四位友人在同一個時段來談穆旦,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學四人談穆旦》,2002)內容很豐富,道出了許多非親歷者不能體察的內容,所勾描的“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而不得的穆旦形象也生動可感,以致自己當時學識的淺薄、眼界的有限以及訪談技術的粗糙,似乎都不那么醒目了。
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關于穆旦研究的文字已成系列,側重點自然是各有不同。《穆旦年譜》處理的是編年問題,《穆旦與中國新詩的歷史建構》是史論的路數,《穆旦詩編年匯校》著眼于版本,《一個中國新詩人:穆旦論集》是專題論文集,《穆旦研究資料》(上、下冊,與李怡教授合編)是研究文獻的匯編,《幻想底盡頭:穆旦傳》則可說是綜合性的寫法——這么說似乎有點奇怪,實際上,這關乎傳記的寫法。基于并不算短暫的研究生涯和比較多的傳記類文字的寫作,我愈發(fā)傾向于認為:二十世紀的文化語境盤根錯節(jié),復雜難辨,傳記(也包括年譜)類著作很有必要突破傳(譜)主的單一性文獻的局限——突破的力度越大,越能呈現出廣闊的傳記知識背景,也就越能呈現出復雜的時代面影。由是,一部傳記,對寫作者的綜合能力——如何融入傳主的人生、寫作、時代諸方面因素,又能保持必要的平衡——是不小的考驗。不過,這方面的想法還沒有系統地進行歸結,暫且打住。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二十多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生態(tài)已大為改觀,穆旦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相關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已比較完備,穆旦的經典化程度也大有提升。這些變化固然引人注目,尤其是想到自己對這一進程有所推動,有時也會為之振奮,但“二十多年”,實在不算是短距離了。一個人由青蔥歲月走到知天命的年紀,心里難免會況味雜陳。學術工作之甘苦,實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或許,在一本書的結尾,更適合說說有時候浮現出的那樣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因為詩歌、因為文獻搜集而結識的不少天南海北的同道中,有一個微博時代就已結識但至今未曾謀面、現在也不那么年輕了的朋友,他很喜歡穆旦,做著跟文學毫無關系的工作,最初只是在微博上互動,有時會跟我透露些穆旦的資料,比如詢問某網上的某個材料是不是穆旦本人的字跡之類。(東西是真的,但有代抄的情形)某次,我為學報主持的詩歌研究欄目刊出穆旦研究專輯之后,給他寄去一本,他說也要給我寄個東西。我猜想可能是他的詩集之類的吧,哪想寄來的竟然是穆旦的第三部詩集《旗》。后來他考取了北方的一所電子研究所的研究生,畢業(yè)后在一家公司上班。我又給他寄過書,他后來又說要給我寄東西,收到一看,是一疊穆旦“交代”材料的復印件(花了不小的價錢購買獲得)。在那些時刻,你真會覺得,即便學術研究的讀者再少,有這樣一個讀者,也是值得的——何況,現在穆旦是熱門的研究對象,很受讀者的歡迎。
提到“交代”材料,順帶說一句,當初覺得去查穆旦檔案多有波折,如今看來,其實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事情了。時代總在發(fā)生改變,一個研究者總會遭遇這樣那樣的無法進入或無法抵達的境況,奈何!
書名中“幻想底盡頭”,出自那首被認為是開啟了穆旦晚年寫作的《智慧之歌》: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
這是一片落葉飄零的樹林,
每一片葉子標記著一種歡喜,
現在都枯黃地堆積在內心。
一個“從幻想底航線卸下的乘客”,“永遠走上了錯誤的一站”(《幻想底乘客》,1942),在1976年3月這個時間節(jié)點上,已然走到了“幻想底盡頭”——精神的折磨還在持續(xù),又因夜里騎車摔傷腿而新添肉體的疼痛。“幻想”在穆旦的寫作中算是比較高頻的詞匯,也有著非常切實的人生含義——疼痛感最終也沒有消失,1977年2月26日,終于決定動手術的穆旦因心臟病發(fā)作而倒下!
我曾經向一些年輕的朋友(主要是我的學生)許諾,比起其他幾本穆旦研究著作,這一本可讀性更強些,沒有那么多的學究氣,但現在看來,它依然不是一本輕松的書。這一方面是因為傳主的經歷,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對文獻的審慎處理,全不是“講故事”的寫法——秉持的是“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然后可說三分話”的原則,努力去追摹史家的筆法,而不作文學式的虛構與渲染。但不管怎么樣,作為幾本穆旦研究著作的作者,我還是更希望大家來讀一讀這本書,它講述了一位中國詩人并不順意的一生,也展現了一個風云變幻莫測的時代。
“二十多年”確實已不是人生的短距離!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學位論文都選擇了以穆旦為主題,感謝業(yè)師劉俊先生和吳俊先生的引領、教誨和寬容,你們的學術風范始終是我前行的動力。為此,也要感謝南京大學文學院、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所提供的成長環(huán)境。而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所度過的大學歲月,作為故事的緣起地,也是值得銘記的。
感謝洪子誠、吳思敬、陳子善、丁帆、李方、成松柳、程光煒、解志熙、羅振亞、郭娟、李怡、張新穎諸位長者一直以來所給予的誠摯鼓勵和幫助。感謝周立民、陳越、徐自豪、王可、李東元、鄧招華、凌孟華、楊新宇、劉波、張元珂、司真真、喬紅、李哲煜、馮昕諸君熱情無私地提供相關文獻或在文獻查找上所給予的幫助。本書的一些篇章,曾在《書屋》《新文學史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讀書》《詩探索》《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首都師范大學學報》《漢語言文學研究》《長沙理工大學學報》《魯迅研究月刊》《揚子江評論》《文學評論》《現代中文學刊》《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等刊物發(fā)表,感謝你們的支持。
還要特別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和肖海鷗女史接納此書,只是因為在2022年7月的時候,看到一則關于“藝文志eons”的推文,里邊有《T. S. 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巴赫傳》《本雅明傳》以及張新穎教授的《三行集》等訊息,立刻就覺得要是“穆旦傳”能放到這里出那就太好了。托母校的劉曉麗教授詢問,很快就聯系上,并且確認“好運都是這么來的”:海鷗說自己“非常喜歡穆旦”,之前藝文志公眾號推送張新穎老師寫穆旦的文章的時候,就有朋友轉我的文章給她看過;又說,張文江老師把《錢鍾書傳》改完交她重版,“要是能加上穆旦傳,那終于能做一些中國了不起的人物了”,遇到這樣的出版者,是何等幸事啊!
所以,不管時代如何流逝,生活總有無限的美好。還是那句話:愛詩者,將與詩同在!
(易彬:《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