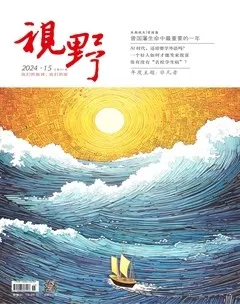一個孩子身上的英雄主義

一
以前支教的時候,班上有一個貧困生,當時那個男孩子只有十二歲,爸爸死得早,媽媽跟別人跑了,留下他和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
他每天一起床,就得先做農活挑水做飯,然后急匆匆地趕去學校上課,放學后又要去放牛割草,把家里的事情都忙完后才能寫作業。
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身體都沒有發育好,卻要和大人一樣做農活。我曾經看過他割麥子的樣子,戴著一個草帽,握著鐮刀,一低頭幾乎就看不見他的人,烈日炎炎下他的動作緩慢卻堅定,就像《孤獨的守望者》那張插畫。
這個孩子成績特別好。當時學校有兩個數學競賽名額,我把他報了上去。去市里考試需要一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我看到他拿著兩個干癟的饅頭對著白開水在那吃,就把他帶去餐館吃飯,點了幾個小菜,他卻遲遲不動筷子。
我問:你不餓嗎,怎么不吃飯呢?
他支支吾吾地說:我沒錢。
我拍了一下他的頭:和老師一起吃飯,能讓你出錢嗎?快點吃,下午好好考試。
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才狼吞虎咽。城市的一切對他來說都是新奇又陌生的,他興奮地望著那些高樓大廈和電子屏,仿佛看到了新世界。那一次他發揮得很好,得了一等獎后縣里還專門派人把獎狀和獎品帶到學校,其實也不是特別大的獎品,就是一塊電子手表,估計也才幾十塊錢,但他把手表握得緊緊的,仿佛拿到了寶物一樣。
這個孩子沉默卻不敏感,并不像一般貧困生那樣容易自卑。我去他家做家訪的時候,雖然早有耳聞他家很窮,但親眼見到的時候還是被震驚了。
這是一個怎樣的家啊?就是黑黢黢的兩間房,滿是灰塵和雜物,唯一的電器就是一臺黑白電視機,還是搜不到信號做擺設的。他卻很大方地給我找了個椅子,然后從開水瓶里給我倒了杯水,像個大人一樣招呼我。他奶奶拄著拐杖顫顫巍巍地出來,說這孩子從小就懂事,腦袋也聰明,就是命不好,兩個大人都不靠譜,要我多照顧一下他。
面對老人的囑托,我只能紅著臉點頭答應,但我自知沒什么能力,我也不過是個大學生而已,我能改變什么呢?
我只能盡力去教他。我經常對他說,你想改變現狀,就要拼命讀書。人要突破自己的逆境,就得拼了命去努力。
二
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他經常去鎮里的書店看書,從他的村子到鎮上,步行要一兩個小時,他早上出門可能中午才能到,有時候回來時天都已經黑了,他卻不覺得疲倦,臉上往往有滿足的笑容。
這個孩子有兩件事讓我印象深刻。第一件是有個學生被牛給頂傷了,大概是那個學生調皮,故意去挑釁路邊的水牛,結果牛發狂了用牛角把他給頂傷了,傷得特別嚴重,胸口都出血了。這個孩子看到后疾步跑過去扯住牽牛的繩子,把繩子系到一棵樹上后把那個受傷的學生一背,飛一樣往村里醫務所跑。
結果受傷學生的家長趕過來,二話不說就給了他一巴掌,那個家長怒罵說肯定是他不好好牽牛把那學生給弄傷的,要是有什么問題要他償命。
旁邊的小孩子連忙為他辯解,說那牛是別人家的,他只是幫忙救人而已。
那家長訕訕地看了他一眼,卻沒有道歉,扭過頭看受傷的兒子去了。
他的臉都被抽紅了,他捂著臉走出門外,然后蹲在地上哭起來。農村往往是這樣,沒爹娘的孩子活該被欺負。
但是后面遇到這種情況,他還是會毫不猶豫地去幫別人,因為善良已經刻進他的骨子里。他的奶奶經常教導他,要做一個好人,哪怕做好事受了委屈,也不是去當壞人的理由。
第二件事就是村子里的大孩子要搶他手表,他當然不會給,大孩子就把他圍起來打,下手也挺沒輕重的,他的腦袋和下巴都出血了。
有個大孩子打起性了,拿起一塊磚頭說:你到底給不給?不給我砸死你。
他把手表護在胸前,眼神里滿是倔強。
那孩子說砸就砸,磚頭砸在他胸口上,他悶哼一聲眼淚都疼出來,卻還是不肯求饒。我那時趕到現場,給了那大孩子一耳光,吼著說:你想做什么?把你爸喊來。
那大孩子還還嘴:你給我等著,我爸來了打死你。
我又給了他一嘴巴,他終于怕了,開始哇哇大哭,結果那個家長趕過來,因為我是支教老師又是大學生,村民都對我很客氣,那家長給我賠了個不是就把那孩子拎走了。我把躺在地上的孩子扶起來,掀開他的衣服一看,胸前瘀青了好大一塊。我說:下次再有這種事,你先把東西給他們好了,老師事后會給你要回來的。
他擦擦眼淚說:這是我最看重的東西,我不會給他們的。
我這才想起來,這塊電子表是他考試獲得的獎品,是他長這么大第一份榮譽,對于他而言,有著無可比擬的意義。
三
我支教結束離開小學的時候,特意去書店買了幾本書,然后送給了他,每本書上我都寫了一些話。我并不能給他多少物質幫助,我只能盡力給他一些希望和勇氣。
七年過去了,他考上了南京大學,以鎮上第一名的成績。他還特意給我發了信息,說謝謝我當年的教導。
我只覺得感動,因為我能想到這個成績背后的艱辛,他讀書時的每一分學費,可能都是省出來或者借來的,他的每一件衣服,可能都有補丁和線頭,而在每一個寂靜的深夜,他都會和恐慌不安做對抗,一次次給自己打氣,鞭策自己拼命走下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即是遭受了不公正的命運,認清生活本質后依然能無畏前行。作為一名老師,我感到慚愧,因為我從他身上學到的遠比我教給他的要多。
(張秋偉摘自微信公眾號“第四條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