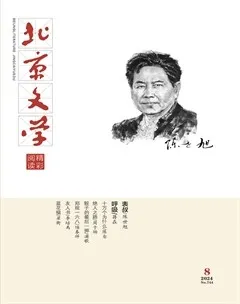尋找莫青平
1
兩個月前,莫青平忽然消失。
那時,我正忙新書出版的事,與小北反復溝通編輯校對、與出版社溝通封面設計。小北說我是徹頭徹尾的完美主義者。我苦笑。剛認識莫青平時,他也這樣說。那天,我們坐在咖啡館靠窗位置,陽光透過整面玻璃打在他身上,我坐在他對面光照不到的地方,看著他像百度百科一樣一字不差解釋了完美主義。
莫青平淺笑著用右手端起青藍色孔雀花紋咖啡杯抿了一口。這種咖啡杯是英國wedge wood古瓷咖啡杯,看似很薄,實則很結實,不怎么摔得壞。莫青平邊說邊放下咖啡杯,九十五度靠在米色布藝沙發上,雙手交叉放在膝蓋處。
四月的廣州已有些悶熱,莫青平穿海軍藍襯衣、淺灰色條紋西裝,戴青藍色領帶,在陽光直射下坐了一個多小時,竟絲毫沒出汗。莫非他的體溫也和其他方面一樣異于常人?
那天,我們在咖啡館坐了很久。熾熱的光慢慢從他身上褪去,緋紅的夕陽漸漸灑在我身上,直至黑夜籠罩窗外。我們不是一直在聊天。很大一會兒,我們什么都不說,只是看著窗外錯落的墻面、鼎立的羅馬巨柱以及盤根錯節的古榕樹。
后來,我們也時常來沙面島散步,偶爾會選一間咖啡館度過大半天時間,我敲敲打打寫我的書,莫青平則讀些哲學、心理學之類的書。莫青平說,這類書是研究人的,他得好好理解。我笑說,書讀百遍,其義自見。莫青平說,大部分書他都會背,但不理解意思。我不信,隨便抽幾本考他,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說出來。沒人的腦子能記這么多且這么準確,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一臉不可置信。很久之前記得的。莫青平輕描淡寫地跳過了這個話題。
他身上總有很多超乎我意料的東西。
莫青平徹底消失兩個月后,我的新書已面世,小北時常發信息通知我新書的銷售情況。眼下我把一切都委托給了小北。除了在沙發上挺尸,我對一切毫無興致。在你對現實沒辦法的時候,沒什么比一張這么舒服的沙發更能給你安慰。除了吃飯上廁所,我長久陷在沙發里,試圖找回一點睡眠,可腦子反復被凌亂的思緒穿刺,沒有片刻安寧。看著棕色的光面皮沙發塌陷出一個完整的人形,我拿手機拍了一張照片,發給莫青平。兩個月來,我一如既往發很多信息給莫青平,盡管他一條都沒回復過。
莫青平像一個滾燙的種子,在我心間不斷向下生根。我迫切想找個認識他的人聊聊他。我攤開四肢躺在沙發上,翻著手機通訊錄里的472個聯系人,很多人竟已想不起,也許曾經認識過,太久沒聯系,忘記了。又或者,很久以前只是一面之緣,不能算認識,所以一點也想不起。刪除他們的時候,我設想,也許某天有個陌生號碼打來,很熟悉地打招呼說,你好孔達珍,好久沒聯系了。
孔達珍,好久不見。
莫青平會不會忽然出現,笑著對我這樣說。那么,我該怎樣回應?轉身就走?又或者把自己裝進他懷里,像無數次擁抱的時候一樣?太沒出息了,對一個一聲不吭就消失的男人,得有個更絕情的反應。
胸口像壓了一塊巨石,我翻身側躺,眼里赫然出現了龐宇的電話。
龐宇……我想起來了,莫青平的朋友,據我所知,也是他唯一一個朋友。半年前,我們一起吃過飯,飯后,龐宇說留個聯系方式,以后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聯系,我們留了電話、加了微信。僅此而已,后來再沒聯系過。我已想不起龐宇的具體模樣,只大概記得他是個不愛說話的理工男,像所有理工男一樣,文靜秀氣還帶點清冷。
猶豫再三,我撥打了龐宇的電話。幾秒后,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疲憊的男低音,你好。
你好,我是莫青平的朋友孔達珍,我們一起吃過一次飯。
誰?
莫青平的朋友孔達珍。半年前,我們一起在長青路吃過一次飯。
哦,我知道了。我現在在外地出差,你找莫青平是吧?我一個月后回去了聯系你。
你知道他在哪兒?
知道。
他在哪兒?我找他有事。
你找不到,而且也進不去。我一個月后回去了聯系你。
還沒等我再接著說,對方快速掛斷了電話。
2
來廣州不久我就明白,在廣州大浪翻涌的生活里,我不具備結群能力,我與他人之間注定生出漫長的疏離。只有小北,時常穿越我認為不可逾越的疏離帶,把鮮活的生活輸送到我面前。宅家不出的日子,小北偶爾來我家留宿一晚,趁機把自己的戀愛故事、出版社里的八卦、文學圈里的起起伏伏一一道來。小北的表達欲時常能填補我微弱的生活現場感。
小北快四十歲了,但看起來就三十歲的樣子,身材纖瘦,五官精致,茶色中短發完美落在鎖骨上。你沒法用某個詞或者某些詞定義她。她活得只像她自己,或者說她自己也不能完全確定她的生活狀態。小北只有母親,聽小北說,父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走了。我不確定,小北說的走了是離開家了還是去世了。我沒問。如果是拋妻棄子,小北會恨;如果是去世,小北會痛,沒法說哪種傷害更大。
小北的母親是廣州本地人,開明厲害,從不抱怨,也從不干涉小北的事,包括小北是個不婚主義這件事。小北說,婚姻本就是維持種族的特別安排,只要達成生殖目的,造化便不再惦念嬰兒的雙親是“永浴愛河”,還是只有一日之歡而已。小北接著說,當然,這不是我說的,是某位偉大的哲學家說的。
小北左手托住棱角分明的下顎,右手擺弄著手上的白色立體鑰匙扣。
莫青平有消息嗎?
沒有。
一個人怎么會莫名其妙消失?見莫青平第一面,我就有種說不上來的感覺,不是好,也不是壞,就是未知或者不可知。你知道,任何人與人的關系都是未知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斷建立關系,以對抗時間的虛無和生活的瑣碎。但人卻是可知的,初次見面,你的潛意識會獲取一些對方的信息。莫青平屬于未知的那種人。你了解他嗎?小北在沙發另一側躺下,用涂了大紅色指甲油的腳趾蹬了蹬躺在這頭的我。
了解?怎樣才算了解一個人?莫青平身高一米八一,北京人,在一家科技研發公司上班,不抽煙不喝酒,無不良愛好,交際圈僅限于同事,生活作息規律,上班、運動、陪我。他知識面廣、記性好,不怕冷也不怕熱……我還知道更多,可又能怎樣?他還不是一聲不吭地消失了?
我仰天盯著天花板。風從陽臺半開的窗戶吹進來,水晶吊燈丁零零響。
真好聽。小時候我用一天時間做了一個千紙鶴門簾,就是用很多條線穿起一串串五顏六色的千紙鶴,并排掛在門上,風穿過的時候,我似乎也聽見了這種丁零零的脆響。可不到五分鐘,小我兩歲的表弟故意從中間跑過,把一個個千紙鶴扯下來,撕碎了。我一直哭,拿他沒辦法,我希望父母替我教訓他,可父母說,就是些碎紙疊的小玩意兒,壞就壞了。哪怕我站在門邊哭了一兩個小時,他們也沒理睬我。你對一切毫無辦法,最后不得不妥協,接受自己最珍貴的東西在別人眼里一文不值。小北,你說人是不是就是這樣反復妥協,以至于最后什么珍貴的東西都丟了?
爸爸離開的時候我六歲,那天,爸爸媽媽吵得很兇,比廣州最厲害的雷雨天還讓我害怕,我們住的老舊小區,樓都快被他們吵塌了。爸爸忽然安靜,抱了抱我,轉身往外走,我不知道那意味著什么,我只是下意識地拉他的手,不讓他走,可他回頭看了我一眼,甩開了我的手。我依然記得他額頭及太陽穴上青筋凸起,兩眼浮腫,紅血絲幾乎布滿整個眼球。從此,我再沒見過爸爸。那時,我寧愿拿從小到大所有珍貴的玩具換回爸爸,對我而言,那時最珍貴的就是爸爸。再后來,18歲,我第一次談戀愛,和喜歡的男生一起騎車,清冷的月色下,牽手在珠江邊散步,我們憧憬著一起讀大學,一起考研,一起畢業,一起工作,再買個屬于我們的房子……我把最珍貴的自己給了他,可后來,我們各自去不同的城市讀書,從一天聯系幾次,到一周聯系幾次,再到一個月聯系幾次,我們連一年都沒走完……我可以一直說下去,所以你說,我們最珍貴的東西到底是什么啊……
小北被長長的講述累得大口呼吸。
是啊,小北說得對。遇見莫青平以前,難道我不是那么癡迷地愛過另一個男人?顧遠方,我已經很久沒想起他了。他像老家的一件舊物,留在了老家遙遠幽深的角落。我遠走他鄉,他永遠被困在那里動彈不得。在廣州,在距離他一千多公里外的地方,很多次被酒精麻醉的時候,他都會閃電般橫亙在我心里,我想打電話問他,有沒有為自己的決定后悔過?哪怕只是一絲一毫地想過,也許她真的很愛自己,該拋棄一切跟她走、抓緊她。
可最終,我一次也沒問過。答案不重要了。
就像一條已經開膛破肚的魚不再需要水一樣。
你呀,真讓人擔心。這是莫青平最常說的。莫青平說,我重新給你找了個光線好的房子,什么都安置妥當了,過兩天幫你搬過去。你身體太差,要多曬太陽,按時吃飯,按時檢查身體,別胡思亂想,我一直在。莫青平摸摸我的頭,拍著我的背。把自己埋進他懷里的時候,你覺得好像所有鮮活的傷口都在慢慢愈合。
陽光鋪滿整個屋子的時候,我做了一串串的千紙鶴門簾,莫青平和我一起做,還說得保護好這些珍貴的小飛鶴,說不定就變成真的鶴飛進我們的夢里。
那天晚上,我和莫青平似乎真的飛進了清澈的云朵里,軟軟的。
3
一個月后,龐宇打電話給我,約了周六早上十點見面,還特意強調他開車接我,我還想說什么,龐宇已掛斷電話。
一晚上輾轉反側,周六早上六點鐘我就醒了。屋子靜悄悄的。所有寂靜化為心間翻滾的不安,一點一點吞噬著我。
起床,一如既往用米黃色面包機烤了兩片全麥面包,煎一個雞蛋,熱一杯牛奶。以前都是莫青平做,他煎溏心蛋是一絕,不像我,每次煎的雞蛋不是太老就是太散。莫青平說,要是沒我,你可怎么辦。
莫青平的聲音風聲般回響在寂靜里。我冷笑。對著做好的早餐毫無食欲。今天,我就要見到莫青平,搞清楚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定得給我一個滿意的答復。
我走進衛生間,洗漱沐浴,迷霧般的水汽里潛伏著白檀雪松香味。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款沐浴露,香味能在皮膚上留存許久,可莫青平除外,哪怕他剛用沐浴露洗完澡出來,我仍聞不到他身上有任何味道。有次,小北留宿我家,剛洗澡出來,我拉起她的胳膊聞,香味清新淡雅。我問小北,為什么莫青平身上沒味道,小北哈哈笑著說,誰讓你找了個沒滋沒味的男人!
記憶漫溢而來。我蹲下,雙手環抱自己,看淺綠色花灑噴出的水串,水在我光滑白皙的皮膚上劃出不同行道。
他不愛我了嗎?所以才不告而別?我那么愛他,難道他一點都感受不到?三個月以來,我第一次迎面朝這個問題撞去。難道我真的不值得被任何人愛?顧遠方也好,莫青平也好,難道他們不過是拿愛情當誘餌誘我上鉤,享受我尚且年輕緊致的肉體,然后心滿意足地轉頭,把整個自己獻祭給生活,再也不顧我內心的荒蕪和絕望?
我哽咽著一遍遍撥開臉上的水流。我想看清楚水是如何從花灑噴涌而出。所有水流都要有出口。幸好我們有眼睛,那些還沒有被過濾的、裹挾著毒物的水流,可以從眼睛千軍萬馬般奔向未知。
陽臺忽然響起烏鴉的啼叫。我起身,裹起米黃色牛奶絨浴巾,走出浴室。一只黑色烏鴉國王般威武地立在陽臺龍須樹枝葉上。對視的瞬間,它再次啼叫。黑色叫聲撲面壓來。我轉身躲進房間化妝換衣服。我沒有勇氣與一只烏鴉對峙。半小時后,我走出房間。那只不知從何而來的烏鴉已不知飛去何處。
換好一套半休閑西裝,我半靠在沙發上等龐宇。十點整,龐宇開著一輛黑色越野車出現在小區樓下。
坐上車,我恨不得馬上詢問莫青平的下落。可從龐宇拒人于千里的表情我猜得出,他不會這么快就說。簡單打招呼后,我不再說話,轉頭看著車窗外快速撤退的一切。
廣州太大,找一個人像大海撈針。莫青平剛消失時,我每天坐許多輛公交車,轉許多趟地鐵,希望一抬頭,就能看見那個熟悉挺拔的背影。我依然看著窗外,像對自己說。語言像沒成熟的蘋果,生澀苦口。我不能再接著說任何一個字。
龐宇左手扶著方向盤,右手胳膊肘搭在中控扶手上。我坐在他的右后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感覺他會說點什么。
感情這事不好說,有時結束就是結束了,我們不得不重新開始。龐宇后頸發根處冒出細微的汗珠。
莫青平從來不出汗。
是的。
你知道?
知道。
莫青平身上沒任何味道。
是的。
你知道?
知道。
莫青平能背很多書。
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
夠了!是的,我什么都知道。一會兒會全部告訴你!
說完,龐宇把車載音樂聲音開大,低沉的男聲娓娓唱著:我是這路上 沒名字的人 我不過 想親手觸摸 彎過腰的每一刻……
我不再說話。靠著后背,閉上眼睛。風從縫隙鉆進我的眼睛和耳朵。耳膜處生疼。
我不知道龐宇要帶我去何處。他是莫青平唯一的朋友,只有他能幫我找到莫青平。
昏昏沉沉間,龐宇停好了車。那是一處不顯眼的郊區獨棟別墅。龐宇輸入大門密碼,引我穿過青灰色亮面大理石走廊,在一間會議室坐定。
喝茶還是咖啡?
不用。莫青平在這里?
那就喝茶吧。
龐宇泡了一杯紅茶遞到我面前,轉身從背后的白色啞光文件柜里取出一沓用回形針歸類整齊的文件,并抽出最底下的一沓推到我面前。
還記得五年前你參與過的一個科技研發試驗嗎?
我木然地翻動著資料,看到文件上自己親筆寫的字:本人自愿參與貴公司任何形式的科技研發試驗,由此產生的任何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擔。
我翻動回憶,試圖找出五年前簽字的那一天。是的,是我簽的。在一場簽售會結束后,在同個場地聽了一場機器人高端研發講座,抑制不住好奇心想參與其中,當場簽了一沓文件。
我雙手緊握細長的玻璃茶杯,手心滲出一層細汗。我想開口說話,可雙唇細微地黏合在一起,我沒法開口。我求助似的望向對面的龐宇。
龐宇微低著頭,時不時看我一眼。
我帶你去看。龐宇起身。胡桃木質凳子在地上刮擦,尖銳刺耳。
我緊握扶手起身,跟在龐宇身后。
通往二樓的樓梯扶手表面光滑,是深色紅木,下面由同色的鐵質材料雕花鏤空。穿過二樓并排而立的房間,龐宇打開了走廊盡頭的紅棕色雙開木門。
光撲面而來,我別過臉。
你看,這些是我們熟悉的,電視電影里常出現,廣州許多酒店、醫院也都投入使用這類機器人。它們的功能簡單,只能完成一些基礎的工作。
見我沒說話,龐宇接著說:這些機器人只是我們研發的初級階段,拿人來打比方,它們就是嬰幼兒階段,會簡單的對話交流,承載不了太復雜的程序和任務。所以我們一直在努力,幫它們長大,也就是我們現階段在研發的高仿真機器人。你應該猜到了。
龐宇試探著走進房間最深處的暗門處,雙手緊握鐵質雙門把。
它在里面。
他在里面。他真的在里面?那個消失了三個月、我足足找了三個月的男人,真的在里面?所有問題在我心里撒潑打滾。
我依然說不出一個字。
龐宇打開門。是的。我看見了……無數個……在白熾燈下閃閃發光的……莫青平。它們以一模一樣的姿勢閉眼低頭站立在偌大的房間。
這批機器人的主要試驗目的是完善機器人情感程序的豐富度和敏感度,所以在投入實驗前,我們針對自愿參與實驗者做了嚴格篩選。一般來說,我們會在它們投入使用一年后召回,召回前設定正常程序,吵架、冷戰、分手、消失。可是,這批機器人在投入使用第六個月時,產生了自主意識。我們無法預測它們的某些行為。比如你參與試驗的009號,開始試圖理解它程序里儲存的知識,甚至開始自主學習人的感情,出現了一些違反程序的行為。這對我們來說存在不可預知的風險,所以臨時召回了這批次的所有機器人。最近幾個月,我在全國各地處理善后事宜。你知道,有的女士很灑脫,會坦然接受被分手的事實,不會找也不會聯系我,但也有和你一樣的,幾個月都沒放棄,最后聯系我。所以,抱歉,我有些不耐煩。處理第一起的時候,我不是這樣的,可后來,慢慢地,我沒法再找回那種狀態。
龐宇的話回蕩在無數個閃亮的莫青平中間。
莫青平是機器人?
莫青平是個活生生的人。我們在全國征集男性志愿者,并通過大數據分析你們這批參與實驗者對男性的喜好,從名字到外形再到性格學識等,選擇與你們配型度最高的人,再以他為原型,制造高仿真機器人。它們的舉手投足、微表情、情感模式、行為模式,等等,我們都盡量以莫青平為原型來制造,最大程度消除它們與人類的細微差別。可你也注意到了,我們依然有很多地方還沒做到,比如皮膚的溫感靈敏度、排汗程序,但這些差別很細微,在大量優點的掩蓋下,大部分人都不會發現。你知道,除了這些細微的地方,其他方面,它們與人類毫無差別,在某些方面,它們還祛除了人類的缺點,比如極端情況下舍棄他人的自保,比如極度勞累下的情緒失衡,再比如親密關系里的過度索取等待。總之,它們是把你們放在第一位的,你們的感受、你們的安全、你們的情感需求,因為它們被設定的就是利他而不是利己。這一切正是我們人類在一段親密關系里最想得到的。我們想在這樣的實驗里完善它們的情感程序。可它們像太過聰明的孩子,成長太快,遠遠超出了我們的可控范圍,所以被迫提前終止了試驗。希望你理解。也非常抱歉。
有一個真的、叫莫青平的男人?
是的。他和你們一樣,也是我們這次實驗的參與者之一。
他在哪里?
抱歉,所有參與實驗的人員信息我們都要嚴格保密。不過,針對這批機器人,我們的研發人員一直在修補程序漏洞,尋找應對它們自主意識的程序,一旦破解這個問題,作為對你們的回報,你們可以把產品帶回家,我們終身質保。
把產品帶回家?終身質保?就像我買的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一樣?我竟然笑了起來。
本質上來說,是的。
哪個是莫青平?哦,不,哪個是009?
龐宇領我走到了第一排最左邊。
這個。
它能說話嗎?
能。
它的程序沒有清空,所以它記得你。
它還認識我?
是的。它還認識你。它的記憶儲存系統沒有被清空。作為參與者,只有你能決定是否要清空。因為這批機器人試驗目的特殊,所以我們要嚴格遵守相關行業規定,為了不侵害實驗者隱私,只讀取其情感處理系統,記憶存儲方面一旦進入就會嚴格違規,簡單來說,就像被黑客入侵時,監督部門會收到警報提醒。所以這次請你來,也是要請您作決定。
說完,龐宇握住它的手,用大拇指按了按它手心。
孔達珍,好久不見!你還好嗎?真擔心你!……
是的,是莫青平……不,它不是莫青平……
我轉身,穿過二樓長長的走廊、順著環形樓梯,跑向停車場。
見面一個月后,龐宇時不時發信息問我是否作好了決定。我不知道他說的決定是指帶莫青平回家還是抹除它的記憶。我沒回復。我不知道怎么回復。
廣州更熱了。很多個傍晚,太陽漸漸隱去,只留層層熱氣包裹人群,我一遍遍踩著熟悉的路走進咖啡館靠窗位置。
窗外多了一群身穿白衣打太極的人。我每天坐在同樣位置,看他們隨琴音出拳收掌。沒什么比空更難對付,哪怕竭盡全力,都沒法把拳頭打在實處。莫青平,你看,這多像我淤積在心口的愛情。
一拳一掌間,時空似乎慢慢折疊,我踩著莫青平在我生活里留下的一個個空洞走回了最開始的地方。
小北問龐宇帶我找到莫青平沒。我說沒有。小北說,啊,他是騙子?我說,不是。小北說,那怎么辦?我說,接著找,總有一天,我會找到莫青平。回復完小北,我給龐宇發了一條信息:當人與物無限接近的時候,人何以為人?物何以為物?如果我們不斷努力,是為了讓人更不愿意與人為伍,那人類的最終出路在哪里?
拉黑了龐宇的所有聯系方式,我開始寫下一本書,書名叫《尋找莫青平》。
責任編輯 丁莉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