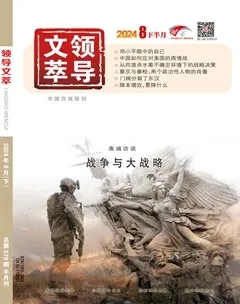蔡京與秦檜:兩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考察歷史人物,甭管是巨公偉人,還是奸佞惡棍,都是可以放到顯微鏡下來觀察透析的“標本”。無論面對的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有必要多問幾個為什么。
“基本盤”
在孟子和荀子之間選邊站,似乎無多少意義。人性本善還是本惡,至今無解,還是需要對具體個案作具體分析。判斷某人是善人還是惡人,還是要看他的“基本盤”。有缺點的戰士與完美的蒼蠅,有本質的不同。偉人可能有陰暗的角落,卑鄙小人也可能有一些亮點。
先說秦檜。他的“基本盤”很清晰——惡人、奸人,臭氣熏天。他的惡名污跡,即便抽干太平洋的海水,也洗刷不掉。僅僅一個冤殺名將岳飛的舉動,就足夠讓他永遠臭下去,直到整個人類在宇宙消失。所謂“不殺士大夫與言事官”的“趙氏家規”,在秦檜執掌朝政時,幾乎蕩然無存。北宋懲治大臣,尚有一塊遮“殺”布,多以貶黜流放為主。秦檜則嫌那塊布太礙事,除了貶放、除名、編管,更大開殺戒。連譽滿朝野、令金人恐懼的大將岳飛也敢殺,那還有誰不敢殺?甚至高宗都恐懼為其所殺。秦檜死后,高宗對楊郡王云:“朕免得膝褲中帶匕首。”此說還有王夫之所記為證:“故高宗置刀靴中以防秦檜。”可見秦檜“奸威”之盛。自秦檜掌權,塞言路,凡有異己者,必下獄治,或流貶,或殺之。秦檜死前,其案幾上有欲誅殺53位官員的文牘,他提筆欲批,手卻握管顫抖不已,“竟不能字”。其妻王氏在屏后搖首曰:“勿勞太師。”“檜尤自力,竟仆于幾,遂伏枕數日而卒。”于是獄事大解,那53人幸免于人頭落地。
蔡京有奸的一面,亦有雄的一面。蔡京的人格構成,遠比秦檜復雜得多,無法以一“奸”統之。宋徽宗不像高宗那樣,對同樣位極太師的蔡京有警懼感。岳飛死后,秦檜在相位十八九年,黨羽遍布朝堂,高宗根本不敢動解除其相位的念頭。而宋徽宗則因天象異變,三次罷掉蔡京相位,待天象正常又恢復其位。蔡京歸來時,宋徽宗常常設盛宴接風,似乎蔡京不是官復原職,而是出征大捷、班師回朝。蔡京遺存的詩文中,有多篇寫皇上宴請的盛況。
蔡京雖然權重,但從未對皇權構成威脅。他與宋徽宗藝術趣味相投,徽宗甚至在內宮專設一閣,收藏了蔡京所有上呈的墨跡。此種特殊待遇,在兩宋藝術家中絕無僅有。蔡京經常在宋徽宗創作或收藏的前人畫作上題跋。他的書法作品,在靖康之難后大部分被毀,或毀于金人戰火,或毀于南宋官方,能夠流傳下來的部分,大多與宋徽宗的藝術交往有關。宋徽宗將王希孟《千里江山圖》轉贈蔡京,蔡京在圖上題了一段話,而今人所知的有關這幅畫的信息,就全部來自蔡京的筆墨。蔡京與宋徽宗還是親家,徽宗女茂德帝姬下嫁蔡京之子蔡鞗。宋徽宗還曾輕車小輦,七次幸臨蔡宅私訪……關系如此親密,家事國事攪成一團,乃至有大臣冒誅殺之險,批評皇上不應如此,以免令百官心寒。蔡京八十歲遭貶逐,已是欽宗登基之后了。
蔡京對蘇軾兄弟及書法家米芾等名士,態度尚算友好,尤其對米芾,算得上予以特別關照了。蘇軾逝于北歸之途時,蔡京尚未登上相位,想迫害蘇軾也沒有機會下手。而蘇轍活了74歲,病逝于政和二年(1112),正是蔡京權高位顯,重拳捶擊元祐黨人之時,但蔡京并未對元祐更化時,曾狠狠彈劾蔡京政治投機的蘇轍施以報復性打擊。蘇轍去世后,其子孫也得到善待。
蔡京與書法大家米芾可稱為摯交。米芾別號“米癲”,是一個有神經質、不拘小節的人。他在雍丘當一個地方小官時,某次出游,竟然將自己下榻的處所裝飾得花里胡哨,自號“天臨殿”。好家伙,真是膽大沒魂了。這天下是誰的天下?除了當今皇上,誰敢自稱“天臨”?此事被巡察官員發現,上奏一本,稱其擅自“創殿立名”。皇上如果知曉了此事,治他個不恭之罪,不掉腦袋,恐怕也要讓其到瘴癘之地“發癲”去,能否活著回來都難說。恰巧奏章落到了任翰林學士的蔡京手中,蔡京將此事壓下,米芾因而躲過一劫。米芾后來官至書畫博士,相當于今日的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也得益于蔡京的舉薦。
蔡京的“奸”名,主要來自靖康之難導致的北宋滅亡。北宋滅亡有其復雜因素,王夫之也不認為蔡京應該為此負主責。《劍橋中國宋代史》既對宋徽宗和蔡京任相時期操控的“崇寧黨禁”給予嚴厲批評,認為“它確實代表著北宋歷史上最為惡毒的黨爭沖突”,也認為“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蔡京毋庸置疑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壟斷了相位,并且開創了一個政治穩定的時代”。蔡京延續王安石變法,推行了許多變革措施,涉及理財、商貿、興學,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因此也不宜用一個“奸名”便將之全盤抹殺。
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此二人政治主張的推行,皆獲得圣意許可、支持。蔡京在第一次被罷相后,“令其黨進言于上,以為京變法度者,皆稟上旨,非私為之。若學校、大樂等數事,皆是紹述神考美意。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秦檜在力主與金和談時,也曾反復征求高宗的意見。紹興八年(1138),當高宗表態接受和議時,秦檜請高宗用三天考慮這個問題。三天過后,高宗表示朕意已定,秦檜請高宗再考慮三天。當高宗再次表態后,秦檜要求讓他全權負責排除一切阻礙和議的干擾。因此,在那時皇帝的眼中,京、檜可不是后人詬罵的“奸臣”。宋徽宗對某些大臣彈劾蔡京表示不理解。秦檜死后,高宗親題神道碑額:“決策元功,精忠全德。”評價之高,堪稱“賢相”了。
漸變與突變
無論是蔡京,還是秦檜,其人格形象都有一個漸進的演變過程。當然,演變達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因某個因素驅動產生突變。
蔡京、蔡卞兄弟皆為飽學之士,同年考中進士。蔡京在學童時,曾把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倒背如流,對憂樂天下的士人境界頗為崇尚。在入仕前,也曾趁蔡襄回鄉省親的機會,倡修木蘭陂,引木蘭溪水改造莆田沿海的鹽堿地,造福于民。蔡京任相,是他人格形象轉變的重要節點。立“元祐黨人碑”,奉行“豐亨豫大”的極端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盛行,皆在他登上宰輔高位時。由此我們可知,權力對人的異化,常常是隱形的,不可抗拒的。
而秦檜的突變,有一個明顯的分界線,那就是南歸(從金人處逃回臨安)之前與之后。靖康元年(1126),當金人軍馬抵達黃河岸邊時,遣使要求割地賠款,舉朝惶恐,有數十人棄官而逃。而秦檜此時上呈奏札《上欽宗論邊機三事》,建言“不宜示怯以蹙削”。當金人欲立張邦昌為傀儡皇帝時,秦檜表示異議,主張應在趙氏家族中選人,可謂有氣節之臣。對于秦檜是如何從金國順利回到南宋,史學界一直有爭議。秦檜自稱是“殺監己者奔舟來歸”,這怕是只有鬼才相信;但說他是金人派遣潛回的內奸,也無直接證據。只能說他的政治主張,在回之前與回來后,發生了180度翻轉。秦檜和其子秦熺,“偽造或消滅了許多關于他(秦檜)在1131—1132年第一次拜相期間的檔案資料”。為了控制私家著書、印刷和公開談論與秦檜主張不同的聲音,秦檜“鼓勵百姓告發那些在他們的私家札記、通信甚至談話中表達反朝廷觀點的人”。御史臺成了秦檜清除所有政敵的工具,他排除異己的手段,比蔡京要兇殘一百倍。這與他做賊心虛,有必然的邏輯關系。
總之,同為“奸”,蔡京之“奸”非秦檜之“奸”,秦檜之“奸”也非蔡京之“奸”——可謂各有其“奸”。
蔡京可能是那個時代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秦檜不是。
秦檜之“黑”,如鍋底的灰,不用手摸,就知道有多黑;蔡京之“黑”,如鍋里的水,是清是濁看上去很模糊,倒出來才知是啥模樣。
(摘自 《文學自由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