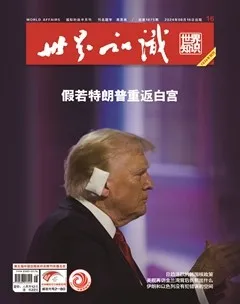“交易式孤立主義”和“美國優先”路徑

孫成昊:特朗普若當選,將秉持傳統右翼理念,在社會層面推行強硬的反移民、高等教育改革等保守主義政策;將提升移民執法部門的作用,可能將部分聯邦執法機構的事務轉移至移民執法機構,派遣國民警衛隊和地方執法部門加快驅逐移民,恢復并擴大針對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等;還將繼續推動民生、教育領域的保守化改革。對外,其將立足于美國自身狹隘利益,持續推動“大國競爭”,但盡可能減少美國被直接卷入沖突的風險,同時繼續熱衷于與盟友伙伴和主要對手搞利益置換——這被《時代周刊》稱為“交易式孤立主義”(transactional isolationism)。
特朗普在黨內千挑萬選選出的競選搭檔詹姆斯·萬斯意識形態極度保守,一些主張甚至比特朗普還極端,他的脫穎而出使得特朗普“交易式孤立主義”的“孤立主義”色彩更加濃重。
一旦“歸來”的特朗普,在內政和外交的關系上仍將是內政優先、“以外養內”,有如他在《時代周刊》訪談中展現的邏輯:“我們談論的是內部的敵人。我認為,在很多情況下,對我們國家來說,內部敵人比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各種外部敵人更危險”,“如果總統是一位優秀、可靠、合適的人選,那么你就不會與中國、俄羅斯或其他國家產生大問題,但我們國家內部的病人仍然會帶來問題。”
特朗普主張通過“美國優先”政策“重振”國家實力,確保美國的領導地位,路徑就是降低或者干脆卸去美國承擔的冗余國際責任與負擔,鎖定“大國競爭”,將戰略資源向“印太”集中,全力對付中國。這一理念背棄了美國在權力與原則之間尋求平衡、兼顧硬軟兩種實力的傳統思路,從狹隘的國家利益角度定義對外戰略。在這種戰略邏輯之下,加之外部國際變局的推動,特朗普二任的對外政策將更加呈現經濟關系安全化、安全關系經濟化的趨勢,反過來也會作用于國際變局,加劇世界的動蕩與不安。

受體制和能力制約,特朗普本人對軍務干預有限,其若重返白宮后不太會對現行防務政策作大的調整,但要賦予其“重建美國軍隊”的旗號,這既包括提升進攻與防衛能力,也包括改善退伍軍人境遇、在禁毒和邊境安全方面加強軍隊與國內執法部門合作等內政屬性的內容。美國的全球防務戰略將體現高度的連續性,繼續推動“大國競爭”成為國際關系主旋律,用“以實力求和平”的原則指導軍隊建設,延續以壓制中俄為主要目標的戰略博弈。為維持美國在軍力上的絕對優勢,特朗普將試圖推動配合“大國競爭”戰略目標的軍兵種改革、恢復海軍長期造艦計劃、加強太空能力建設等。
特朗普及其團隊更多從“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待同盟關系,極力向盟國轉嫁戰略負擔,試圖以“等價交換”的思維提升盟伴承擔的責任,要求回饋美國的“安全保護”甚至反哺美國的經濟發展。特朗普首任威逼北約和韓國、日本等盟友提高國防費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聲稱繳足“保護費”才能從美國獲取安全保護,攪亂了美國的同盟體系。拜登政府上任后立即修補盟友關系,加強跨大西洋聯盟,并且利用烏克蘭危機強化和擴大了北約,禁止退出北約的條文也于2023年底寫入《國防修正案》立法生效。而眾多北約和歐盟國家受到烏克蘭危機的震蕩,積極加強自身防衛,國防費的GDP占比接近達到2%的北約標準,有的甚至超標。近年歐洲、中東、非洲、東北亞、東亞等不同方向上的地區熱點均呈不確定和多變之勢,對美國戰略安全利益構成直接挑戰,美國應付起來捉襟見肘,特朗普若當選,可能會意識到外部協作的重要性,不排除其對盟友伙伴的態度轉趨務實、溫和。
特朗普首任對美國的核政策進行了較大幅度調整,2017年《核態勢評估》報告提出強化非戰略核力量,發展部署多型戰術核武器,發展多層次反導系統等,對今天的東北亞、烏克蘭局勢也產生了影響。拜登政府取消了國際上反對呼聲最高的潛射核巡航導彈計劃,但在其他方面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方向,還大量投資“下一代攔截技術”。特朗普若回歸,將繼續推進其親自定調的大力強化和擴展攻防一體美國核能力的政策,包括擴充戰略核武庫、發展戰術核武器,建造“最先進的下一代導防系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