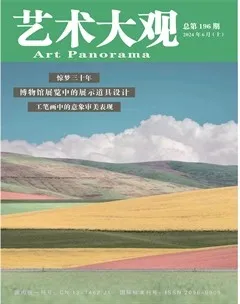走夜路請放聲歌唱
在呼藍別斯,大片的森林,大片的森林,還是大片的森林。馬合沙提說:走夜路要大聲地歌唱!在森林深處,在前面懸崖邊的大石頭下,那個黑乎乎的大東西,說不定就是大棕熊呢。大棕熊在睡覺,馬蹄驚擾到它之前,請大聲歌唱吧!遠遠地,大棕熊就會從睡夢中醒來,它側耳傾聽一會,沉重地起身,一搖一晃走了。一起唱歌吧!大聲地唱,用力地唱,“啊啊~~~”地唱,閉著眼睛,捂著耳朵。胸腔里刮最大的風,嗓子眼開最美的花。唱歌吧!
呼藍別斯,連綿的森林,高處的木屋,洗衣的女孩在河邊草地上晾曬了一大片鮮艷的衣物。你騎馬離開后,她就躺在干凈的,花朵般怒放的衣服間睡覺。一百年都沒有人經過,一百年都沒人慢慢走近她,端詳她的面孔。她一直睡到黑夜,大棕熊也來了,嗅她,繞著她走了一圈又一圈,這時遠遠地有人在星空下唱歌。歌聲越來越近,女孩的睡夢越來越沉。大棕熊眼睛閃閃發光。
夜行的人,你們一遍又一遍地經過了些什么呢?身邊的黑暗中有什么永遠地被你擦肩而過?那個洗衣的少女,不曾被你的歌聲喚醒,不曾在黑暗中抬起臉,草地上支撐起身子,循著歌聲回憶起一切。夜行的人,再唱大聲些吧!唱愛情吧,唱故鄉吧。對著黑暗的左邊唱,對著黑暗的右邊唱,再對著黑暗的前方唱。邊唱邊大聲說:“聽到了嗎?你聽到了嗎?”夜行的人,若你不唱歌的話,不驚醒黑夜的話,就永遠也走不出呼藍別斯了。這重重的森林,這崎嶇纖細的山路,這孤獨疲憊的心。
夜行的人,若你不唱歌的話,你年幼的阿娜爾在后來的清晨里就學不會根據植物的氣息辨認野茶葉和普通的牛草。你年幼的阿娜爾,你珍愛的女兒,就夜夜地哭泣,膽子小,聲音細渺,眼光不敢停留在飛逝的事物上。要是不唱歌的話,阿娜爾多么地可憐啊,一個人坐在森林邊上,聽了又聽,等了又等,哭了又哭。她身邊露珠閃爍,她曾從露珠中打開無數扇通向最微小的世界的門。但是她再也打不開了,你不唱歌了,她一扇門也沒有了!
要是不唱歌的話,木屋門口那個古老的小墳墓,那個七歲小孩的蜷身棲息之處,從此就不會寧靜。那孩子會夜夜來找你,通過你的沉默來找他的母親。那孩子過世了幾十年,當年他的母親下葬他時,安慰他小小的靈魂說:“你我緣分已盡,各自的道路卻還沒有走完,不要留戀這邊了,不要為已經消失的疼痛而悲傷。”……但是,你不唱歌了,你在黑夜里靜悄悄地經過他的骨骸,你突然驚擾到了他,而不是從遠方開始慢慢讓他認出你來。你的面龐黑暗而沉默,他敏感地驚疑起來。他頓時無所適從。
要是不唱歌的話,黑暗中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叫我如何回到呼藍別斯?那么多的路,遍野的森林,起伏的大地。要是不唱歌的話,有再多的木薪也找不到一粒火種,有再長的壽命也得不到一天的松弛與自由。要是不唱歌的話,說不出的話永遠只梗塞在嗓子里,流不出的淚只在心中滴滴懸結堅硬的鐘乳石。
我曾聽過你的歌聲,我在呼藍別斯最高的山上最高的一棵樹上,看到了你唱歌時的樣子,他們喜歡你又嚇唬你,說:“唱歌吧唱歌吧,唱了歌熊就不敢過來了。”你陡然在冷冷的空氣中唱出第一句,像火柴在擦紙上擦了好幾下才“嗤”地引燒一束火苗,你唱了好幾句才捕捉到自己的聲音,你緊緊握住自己的聲音在山野飄蕩。我就站在你路過的最高的樹上,為你四面觀望,愿你此去一路平安。
我也曾作為實實在在的形象聽過你唱歌,還是黑夜,你躺在那里唱著,連木屋屋檐縫隙里緊塞的干苔蘚都復活了,濕潤了,膨脹了,迅速生長,散落著肉眼看不到的,輕盈雪白的孢子雨。你躺在那里唱,突然那么憂傷,我為不能安慰你而感到更為憂傷。我突然也想和你一起唱,卻不敢。于是就在心里大聲地唱,大聲地,直到唱得完全打開了自己為止,直到唱得完全離開了自己為止。然后我的身體沉沉睡去。這樣的夜晚。睡著了仍在唱啊,唱啊,大棕熊你聽到了嗎?大棕熊你快點跑,跑到最深最暗的森林里去,鉆進最深的洞穴里去,把耳朵捂起來,不要把聽到的歌聲再流出去。大棕熊你驚訝吧,你把歌的消息四處散布吧,大棕熊,以歌聲為分界線,讓我們生活得更平靜一些吧,更安穩一些吧。
Ok,親愛的,哪怕后來去到了城市,走夜路時也要大聲地唱歌,像喝醉酒的人一樣無所顧忌。大聲地,讓遠方的大棕熊也聽到了,也靜靜起身為你在遙遠的地方讓路,你發現馬路如此空曠,行人素不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