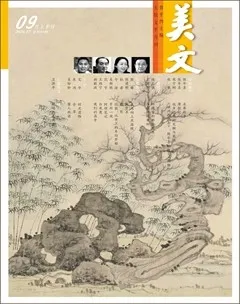故鄉之書的筆觸與筆法
一、故鄉之書
峽河,是陜西70后詩人、作家陳年喜丹鳳老家的一條河。“峽河西流去”,是陳年喜在《南方周末》所開的散文專欄的名字,也是他最新散文集的書名(陳年喜:《峽河西流去》,湖南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中國的河流,絕大多數都是向東流,峽河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在陳年喜的老家,峽河經歷七十里的西流之途,才折向東與丹江匯合,所以,“峽河西流去”并非虛言。
《峽河西流去》是陳年喜的第四部散文集,也是他以故鄉峽河作為書名的第一本書。書名中有故鄉,也有作者對逝者如斯的感嘆,其中含藏著些許無可奈何,卻也不乏事后的豁達——畢竟,作者是歷經生死病苦,并因此而煉就了心胸的。
一如書名所示,《峽河西流去》是部故鄉之書。雖然在此前出版的《活著就是沖天一喊》《微塵》《一地霜白》等幾部散文集中,陳年喜或在零星文字中,或在個別篇章中,也曾多次寫到故鄉,但在《峽河西流去》中,他才以更為細密的筆觸,集中書寫了故鄉。
在該書“自序”中,作者回顧自己的經歷,說“我這半生,和兩個場域扯不斷理還亂,一個是關山萬里的礦山,一個是至今無力抽身的老家峽河”。他的詩歌和散文寫作,也大致從這兩個方面展開。其中,有些文字主要寫礦山生活,有些文字主要寫家鄉山村的生活,許多文字則兩者兼有,只是篇幅多少而已,如作者所說,兩個場域“扯不斷理還亂”。而其所寫,有自己,更多的則是他人。因此才稱得上是一部故鄉之書,而不只是自我之書。
陳年喜從小到大生活在峽河邊的山村,那里有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家、他的根。待他長大成人,需要擔負起養家糊口的重任,而在貧瘠閉塞的農村又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實在沒辦法,才外出打工——尤其是去離家不遠的礦上干活。做工的地點,從離家不遠的伏牛山、靈寶,到愈來愈遠的長白山、鄂爾多斯、山東玲瓏、新疆喀什地區的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接近邊境的地方。可謂天南海北,備嘗苦辛。如此經歷,也并非他獨有,而是與他一樣的一代乃至幾代山村青壯勞力所共有的。仿佛共同的腳本,不同的只是細節。陳年喜的經歷固然豐富、傳奇,甚至不乏悲苦,與他一樣外出打工的鄉鄰們,進而在中國大地上上億的外出務工者們所經歷的,又何嘗不是如此?甚至有人為此搭上了生命,或者犧牲了身體的一部分,導致不同程度的工傷或殘疾,鮮有人能全身而退——陳年喜犧牲的則是頸椎和肺。
天南地北的打工生涯并非單純的離家、離鄉,在另一個空間場域中展開生活。毋寧說,那里沒有生活,只有工作和休息間隙。對于千千萬萬的打工者來說,打工生活算不得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在另一頭的家鄉,在一家人的團聚,在日復一日的家長里短和煙火中,雖然外出打工的生活,從時間上來說遠遠多于在家。
也因此,他們走得再遠,也不可能不回頭反顧。陳年喜也一樣,他心系著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一次次拉扯他回到家鄉:孩子出生、父母生病、鄉鄰去世……更不用說逢年過節,能回家的時候總是要回家。即使平時回不了家,也要通過書信、電話與家中聯系。于是,在家鄉與打工地之間,就拉扯起更為繁復的情感牽系。
不過,雖然打工的時候常年離鄉,切膚的生活經歷,卻并沒有讓作者對家鄉產生牧歌或鄉愿式的美好想象與回憶——這是很多早年生活在農村,后來通過讀書而在城市中落腳的人們常會在文字中展露的傾向,實際上也是虛假的傾向,并因其虛假而使得他們地寫作變得無效。
身為農民而又不得不成為“(農)民工”的陳年喜,沒有奢侈和浪漫的機會,沒有對家鄉產生那種鄉愿式的顧念。他清楚地記得小時候的事,記得在農村時做義工、“大會戰”,記得鄉村生活中的質樸與狡黠、互助與計較、溫情與緊張……記得幾代人為什么背井離鄉外出打工。但他寬容、豁達,并不苛責個體,而是對過往的人與事,都抱以回望和理解的釋然。(《1998年的鄉村逸事》)
當然,在這釋然里,也有無奈、嘆息和徒然的觀望。尤其是隨著人口的流失,鄉村無可挽回地衰敗。一如農村里曾經熱鬧的年戲,已多年不再上演(《年戲》)。就此來說,陳年喜的散文和詩歌寫作,其中相當分量,是他生于斯長于斯、他的父輩們生于斯葬于斯的鄉村幾十年的發展與衰落史。包括作者寫到的從鄉居到城鎮的過渡(《村居現狀憂思錄》),它的復雜,以及作者對它難以割舍的眷戀:“打工生涯里,我見過數不清的野棉花,在北疆,在青海,在風沙漫天的毛烏素邊緣,夏天它們是花,秋天它們是棉,但西溝嶺上的野棉花,是最壯觀的、最溫暖的。”(《摩托記》)這些文字,可說是“月是故鄉明”的當代版注釋。
不過,陳年喜并沒有因此而美化鄉村,同樣重要的是,他沒有在文字中“賣慘”,而是通過清簡疏朗的文字,寫下略帶傷感的真實記錄。就此來說,陳年喜的鄉村書寫與此前梁鴻、黃燈等人的鄉村書寫一起,構成了新世紀以來,尤其最近十余年以來關于鄉村的新圖貌,也為我們理解當下的中國農村,提供了真實可信、切實可依、清朗可讀的非虛構文學文本。
二、人事風物
書寫鄉村,必然會寫到鄉村中生活的人。這些人在鄉村中生,于鄉村中死,鄉村養活他們,也在貧瘠無告中將他們推向外面的世界。
的確,陳年喜在散文中寫了很多人,他所認識、接觸抑或聽說的人與事,從親人、鄉鄰,到工友、老板,不僅寫他們生命歷程中的一瞬,更寫他們長達幾十年的生活經歷,乃至命運,哪怕只是寥寥數筆。
包括他的父親、叔伯在內的上一輩,由于社會環境的限制,他們大都在山村中度過貧苦、不起眼的一生,至多出過幾趟遠門,一輩子都在家門口周圍方圓幾十里地中打轉;他的同輩人,則由于時過境轉,社會環境的寬松,多外出打工,如他所寫:“這些年,村里一半的年輕人都上了礦山,他們星星一樣撒落在秦嶺、長白山、祁連山、賀蘭山脈,或者大河之側。”(《峽河七十里》)除了打工、下礦井,山村里的年輕人實在沒有多少別的出路。如此選擇,其實也是生活所迫,陳年喜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走過很多地方,經歷不少人事。其中,最令人觸目、想起來叫人發怵的,就是礦工生涯的艱辛與兇險,以及看似平常的生活中的無常。
某種程度上說,在礦上討生活,就是與死神對弈。對于在礦上干活的普通民工,命運的殘酷與叵測,時時縈繞左右。有的因為意外當時就命喪礦井,有的則在多年超負荷、無保護的條件下勞動之后患病(尤其塵肺病),長期與病痛相伴,并最終因病而逝。如此情形,不僅對于在井下工作的人,即便對那些從事井上工作的人來說,也極為常見,正如他在散文中所寫的機師傅(《人們叫我機師傅》)和劉師傅(《煙塵》)們;哪怕從事礦石粗加工并大賺了一筆的小老板們,往往也難以幸免,即使曾經日進斗金一時暴富,到頭來也難逃病苦以及隨之而來的生之艱難(《我的朋友周大明》)。
就此來說,陳年喜所寫的無論關于礦井還是關于故鄉的文字,都是在寫底層百姓的艱辛與小慶幸,悲苦與小確幸。散布于這些人事命運中的,更多是流離與漂泊。正如他在第一部詩集《炸裂志》的“后記”中所寫,“這是一部漂泊的詩(集)”。他通過詩文所記錄的,既是一個人的漂泊,也是一群人、一代人乃至幾代人流離、漂泊討生活的經歷。
陳年喜的筆觸并不全是寫人事,他也寫家鄉獨具特色的風物,如蘆花、桐子、蘑菇、葫蘆、漆樹、苕(山藥)、疙瘩葉兒……只是,這些對山鄉土特品物的書寫,要么也伴隨著對人事或多或少的書寫(如《苕》《年戲》等),要么就是以寫這些品物為引子,引出與之相關的人事(如《葫蘆記》《割漆的人》等)。
如《年戲》,由寫山村里春節前后唱年戲而寫到參與年戲順利演出的若干人,以及他們在時光中的老去,同時,也寫到故鄉河邊常見的蘆花——“峽河邊上,兩岸無邊的蘆花,熬過了冬天,正往春天里白”。文章結尾,作者再次提到蘆花,并將蘆花比作另一場年戲:
我已經三個月沒有回過老家了。
車進峽河,天已黑透了。車燈打起來,明亮的光柱在山邊、河邊劃動。枯水季節,河里幾乎沒有什么水,只有在有落差的地方還能聽到水聲。河床寬寬窄窄,九曲十彎,白茫茫的東西充滿其間,因勢就形,它們豐盈浩蕩,搖旗吶喊,前不見所始,后不見所終,那是蘆花。
只有蘆花還在。它無意見證什么,卻見證了所有,它無意說出什么,卻說出了一切。它見證了一位少年到中年的歷程,見證了年戲從興到衰的光影。
蘆花年年到天涯,那是另一場鄉戲和年戲,它高歌蒼壯,細柔溫婉,沿長江一直唱到大海,唱給風聽,唱給水聽,唱給天地聽。
這里,白茫茫的蘆花既是無盡的見證與訴說,又仿佛是離鄉之人的化身,替他們守著鄉村,此外也更像是對人們離鄉之后日益衰敗的鄉村的祭挽。在《割漆的人》等篇中,作者在書寫風物的同時,用不多的文字將筆觸延伸到人事,甚至達到令人揪心的程度。
讀陳年喜所寫的這些有關人事及其命運的非虛構散文,不免會感到沉重。然而,陳年喜并非要刻意這樣寫、刻意追求這樣效果的。正如他所言:“不是我要寫得沉重,是我經歷的生活、經見的人生本來如此。”(《表弟故事》)對于一個身處社會底層、年過半百的農民作者來說,這就是他——以及他們——在幾十年的生活中所經歷的,只是由于真實,而令缺少這些經歷的人們讀來感到唏噓,甚至不可思議。
三、春秋筆法
陳年喜的散文,在寫法上也很有特點。他的文字清明流暢,在寫法上,常大開大合,有限的文字里,蘊含著巨大的信息量,比如寫離家出門干活,一路上“車過石門、吊蓬、靈口、犁泥河、小河,最后到達楊寨峪金礦坑口”(《摩托記》),僅用十幾個字,就勾勒出所走過的路線,既為文章打開遼闊的空間,也為讀者撐起廣闊的想象空間。比如寫時間,“霜露荏苒,日月如捐,一晃二十一年過去了”(《1998年的鄉村逸事》),也是在短短一句話里,打開二十一年的時間跨度,打開從現在通往過去的通道,展開關于過去的敘事。不僅如此,作者有意識地避開“光陰荏苒”“歲月如捐”這樣人們耳熟能詳的成語、熟語,對其加以精心改造,使文字顯出陌生化、個性化的效果。
陳年喜的文字也常含幽默。《表弟故事》寫自己年輕時與表弟一起玩獵槍,“那時候,我們都還沒有討到老婆,不過,也并不為討不到老婆發愁,一則是村里遍地都是大姑娘,那會兒還沒有打工潮和大學潮,人生都沒有選擇余地,像野桃花兒一樣,再好的顏色都開在山上,凋在山上;二則是我們有獵槍,對于我們兩個光棍,那是比愛情更美好的快樂。我們倆常常背著槍游蕩在山林間,如兩個響馬”。這段文字既是很好的歷史敘事,真實過往與現實的寫照,又充滿幽默與戲謔,使原本有些嚴肅和沉重的敘事,表現出活潑與彈性。這種敘事方式是漢語敘事中非常稀缺的質素。
陳年喜的文字注重敘事,很少抒情,更不煽情,很懂得以少為多、點到為止的藝術。有論者指出陳年喜的散文“動用了小說寫作手法”,有“小說體散文”的特征(武歆:《微塵·序》)。的確,陳年喜散文中的好些篇章,讀來都有懸念,個別篇目,如《葫蘆記》《割漆的人》等,不僅可以當小說看,更可以看作是他無意中延伸、拓展了散文和小說寫作邊界。
在一些小說性不那么強的篇目中,他也借用小說的寫法,比如《年戲》中,由寫汽燈而寫到點燈的老李:
點汽燈也是個技術活,不是人人會點,一晚上,兩只汽燈,要燒不少煤油,點得好,省油又明亮,點不好,費油又昏沉。村里,只有老李點得好,所以汽燈用的時候,由老李來點燈,不用的時候,就由老李來保管。老李個子矮,平時人們喊他老李,也有人喊他矮子的,只有到了用汽燈時,人們才喊他燈師傅。老李一年的高光時刻不多,有些年景三四回,有些年景一兩回,老李每年定數的一回,就是唱年戲時。老李平時難得被人當人,只有點汽燈時,才被人當人,老李這時也把自己當人一回,必須和演員們吃住在一起,戲開演,他也不坐臺下,一定得坐兩邊廂臺上,不知道的,以為這人是劇務,或者導演。
這段關于老李的文字,就很有小說的特點,或說小說的筆致。
僅看題目《苕》,以為是寫故鄉植物的散文,也由苕而寫到挖苕,寫到挖苕的人——“我”和兔:
那時候,經常和我結伴上山挖苕的,有一個叫兔的女孩。兔嬌小,兩只眼睛圓、怯,見人躲閃。兔沒有哥哥,有一個弟弟,弟弟小、弱,三歲了還不會走路。兔除了上學、做家務,就是帶弟弟。我手腳并用地攀到崖頂上,褲帶上別一桿小鋤,她在下面渾身顫抖,捧個簍,一會兒喊,哥,小心點;一會兒又喊,哥,慢點。聲音細細的,茸茸的,像兔毛,白而柔,往人心上蹭。如果巖坎光滑,鋤就失去了用場,兩手抓住草窠用力一揭,黑乎乎的土層下,苕一下就亮了出來,根根盤繞,竟有胳膊粗壯的。抖凈了土,苕毫發無傷,收獲了。并不是每次攀上崖都能見到苕,也并非每次都那么幸運,挖到完好的苕。下山,多是在夕陽壓巔時,我荷鋤,兔背簍,歡天喜地。見人,兔子都會送上一根,好像我們是天下最富有的人。
這里關于名叫兔的女孩的書寫,同樣以小說的筆調,寫出她女孩兒的心性、令人生憐的個性,以及她內在的良善,讀來令人動容。
此外,陳年喜還在其散文中寫了不少堪稱傳奇的事。《絕活》中寫父親有一手絕活:看棺斷生死。所謂看棺斷生死,“是根據打棺工作第一斧頭下去木屑廢除的方向和遠近”來判斷受用者的壽數。比如在給一個生病的人做棺材時,第一斧下去,“一片木屑子彈一樣嗚一聲飛起來,它飛向墻壁,在墻壁上撞擊了一下折返到另一個方向,它飛過眾人頭頂,氣勢兇猛,最后輕輕落在地上”。父親由此判斷,這個生病的人沒有福分用這個棺材。果不其然,后來這個棺材被這個人最小的女兒給用了。再比如,有一年村里有人在山西礦上干活,據說出了事,作者被安排和村里幾個人一起“過黃河領取尸骨和談判”,負責在家里打棺材的父親則說,“人回不回得來還不一定”。最后,果然死不見尸。這些故事讀來,都令人咋舌,感嘆其傳奇色彩。而傳奇,既是小說的前身,也至今還是小說的基本方式之一。
《摩托記》中寫作者在藏區礦上工作,晾著的褲子被牦牛吃了。“我一怒之下,拿起一根釬桿,沖向它們,它們不敢對抗我手里的鐵棍,四散而逃。……這時候,一輛摩托車風一樣停在我面前,一個彪悍的人,騎一輛彪悍的摩托車。……事情的結果是他答應賠我一條褲子,并請我到鎮上喝酒。……他說我是一條漢子……”這樣不打不相識、繼而成為朋友的經歷,同樣帶有小說式的傳奇色彩。后來,在這位名叫瑪旺的藏族青年決定離開家去外面的世界闖蕩時,將這輛黑色雅馬哈勁虎150摩托車送給了“我”。其豪邁與義氣,也一樣具有小說式的傳奇色彩。
更不用說像《表弟故事》中那樣草蛇灰線,布滿謎網的敘事——劉大發給表弟看的有關金礦石的化驗單是否為真?如果不是,他為什么要那么做?表弟后來怎樣了?劉大發在病床上說,這件事他“到死也不會說”,結果第二天天亮時,他就病逝了……讀來不僅懸疑,甚至有點幽森詭異之感。
這些寫法,都大大增加了陳年喜散文的可讀性,也極大地吸引了讀者。
四、結語
關于故鄉的風物人事,陳年喜懷著克制的情感寫了很多。他說:“寫作,也是思鄉者與故鄉彼此走近相看的過程。”(《峽河西流去·自序》)在這“相看的過程”中,有些事物看得更清楚,有些則由于久視而更加含混不定。即便如此也是值得的,甚或說更值得,因為世上的很多事都難以簡單地分作黑白,在模糊中看到更多的灰色與難解,何嘗不是一種認識的深入、認知的提升,甚至更大的收獲?
陳年喜還說,自己“不過是個寫信的人,我以文字歌哭、悲喜,以晨起暮歇的有用無用功為世界、為人們、為看見和看不見的事物寫信,又以同樣或不同的方式接收來信”(《峽河西流去·自序》)。其實,作為讀者,我們同樣也是收信人,所收到的不僅是來自包括陳年喜在內的作家們的“來信”,更是他們的文字從我們心底喚起的種種情感、記憶與想象。換言之,我們通過作家們的文字最終收到的,是我們的感受、理解與思想,是我們內心的激蕩、回應與呼聲。而這,也是文學閱讀最重要的意義之所在。
(責任編輯: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