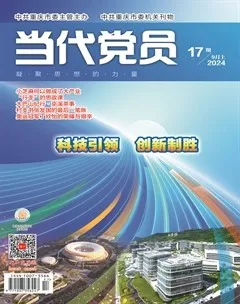村支書張發國的最后一筆賬


翻開有些破舊的筆記本,記錄的最后一頁,只有簡單四行字——
“2024年8月13日秋月梨銷售:張述典,20斤,160元;陳恢江,37.5斤,300元;簡包裝,8箱,544元。”
共計1004元,這筆賬不多,但筆記本的主人,時任重慶市巫山縣廟宇鎮南溪村黨支部書記的張發國很高興。
秋月梨是南溪村今年剛發展的集體經濟產業,當下正是大量上市的季節,將梨推廣銷售出去,是張發國最近一段時間最忙的事。
眼看梨越賣越好,張發國卻倒下了。
8月18日上午10時,今年51歲的張發國,生命永遠定格在鄉村振興一線。
沒賣完的梨
站在南溪村黨群服務中心門前遠眺,綿延的大山裹挾著廣袤的平地,各式農舍四散在成片的稻田間,很美。
但看上去很美的地方,發展得卻很慢。
廟宇鎮是巫山縣萬畝糧倉之地,盛產優質大米。南溪村也占地利,1700余畝耕地中水稻種植面積達780畝。“但村子沒啥產業,青壯年外出務工日益增多,本是糧倉之地的南溪村越來越缺乏勞動力,以至發展滯后。”巫山縣委宣傳部派駐南溪村第一書記易洪剛說。
2017年,土生土長的村民張發國任南溪村黨支部書記。南溪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張發國一直在苦苦尋找。
這些年,為發展村集體經濟,張發國帶著村干部想了很多辦法。他們先是依托豐富的光熱資源優勢,引進光伏發電項目,每年為村集體創收1萬多元;而后把村里50余畝閑置的水稻田流轉給鄉村振興集團,每年為村集體增收3萬多元;后來利用閑置土地引進煙薯種植項目,不承想以失敗告終,今年又因地制宜種植黃豆……
發展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提升農村生產力和農民收入的關鍵途徑,是張發國心中最重要的大事。找不到發展村集體經濟的有效突破口,讓他憂心不已。
“他總是對我說,為了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我們要想方設法,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南溪村黨支部副書記陳恢虎含淚說道,“他工資卡里僅有的4000元都墊付在務工群眾的工錢里了。”
“只要一有時間,他就會和駐村工作隊的干部一起琢磨發展村集體經濟的點子。”易洪剛回憶。
轉機出現在今年初。
與南溪村鄰近的廟宇鎮長梁村在大力發展秋月梨產業的同時,也琢磨著壯大水稻產業。張發國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和村“兩委”及駐村工作隊商討后,和長梁村、永安村、廟宇村3個水田最多的鄰近村商量著共建農產品加工廠,聯合發展村集體經濟。
6月,由4個村聯合創辦的巫山廟宇鎮金稻糧源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成立。8月8日,隨著800畝秋月梨上市,公司正式營業。
公司秋月梨的產量預計在2.5萬公斤左右,為打開秋月梨的銷路,盡可能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除了線上銷售,4個村也沒有放棄線下售賣。大家一致決定,賣梨期間,每村都出一人牽頭銷售,張發國就是其中之一,負責到巫山縣城摩天嶺小區售賣。
秋月梨香甜可口,細嫩化渣,較受歡迎,大家都憋著一股勁,打算賣完梨就收割稻谷賣大米,大干一場。
張發國深知自己村里沒什么拿得出手的產業,這次發展的村集體經濟主要是“借別人的雞生自己的蛋”,所以自己能有多大勁兒就出多大力。也就是從8月8日開始,他開始了每天凌晨四五點出門賣梨、晚上九十點才忙完回家的行程。這段時間,張發國不是在賣梨,就是在賣梨的路上。
倒下前,張發國打了三通電話,第一通是打給長梁村黨支部書記許生的。
“又是商量賣梨的事情。”許生說,張發國因為要調解村民矛盾,跟他招呼第二天不能到摩天嶺賣梨了。
第二通電話是打給永安村黨支部書記張述典的,打了兩次。
“第一次,他告訴我第二天不能到摩天嶺賣梨了,他協調讓南溪村的會計去。第二次,他說會計的車壞了,不方便去,等忙完他就親自去。”
張發國最終沒能賣完秋月梨,離世時,他的指甲縫里沾滿了梨漿。
梨不等人,800畝越發成熟的秋月梨等著采摘送往市場。那堅實的果筐,終將裝完數萬斤香甜的梨,卻永遠裝不下一顆一心為村民謀發展的心。
沒吃完的藥
“我最近有點暈,可能是中暑了。”
“那你注意點,趕緊去醫院檢查一下。”
“現在正是賣梨子的旺季,不能耽擱,等我忙完就去。”
這是8月以來,張發國生前與同事、家人最多的對話。
8月15日,身體實在扛不住了,張發國抽空去醫院做了腦部CT檢查,結果顯示有輕微的血栓,醫生囑咐他要注意休息。心里牽掛著賣梨的事,張發國在醫院買了些藥就匆匆回村了。
8月17日上午9時許,張發國的母親丁時秀發現兒子沒去上班。
“按照平常,這個點他早就在村里忙工作了,今兒怎么還沒開門?車也還在門口。”察覺異常,丁時秀連喊幾聲,得不到回應的她透過窗戶往里看,只見兒子四肢僵直,斜橫在床上,沒了反應。
“快來啊!發國不行了!”丁時秀哭喊道。
村民從四面八方飛奔而來,破門、砸窗、送往醫院、搶救……遺憾的是,張發國的心跳還是于18日上午10時停止了跳動,那一大袋才開始吃的藥,還安然擺在臥室里。
沒吃完的藥,沒忙完的事業。
在南溪村黨群服務中心的會議室里,擺著一份文件,是2024年巫山縣社情民意調查中心對全縣26個鄉鎮(街道)340個村(社區)開展的第二季度滿意度調查結果。結果顯示,南溪村排在第160位,綜合得分94.10分。
排名不算靠前,得分也不算高,但要整改的問題,只有兩個:一個是村民飲水問題,一個是道路交通問題。
事實上,張發國一直為村子的發展奔忙著。
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發展的重要環節,完善的基礎設施不僅可以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還能為發展村集體經濟提供堅實的基礎。
過去,南溪村水資源匱乏,極大地限制了村民的生產生活用水,如今,全村27口水塘通淤儲水;過去,南溪村的路既狹窄又崎嶇,村民出行、產品流通十分不便,而今,村里實現了村村通、組組通、戶戶通,道路交通得到極大改善。但張發國深知村民還有更美好的期待,離世前還心心念念著南溪村的道路擴建問題和飲水灌溉問題,多次就此跟陳恢虎探討方案,“想盡辦法滿足大家的期待”。
南溪村經濟底子薄弱,要帶領2300余名村民致富,談何容易。張發國意識到,村子要發展,必須注入有頭腦有想法的年輕血液。
2021年,張發國向廟宇鎮黨委、政府請示后,幾次電話深談和邀請,將大學剛畢業的龔文踩作為本土人才引回了南溪村。龔文踩雖生在南溪村、長在南溪村,但并不懂農村工作如何開展,為讓龔文踩扎根南溪村,無論是調解矛盾糾紛,還是開展其他各項工作,張發國都會帶著龔文踩,讓他快速學習成長。
3年過去,當初對農村工作一竅不通的龔文踩,已能獨當一面,成為南溪村的綜合治理專職干部。“最近兩個月,他一直謀劃著推舉我去學習操作無人機、駕駛耕作機等農業技能,以服務村子的產業發展。”龔文踩說。
沒說完的話
每天晚上10時多,張發國會和分隔兩地的妻子何艷互通電話或微信聯系。
張發國上有患病的八旬父母,下有待業的閨女和正在上學的兒子,家庭經濟負擔十分重,僅靠務農和工資收入,難以維持家庭生計。為讓丈夫安心工作,2019年起,夫妻倆開始分隔兩地,何艷在重慶主城進廠務工,以補貼家用。
張發國此生最后一通電話,就是打給何艷的,但那天工作太累的何艷并沒有接到。
“我真后悔啊。”這份鉆心的遺憾,讓何艷悲痛欲絕。
那天,張發國想跟妻子說些什么呢?
一定有村子的大凡小事。
張發國的父親張家倫,曾在南溪村當了38年的村黨支部書記。張發國當選村黨支部書記后,張家倫對兒子千叮嚀萬囑咐,“做農村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心的工作,不然就‘擱不平’!”
8年來,張發國一直牢記父親的話,心里始終記掛著村民的冷暖安危,村里的大事小事、家長里短,都了如指掌。
或許有工作的酸甜苦辣。
南溪村的事,再小的事對張發國來說都是天大的事,他的悲喜,大多與南溪村相關。
今年4月,村民吳世春被查出患肺癌,妻子又身有殘疾,家庭難以為繼,這讓張發國十分憂心,他四處奔波為吳世春家辦理低保的申請手續。
5組到6組、7組的機耕道擴建涉及20戶村民,因為修路存在不少矛盾糾紛,這讓張發國揪心不已。這些年,張發國反復調解,最近終于讓問題基本得到化解。
村民龔文清家十分困難,但一直對生活充滿希望,種植了大片水稻增加收入。4年來,張發國時常探望龔文清一家,并幫忙銷售大米數千公斤。眼下水稻即將豐收,龔文清又請求張發國幫忙銷售,張發國十分欣慰……
或許有生活的向往。
這些年,忙于村民的事,張發國和家人聚少離多。即便一家人好不容易聚齊,張發國也總是大清早就出門奔波,天黑才回家。
“我們很理解他,一直很支持他的工作。”兒子張杰、女兒張雪蓮哽咽道。
張發國有個心愿,待到兒女成家立業時,他能閑下來,幫兒女帶孩子,一家人好好在一起。
那一天,張發國等不到了。
“你怎么舍得撇下南溪村,撇下我們啊。”何艷痛哭道。
驚聞張發國離世的消息,村民都很悲痛。
“張書記在我心中是位能干、肯干的好書記。村民事多,常常在微信群發些為難之事,張書記看到后都會盡力排憂解難。”
“細數張伯伯的一生,沒有豪言壯語,沒有豐功偉績。我一直在想,作為一名最基層的黨員,他的心到底有多大,裝得下群眾,裝得下親情鄰里。”
“南溪村的好支書,基層的好干部!張書記用生命詮釋責任和擔當,生命雖短,但他拓寬了生命的厚度,可泣可敬。”
……
張發國走后的第三天,吳世春一個人來到張發國的墓前深鞠三躬:“張書記,你是位好書記,我打心底感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