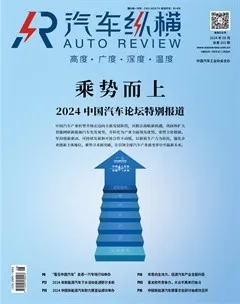中國汽車芯片如何攀“高”向“新”

7月13日上午,業內重磅專家、汽車芯片各細分領域企業代表齊聚2024中國汽車論壇的主題論壇現場,圍繞“汽車芯片高質量發展,鞏固智能網聯新優勢”展開交流分享。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李邵華、中國一汽研發總院智能網聯開發院院長王仕偉、工信部電子五所元器件與材料研究院高級副院長羅道軍、國家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中心技術標準化部部長吳倩、北京經緯恒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電子研發院總裁辦所長王會蘋、上海智能汽車軟件園總經理李成蹊、黑芝麻智能產品副總裁丁丁、無錫英迪芯微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市場總監莊吉、湖北芯擎科技有限公司副總裁兼產品規劃部總經理蔣漢平和長城資本上海區總經理貢璽在論壇上發表了精彩演講。本場論壇由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楊中平主持,為汽車與芯片及相關產業搭建開放、合作、共享的交流平臺,圍繞汽車芯片的技術創新、產業鏈構建、市場需求與趨勢等議題展開深入討論,分享前沿成果,探討合作機遇。
整體短缺趨緩,市場需求猛漲
“過去我們曾面臨芯片短缺的嚴峻挑戰,深刻認識到芯片對于汽車產業的重要性,當前階段(重點)已經從芯片短缺、整芯融合發展轉到芯片的高質量發展上,短缺趨于緩和。”王仕偉指出,面對新能源智能網聯汽車的下半場,數據、算法、算力這3大引擎最關鍵的技術底座就是芯片。
當前,汽車產業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新能源汽車的崛起、智能網聯技術的飛速發展,正深刻改變著汽車的屬性與未來。在這一轉型的關鍵時刻,汽車芯片作為智能網聯汽車的“大腦”與“心臟”,其重要性日益凸顯。它不僅關乎車輛的性能、安全,更是決定汽車智能化、網聯化水平的關鍵因素。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李邵華表示,推動汽車芯片的高質量發展,對于鞏固我國新能源、智能網聯汽車的新優勢,促進汽車產業轉型升級,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新的電子電氣架構不僅帶來了汽車芯片巨大的市場需求,同時也牽動產品升級和供應鏈重塑。
王會蘋表示,這種需求不僅體現為“量”的不斷增長,多樣性也在增加,如通信類、控制器類、計算類包括功率類的芯片需求均在增多。
王仕偉以企業各代車型為例介紹說,在上一代電子電氣架構中,芯片數量在300—500顆不等,如上一代電子電氣架構的紅旗H5應用芯片約400顆,但E-HS9作為新能源汽車,整車應用芯片已超過1000顆。王仕偉還透露,單車芯片成本價值原來大概3000-5000元,現在搭載城市NOA的已達到萬元甚至更高的水平。
當前,智能電動汽車的快速發展,也給不少傳統零部件帶來變革新機遇,車燈便是其中之一。據莊吉介紹,如今終端用戶對車燈的功能訴求,早已不僅局限于簡單照明和信號指示,而是追求功能的多樣性、智能化,甚至與智能駕駛、智能座艙等復雜系統深度融合,由此帶來了大量的芯片需求。
隨著高階智駕技術的不斷突破、L2級智能駕駛滲透率的持續提升,從技術趨勢看,蔣漢平表示,從艙泊一體、艙駕一體再到艙行泊一體,這些都將成為汽車的標配,這對芯片提出了更高制程、更強異構算力、更可靠車規特性的要求。
結構短缺仍在,內外挑戰重重
盡管市場空間廣闊,整體性短缺已經緩解,但國產汽車芯片仍面臨不少問題與挑戰。
從技術層面看,原來電子電氣架構是以微控芯片為主導的分布式控制,而現在向以高性能為核心的中央計算平臺和域控發展,這對每個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在整車廠都在做SOA架構,進行控制器集成,芯片用量不減反增。如何進一步讓服務集中化、控制器集中化,成為行業對芯片的新需求。而且目前自動CC73XmI+Yw+qmkFe4gOY5w==駕駛每增加一級,對芯片算力的需求呈指數級的增加(10倍以上增加算力需求)。王仕偉指出,現在汽車行業在生產時進行硬件預埋,通過軟件OTA升級提供服務,這對芯片、對算力、對功耗、對成本、對數據傳輸的效率安全等各方面要求都呈指數級增長,車規級芯片的集成度、工藝制程、兼容算法的復雜度快速上升。
從產品開發應用層面看,丁丁指出,在中國市場,智能化大芯片、域控都面臨一個問題,即裝配率沒有明顯提高,整體可應用落地的車輛并不多,對芯片廠而言整體很難上量。
而且,對于整車廠、Tier1來說,平臺開發周期越來越短,投入卻很大,一代平臺可能兩年就要淘汰,整個平臺又要大規模投入。丁丁透露,汽車芯片周期和芯片域控開發周期不是特別匹配,整體車輛功能迭代的周期也越來越快。如何讓投入對整車廠有持續幫助,也是汽車芯片企業在思考的問題。
從產品結構層面看,“目前自主可控的汽車芯片很少,真正做到從設計制造到封測完全自主可控的目前不到三成,而且都是偏向低端的MCU或者存儲類的芯片,在高端芯片領域對于跨國公司的依賴度非常高。”王仕偉坦言,今年以來,汽車芯片由全類型的短缺已經轉變為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短缺,尤其是隨著歐洲、美國、日本出臺了一些芯片相關的法案,高端芯片的發展受到很大制約。
“結構性短缺,國產高端芯片缺乏,低端過剩。”據羅道軍介紹,車規級芯片目前的自給率不到10%。
在汽車芯片產品的可靠性方面,羅道軍一針見血地指出,目前從工作數據積累來看,國產芯片在質量一致性、工藝穩定性和工藝適應性方面,包括可靠性等方面,和國外先進制程、擁有幾十年積累的汽車芯片公司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
國產芯片研制歷史周期短,經驗和應用履歷不足,“不好用”主要是因為固有風險大、多,存在批次性風險。深究下去,“用不好”是應用的支撐數據少、應用履歷少,“不敢用”是不知道風險在哪里。
在介紹國產汽車芯片產品可靠性時,羅道軍特別區分了“合格”與“可靠”。他強調,“合格”的并一定不代表可靠,合格測試只是按照標準來做,不是測試合格就可靠。而芯片的可靠性包括固有可靠性和應用可靠性。可靠性是與時間有關系的質量要素,經得起時間檢驗的質量才叫可靠。
在工藝層面上,貢璽根據其長期調研的信息指出,我們在很多芯片工藝上有不少被卡脖子的點,其程度也必須引起重視。
從產業發展的宏觀層面看,李邵華指出,當前國際形勢日趨復雜嚴峻,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的變化使得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明顯增強,我國半導體產業面臨更多風險。建設較完備的汽車芯片產業體系,對汽車數字化進程中的數據安全、網絡安全、信息安全和供應鏈安全等方面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雖然中國汽車芯片產業存在技術積累與創新能力不足、產業鏈協同與生態建設滯后、人才與資金投入不足、市場接受度與品牌影響力有限等多重問題,但正是這些問題和挑戰,激發了我們不斷創新的動力,也促使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共謀發展大計。
如何攀“高”向“新”,各方建言獻策
車規級芯片高質量發展,是實現我國汽車產業、汽車芯片產業自主可控,實施“制造強國、質量強國、交通強國”戰略的必經之路,鞏固智能網聯發展優勢的有效途徑之一。如何推動我國汽車芯片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當前這一行業內外的重要課題之一。
作為承擔產業鏈鏈主角色的整車企業代表,王仕偉重點提出了4大建議。
首先是自主攻堅的步伐要提速。
對品種多、需求量大的車規級常規芯片,建議政策上要加強芯片企業主導,整車廠積極應用、提出需求,分類型聯手組建車規級芯片攻關聯合體,集中優勢資源打通從芯片的設計、制造到封測的產業鏈關鍵環節,解決芯片產業投資高、回收周期長、資源配置效率低等問題。
對于技術資本密集的計算類、存儲類的高性能芯片,建議持續加大研發投入,持續創新攻關工程,打破跨國公司的技術壟斷。同時還要推進配套的軟件開發,培育本土化能力比較強的提供底層軟件和應用層軟件一體化的服務商。
其次是協同培育產業生態。
王仕偉指出,芯片是制造業的核心基礎器件之一,應該通過市場引導和政策支持相結合,強化頂層設計,有序分工。
由于車規級芯片的制造、應用、供需生態非常復雜,即便芯片做出來之后上車還有很大距離。王仕偉表示,對于整個電子電氣的架構、算法,我們一直強調軟硬解耦,這對整車廠而言有價值的,因為數字底座并不經常變化,但是應用層軟件可以持續更新。
但對于芯片企業,這可能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對于芯片來說軟硬無法解耦,而是軟硬有效結合在一起,把芯片算力發揮出來,減少代碼數量。王仕偉強調,“這需要整個產業鏈的協同,讓芯片企業更懂算法,讓算法工程師更懂芯片,只有大家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創新發力。”
再次是培養復合型人才。
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在向智能化、新能源轉型過程中,汽車行業和芯片行業正快速融合。相關人才應是對技術、客戶、場景有深入了解,掌握芯片相關行業知識,了解整車廠具體需求,并能把需求轉化為解決方案的跨行業復合型人才。
還要完善全鏈路標準。
從目前來看,國內芯片的認證標準還是以國外AEC-Q系列的標準為主,但這僅僅是入門級標準。建議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盡快把國內芯片標準體系以及構建框架落實下去。
據吳倩介紹,無論是汽車行業還是行業主管部門,近年來都在不斷推動或出臺政策,加快汽車芯片產業的發展,同時明確指出開展汽車芯片標準體系建設,并且推動汽車芯片標準盡快制定。
《國家汽車芯片標準體系建設指南》指出,到2025年,制定30項以上汽車芯片重點標準;到2030年,制定70項以上汽車芯片相關標準,進一步完善基礎通用、產品與技術應用及匹配試驗的通用性要求,實現對于前瞻性、融合性汽車芯片技術與產品研發的有效支撐。
2023年12月,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汽車芯片標準專委會正式成立。專委會由芯片企業、零部件企業、整車企業、第三方機構的頭部單位30多家、委員40人組成。中汽協汽車芯片標準專委會是目前唯一的全國性汽車芯片團體標準化分支機構。
據悉,專委會成立至今半年多,已經完成了4項標準的立項。
此外,推動汽車芯片產業發展還需強化政策保障。
王仕偉建議,應加大對整車企業、芯片企業、軟件企業及相關單位的政策支持,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平衡好不同階段的利益關系,鼓勵優先采用國內的芯片軟件,用好首臺套、首版次的保障措施。“行業發展需要政策的加持,讓雙方都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存活下來,找到企業發展的動力。”
近年來,汽車和芯片兩個行業正在加速融合發展,國內涌現出了一批優秀的汽車芯片設計、制造、封測企業,產業協同進一步發展。
無論是整車企業,還是上游各層企業,在這一融合中也要做好角色、能力和任務的轉換。正如貢璽所言,過去,一個能做Tier1的主機廠是好主機廠,一個能做Tier2的Tier1才是一個好Tier1,而如今,一個對Tier2有抓手的主機廠才是好主機廠,能力一定是往上游下放的。
從產業生態角度,李成蹊建議,不被卡脖子的正確做法不是單純獨立自主,而是要在產業鏈、供應鏈、技術產品方面更具有黏性,更值得被依賴,中國汽車芯片企業要深度參與全球產業生態建設。這也正是上海智能汽車軟件園作為區域平臺、產業平臺,正在努力推動的生態構建和融合事業。
李邵華堅信,通過技術創新、產業鏈協同、政策支持與市場驅動的共同努力,汽車芯片產業一定能突破瓶頸,實現高質量發展,為新能源和智能網聯汽車產業的繁榮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