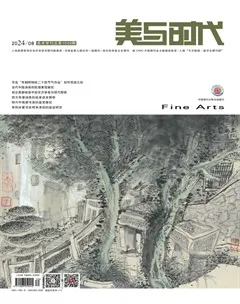矛戟縱橫八法中

摘 要:元代是中國繪畫藝術發展的黃金時期,趙孟頫提出的“書畫同源”理論對這一時期的藝術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該理論認為,書法與繪畫具有內在聯系,鼓勵藝術家在繪畫創作中融入書法元素。在這一理論的啟發下,元代涌現出許多杰出的藝術家,方從義便是其中之一。然而現存的文獻資料多是論述方從義的作畫特點,鮮少提及其繪畫作品中所蘊含的書法特點。從這一方面入手,從書法用筆、書法章法、書法精神三個方面闡述方從義山水畫中的書畫關系,促使人們進一步理解方從義的繪畫作品。
關鍵詞:方從義;書畫同源;筆墨精神
方從義,字無隅,號方壺,又號上清羽士、不芒道人、金門羽客、鬼谷山人,元代道士,尤善書法與繪畫,是頗負盛名的畫家與書法家。元朝時期,趙孟頫提出了“書畫同源”理論,對同時期畫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方從義便是其中之一。在書法方面,方從義擅長草書與隸書,其書法風格自由奔放,充滿個性。這種書法風格不僅展現出他高超的書法水平,還深刻地影響了他的繪畫風格,這是他“放逸”風格形成的重要條件。
一、以書法用筆入畫,線條放逸瀟灑
用筆,是中國畫和書法中的關鍵技藝,涉及筆觸的力度、速度、方向和筆鋒變化等。它直接關系到作品的線條質感和藝術表現力,是衡量藝術家技藝的重要標準。
明代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是這樣記載方從義的書法的:“道士方從義,字無隅,號方壺,貴溪人,工詩文,善古隸、章草。”[1]書中雖然對方從義書法的記載只是寥寥幾筆,但我們通過這些簡單的句子可以了解到他既工詩文又善書法。作為一位如此全能的人才,他的審美與書法水平自然不低。同時,我們也得知了方從義尤善古隸與章草。
元代詩人黃鎮成曾這樣寫道:“方壺仙人灑香墨,矛戟縱橫八法中。青鸞舞罷秋水闊,珊珊飛佩凌天風。”[2]從詩中第一句可以看出方從義能夠熟練運用書法中的筆法——永字八法。這是中國書法重要的用筆法則,以“永”字八筆為例,闡述楷書筆勢的方法。詩中第二句運用物件的比擬手法,通過形容青鸞的飛舞與佩飾的飄動,可以看出方從義作品的特點。無論是書法還是繪畫,方從義的作品都如飄動一般,靈動瀟灑。
永字八法中有一法則是講述橫的:“橫為勒,逆鋒落紙,緩去急回,不可順鋒平過。”陳子莊在《石壺論畫語要》中提到:“元方方壺,善用逆筆。”[3]這是方從義對書法技法熟練掌握的又一例證。陳子莊指出繪畫時順筆易而逆筆難,順筆多用于描繪平緩的地方,逆筆多用于描繪險峻的地方。而山野之間往往不是單一的平緩或險峻的,是二者兼具,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順筆和逆筆的有機結合。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武夷放棹圖》(圖1)是方從義晚年繪制的作品。在《武夷放棹圖》中,首先看到的就是畫面中央的奇峰,此山用筆非常奇妙,可以看出方從義用逆筆繪出了一個險峻的山峰,山體輪廓用筆扎實的同時也沒有忽略粗細的變化。畫面中間山體的紋理線條一頭細一頭粗,這就是快速逆鋒的一種體現。這種用筆方法不僅有利于表現山體生態的生命力,而且能使山體的陡斜更加具體化。
《武夷放棹圖》中有方從義自己的草書題跋。他的草書注重粗細變化,用筆輕松靈巧,還有幾分道家的飄逸姿態。在創作《武夷放棹圖》的過程中,他同樣運用了書法筆法,尤其是在繪制山石肌理時,用筆灑脫奔放。此外,他在皴法表現上模仿了巨然的用筆,但其更加逸筆草草。方從義這種瀟灑的運筆源于草書,他在畫中隨意勾點,無拘無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
方從義的多數作品都展現出明顯的草書入畫特征,給人帶來草書的大筆淋漓之感。《高高亭圖》是方從義筆墨最酣暢的繪畫作品之一,此畫大筆揮墨,描繪了煙云繚繞的山頂景象。這幅作品以“寫”的感覺畫出,下筆飛快,不求形似,旨在強調記錄畫時的心情。在《高高亭圖》中,方從義的草書題跋提到“李君子高昔于南谷丈人坐上會之,今不遠百里求予圖此,已三年矣,醉后縱筆寫之如此”,從中可以看出此畫為酒后之作,這或許是其用筆草草、自由瀟灑的緣故。
在書法創作中,草書不講究形似,而講究虛實結合與書寫者的情感表達。從方從義的作品中就能清晰地看出草書用筆特征。惲壽平云:“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操造化之權,使真宰欲泣也。宇宙之內,豈可無此種境界?” [4]此言完美地體現了方從義的繪畫表現特點。他把個人的精神置于事物的實形之上。在繪畫過程中,他打破了實物的固體造型,使其精神意念在畫作中展現出來。而這種風格與草書的特質不謀而合,正是巧妙運用草書的用筆特征,奠定了方從義“放逸”風格的核心基礎。
由于方從義在繪畫創作中融入了書法用筆,這一手法顯著提升了他在繪畫時的流暢度。書法藝術本身強調“落筆無悔”,即每一筆落下都必須精準果斷,不容許修改或重來。這種對精準和決斷力的要求,使得方從義在繪畫時能夠更加自信和果敢,每一筆都顯得利落有力。他的繪畫作品也因此呈現出一種書法般的流暢美和力度感。
二、以書法章法入畫,虛實相交化神奇
章法,即在書法創作中對作品整體布局的規劃與設計,涉及字與字、行與行之間的和諧、平衡以及呼應。書法作品中對整體結構和布局的精心安排、謀劃,被稱為“大章法”;單個字的筆畫構造和字與字之間的排列方式,則被稱為“小章法”。章法的構成原則是“計白當黑”。“計白當黑”體現了中國書畫藝術中對平衡與和諧的追求,指的是書畫者需要從一開始就構思好如何用墨,最后完美地做到在畫面中留出適當的空白。
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講到“古人論書,以章法為一大事”[5],從中可以看出古人在書法創作及欣賞時對于章法的重視程度。在書法章法中,楷書、篆書、隸書等書體的單字往往可以獨立存在。然而,在草書和行書的創作中,字與字之間的連貫性被給予了極高的重視。這兩種書體有筆勢連接和體勢連接兩種方式。筆勢連接依靠書寫的連貫性,而體勢連接會依靠字體間的穿插錯位。此外,草書的章法特別強調行氣的流暢與和諧。在書寫草書的過程中,書法家需要巧妙運用提按、頓挫等豐富的筆法,以此來創作出一幅具有動感和節奏感的藝術作品。通過這些技巧的運用,草書作品能夠展現出一種生動活潑、富有生命力的美感,使觀者感受到書寫時的韻律和情感流動。
在作品《云山圖》中,方從義就很好地表現了草書章法的特點。首先,該圖中的山體之間是有聯系的。在這幅作品中,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從俯視的角度看這幅畫的風景,那么山體之間就會連成一個“幾”字形。這是筆勢連接在此畫中的體現。然而此畫不僅運用了筆勢連接這一種方法,體勢連接也在這幅畫中體現了出來。從這幅畫的左邊看起,我們可以將左邊的山視為中景,中間的山視為遠景,左邊的山視為近景。那么可以發現,中景與遠景有一部分重疊在了一起,但由于墨的運用程度不一樣,形成了明顯的透視效果。同時,這種前景與遠景的一虛一實,也與草書所提倡的虛實相生一致。
我國傳統繪畫作品多以片段、循序漸進的方式來安排構圖,但是方從義在《云山圖》中并沒有運用這種方式。當我們從左邊的山看向中間的山時,中間的山突然就到了遠處,有如現在的一種數碼拍攝手段突然移向遠景,然而遠景沒呈現多少,又把人的視覺拉回到了近景,這就與草書章法非常相似。在書法作品中,我們很難預判草書的下一筆會如何書寫。草書章法強調節奏感的表現,而方從義的這種“鏡頭”的忽遠忽近,恰巧是一種節奏感的有效證明。
方從義在繪畫創作中,巧妙地融入草書章法,這種創作方法極大地增強了畫面的連貫性。在中國畫中,“氣”的貫通至關重要。而方從義的畫作之所以能夠體現出道家的放逸瀟灑,正是因為他在章法上獨到的處理方式。方從義通過運用草書章法,將書法的韻律美和道家的風范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他個人特有的藝術風格。這種風格既有書法的流暢美,又有道家的超然美,體現出方從義藝術創造水平之高超。
三、以書法精神入畫,自由灑脫畫中生
精神,是人或物內在情感、意志、思想和靈魂狀態的體現,它不僅反映了生命體征,還蘊含了個體的生命力和個性特質。在繪畫創作中,精神的傳達尤為重要。畫家通過作品展現自己的精神世界,與觀眾產生共鳴,促使他們進行思考和情感交流。
徐復觀先生在《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強調了莊子對道家藝術精神的深遠影響,認為莊子的典型性格體現了一種徹底的純藝術精神,這種精神在繪畫藝術中得到了顯著體現。道家哲學將自由視為人生和藝術的最高追求,認為人應該超越現實關系的束縛,追求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自由和無限。道家主張回歸自然,反對壓迫與功利,認為藝術的本質在于表達生命的自然存在和發展。
方從義在年xnlrtZpvrb/GI3j32jxV0nn38gj8B4J8AhFBwIz6kDQ=輕時就成了一位道士,并在那個時期開始深受道家哲學思想的熏陶。其草書的自由奔放和不受拘束的特點,恰與道家追求自然和自由的精神相契合。當我們欣賞古代書法作品時,會發現與詩詞歌賦相比,大部分書法作品在情感表達上往往更加內斂和含蓄,但草書卻能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強烈地傳達書法家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草書的書寫與其他書體有所不同,它多是執筆快速書寫,使字的變化在橫豎頓挫中具有唯一性。正如王羲之嘗試重寫一張行書作品時,他也無法復制第一次寫作時的那份獨特狀態。這種唯一性就如同一次情感表達。老子云:“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6]草書體現出一種天性與自由情感的抒發,擁有一種力圖掙脫世俗陳規的強大的外向力。草書的美是一種解放的藝術,通常能最大化地表達出書寫者強烈的感情,字里行間滲透著濃郁的自由氣息。草書的書寫是書寫者精神漫游的物質體現。書寫者通過抽象的點與線,結合自然環境和情感,從而創作出獨特的藝術作品。
明代董其昌有言:“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7]董其昌認為,草書與隸書抽象的書寫精神可以治俗。這段話很好地印證了書法精神在繪畫中的作用。方從義的繪畫作品給人的印象以煙云繚繞為主,他的山水作品好似人間仙境。如《云山圖》,煙云占據了大部分畫幅,這種大量的留白給人一種人煙稀少或者無人的曠野之感。這種無人之境反映出一種自然最初的模樣,它不受任何世俗的限制。這種自由自在的畫面表現,就是草書精神最生動的證明。正是這種道家精神與草書精神的結合,形成了方從義別具一格的“放逸”風格,這種“放逸”風格使方從義的繪畫免于俗套。
方從義在繪畫創作中將草書精神融入進來,使得道家精神與草書精神在作品中相映成趣,實現了一種精神層面的貫通。草書以其自由奔放、變化無窮的特點,與道家追求自然、超脫世俗的哲學思想不謀而合。方從義的畫作正是在這兩種精神的指引下,展現出一種超凡脫俗的藝術境界。
四、結語
方從義是與趙孟頫同處一個時代的著名藝術家,在思想上受到了“書畫同源”這一先進理念的熏陶和影響。他通過流暢、自由的草書和古樸、端莊的隸書,將書法用筆、書法章法、書法精神融入繪畫作品中,形成了獨特的“放逸”風格。方從義的藝術成就是元代藝術繁榮的一個縮影,也是“書畫同源”理論影響下的產物。他繪畫作品中的書法特點為后世藝術家們提供了寶貴的藝術資源和靈感。方從義的藝術實踐,充分證明了“書畫同源”理論的正確性和前瞻性,為中國畫的發展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
參考文獻:
[1]陶宗儀.書史會要[M].上海:上海書店,1984:343.
[2]成乃凡.增編歷代詠竹詩叢: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696.
[3]陳子莊.石壺論畫語要[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81.
[4]惲壽平.藝文志:南田畫跋今注今譯[M].劉子琪,譯注.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57.
[5]董其昌.畫禪室隨筆[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25.
[6]劉宏彬.經典誦讀:老子[M].武漢:崇文書局,2004:47.
[7]董其昌.畫旨[M].毛建波,校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28.
作者簡介:
李林霖,深圳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畫。